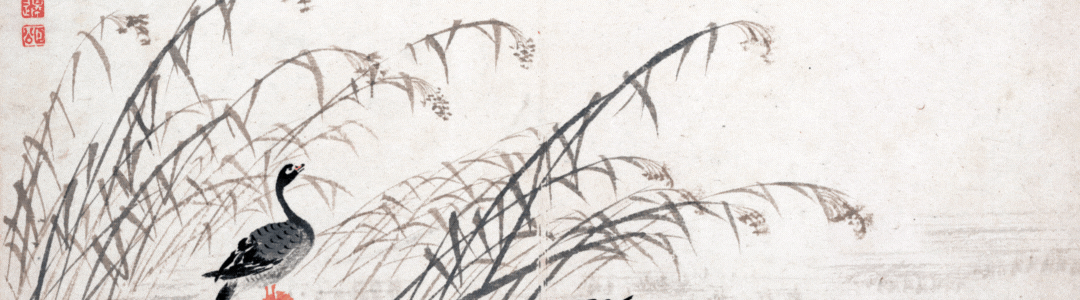
文 |史迁
编辑|史迁
1920年在巴黎签的一份《斯瓦尔巴条约》,1925年中国北洋政府悄悄签了字,之后整整66年没人当回事。
等到中国科学院科学家高登义在1991年翻到挪威《北极指南》的附录,才发现中国居然早就是这个条约的缔约国。

结果,中国在北极的身份,从“门口凑热闹”一下子变成“坐在桌边,有名有份”。不靠吵架,不靠对抗,只靠一纸条约和几十年的科研积累,就把北极话语权稳稳抓在手里。
很多人问,中国北极黄河站怎么来的,凭什么来的,这条被遗忘的条约就是那把钥匙。
斯瓦尔巴:主权在挪威,机会向全世界开放讲北极黄河站,绕不开斯瓦尔巴群岛。地图上看,这是一块离北极点不算太远的群岛,名字以前叫斯匹次卑尔根。看着冷清,背后却是几百年的热闹。
从十六世纪末开始,欧洲航海家往北闯,荷兰人为找去亚洲的新航线,顺带发现了这片群岛。那时候谁也不是为了看风景,大家盯的是鲸油。

那个年代,鲸油差不多就是工业时代的润滑剂和光源,谁掌握,谁就多一张底牌。后来岛上煤炭和矿产被慢慢勘出来,英国、挪威、荷兰等国纷纷上岛抢地盘,插旗子、挖煤矿,一个比一个积极,却谁也没法单方面把主权拍板定死。
这种“谁都想要,又谁都说不清到底归谁”的局面,拖着拖着就成了麻烦。要真比武力,可能迟早要动手;要真比距离,挪威又占便宜。
最后,各国干脆在巴黎坐下来谈。1920年的《斯瓦尔巴条约》就这样出炉,玩了一次很少见的设计:主权给挪威,发展机会大家共享。

条约的核心逻辑其实很直白。对挪威,文件里写得很清楚,承认它对斯瓦尔巴群岛拥有完全和绝对主权,这把挪威的心安住了,岛属于你,这是国际公认的。
对其他缔约国,条约给出一套很实在的安排:只要是缔约国的公民,都可以在群岛上从事商业、科研、渔业、采矿等活动,享受相同的待遇,只需要遵守挪威法律。这就等于说,挪威是房东,不少国家有长期租约,都能用房子挣钱、做研究。
还有一个关键条款,是关于军事用途。条约明确写着,斯瓦尔巴不得变成军事基地。这让那片地方从一开始就被锁定为和平开发和科研区域,给后来的北极合作打了个基调。资源可以去挖,科研可以去做,军舰导弹就不要往那边搬。

在这样的背景下,法国当时提出多拉几个国家签字,目的很现实,就是别让英美在北极布局上占太大优势。于是,中国这样当时无力也无精力去搞北极开发的国家,被拉进了条约圈子。
对北洋政府而言,这是一个几乎不要成本的选择:不用出兵,不用掏大钱,就能在纸面上获得和列强基本对等的条约权利。
1925年,中国签了字,名义上迈进了斯瓦尔巴条约体系。但是那会儿国内战乱不断,生存问题都很紧,别说北极,连近海主权都顾不过来。

这个条约在文件柜里躺了几十年,存在,却等于不存在。等于中国多了一把钥匙,却没有时间去找那把锁在哪。时间往前推到上世纪末,国际政治版图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冷战渐渐结束,世界开始重新审视极地地区的意义。
北极不光是渔场和煤矿,更是气候变化的前哨站,也是未来航道和资源开发的战略高地。沿岸国家早早开始划范围,制定政策,开矿建站。
中国那时主要精力还在近海、南极和经济建设上,北极更多时候是用卫星和模型在“看热闹”,真正参与程度有限。
一切的转折点,落在1991年那本《北极指南》上。
 一纸老条约,从书页里把中国“送进”北极
一纸老条约,从书页里把中国“送进”北极1991年,中国科学院科学家高登义受邀参加挪威组织的北极科学考察。那时,中国已经有南极长城站和中山站,极地科研起步不算晚,但在北极的存在感并不强,很多项目都还停留在观测和合作层面,缺少自己的固定阵地。
考察结束后,挪威方面送给他一本《北极指南》当纪念品。这听上去像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事,顶多是一个工作纪念册。
高登义回去翻书时,注意到书后面的附录,那里印着《斯瓦尔巴条约》的原文和签约国名单。顺着一行行往下看,他在里面清清楚楚看到了“China”这个单词。

这一刻的分量,就不只是一个“惊讶”能概括。因为这个发现,让一个尘封了66年的事实浮出水面:中国早在1925年,就已经是斯瓦尔巴条约缔约国之一。
换句话说,中国在这片北极群岛上,拥有和其他缔约国一样的合法权利,可以在当地开展科研和商业活动,只要遵守挪威法律,无需另起炉灶重新谈判。
在条约重新被注意到之前,中国在北极有一个难以回避的困境:没有北极沿岸国身份,也没有在那里长期存在的基地,一旦要建站,要搞大规模的科考行动,就不得不一遍遍去和有关国家沟通、磋商、申请。

这种状态下,说话就很被动,只能在别人已经划好的框架里找空位,机会大多掌握在别人手里。
条约的“再发现”改变了这一点。因为斯瓦尔巴的规则早就写得明明白白:只要是缔约国,公民和机构就在当地拥有平等开展研究和商业活动的资格。
中国不是从今天才想进来,而是几十年前就已经合法在场,只是自己没用好这个通道。高登义把这一关键信息带回国内,向相关部门进行汇报。这不是一条孤立的“趣闻”,而是一块可以直接嵌进国家极地战略的基石。

条约的存在,让中国在北极从“客人”变成“合伙人”。这不是临时讨来的,也不是靠别国施舍,而是国际法律文件早就确认的地位。接下来的问题,已经不再是“能不能去”,而是“怎么去、去哪、做什么”。
有了这个法理基础,中国的北极部署开始加速落地。纸面权利如果不落实到具体行动,就只能永远停留在书页里。北极方向的决策思路也随之清晰:既然有权利,就要用起来,而且要用得稳,用得久,用出影响力。
1999年,“雪龙号”极地考察船首次北上北极海域,标志着中国不再只是远距离监测那片冰海,而是踏上真正意义上的近距离勘察之路。

这次行动,一方面是科学任务,需要了解北极海洋和大气环境,为全球气候研究积累数据;另一方面也是行动宣示,通过船只进入和科学活动,把条约赋予的考察权实际用起来,让世界看到中国在北极的存在是合规、有据的,而不是临时起意。
北上之后,关于在北极建立固定科研站的讨论逐渐走向实操。到了2001年,国家层面有了关键动作,13个部委联合发文,正式启动北极站选址和建设工作。
北极不再只是科研机构之间的单线推动,而是纳入国家战略安排,涉及到科技、外交、环境、资源等多个层面。这种协调力度,说明北极问题在中国的整体布局中有了明确的定位:既是科研前沿,也是国家长期利益的一部分。

最后落地的结果,就是今天被频繁提起的中国北极黄河站。2004年7月28日,在斯瓦尔巴群岛的新奥尔松地区,中国建成并启用了这座北极科学考察站,地理坐标定格在北纬七十八度五十五分、东经十一度五十六分。
这是中国在北极的首个常年科研基地,也是把《斯瓦尔巴条约》从文件柜里彻底“叫醒”的现实载体。
黄河站的存在标记着中国在北极从法理参与走向实地深度参与,话语权不再只通过文件和发言体现,也体现在一台台仪器、一条条观测曲线、一篇篇科研成果中。

从条约再发现,到雪龙号首航,再到黄河站建成,这条线有一个清晰的内在逻辑。法理地位是起点,国家实力是支撑,持续行动是桥梁。
没有条约,中国参与斯瓦尔巴事务会很费周折;只有条约,缺乏船只、资金、科研队伍和政策协同,权利也会悬在半空。正是规则与能力的结合,决定了中国能走多远,能站多稳。
现在的北极,已经成为全人类观察地球变化的一个巨大实验场。中国通过黄河站等平台参与这一讨论,本身也是在用实际行动回应全球对负责任大国的期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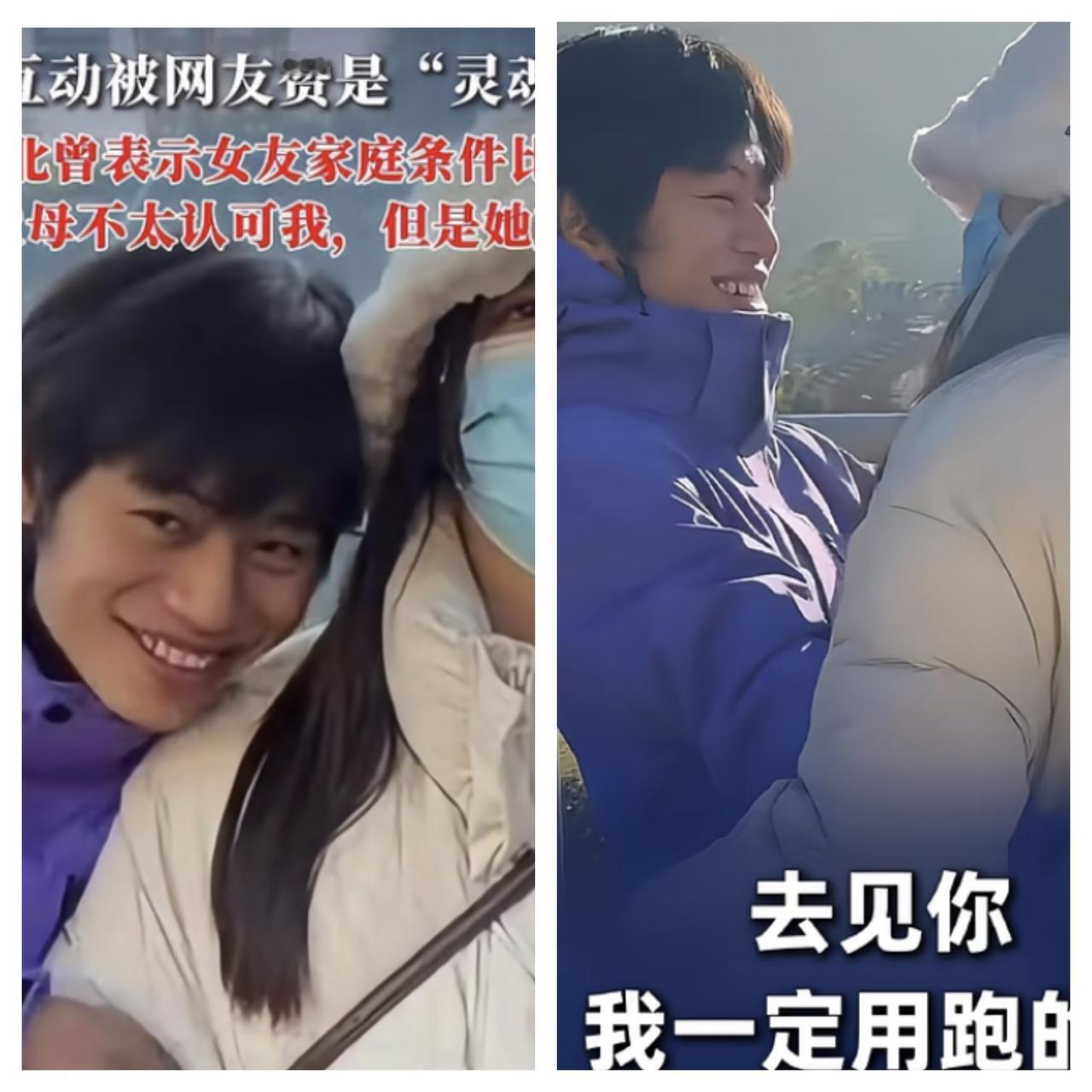




![垂死病中惊坐起,列强不是我自己!太少了,继续造[doge]](http://image.uczzd.cn/803124817420468184.jpg?id=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