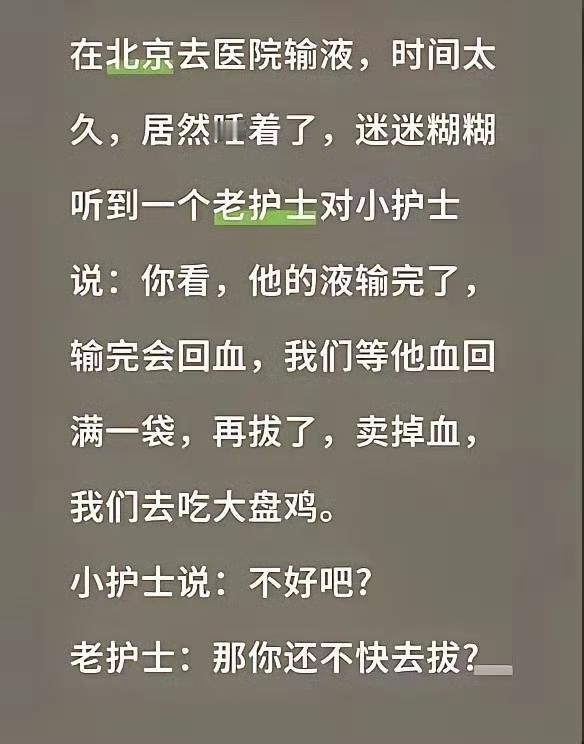[微风]1982年6月16日,就是这个看起来朴实无华的男人,当医生剖开他遗体后震惊的发现,他体内都布满了肿瘤,肝、肺、脊柱,甚至骨髓里……全都是。胸腔里的肿瘤甚至比心脏还大,现场的医护人员瞬间红了眼眶。 一支牙刷能用来做什么?对于1982年住在西安医学院附属医院那个叫罗健夫的男人来说,那不是洗漱用品,而是“止痛器”,每当胸口那股撕心裂肺的剧痛袭来,他就用力把牙刷柄顶在胸前,死死抵住那个让他冒冷汗的位置。 护士长总觉得这个病人“不对劲”,按理说,住进这里的低分化恶性淋巴瘤晚期患者,应该全靠杜冷丁吊着一口气,可翻开他的用药记录,止痛剂那一栏竟然是一片空白。 不是医院不给开,是他自己把药偷偷换成了维生素片,甚至在他去世前那段最难熬的日子里,他还在跟医生讨价还价:“那药打了脑子就成了浆糊,我还怎么改图纸?” 这种近乎自虐的清醒,直到法医那把解剖刀落下时,才真正震住了在场的所有人。 当那个甚至还没显得怎么消瘦的胸腔被打开,医生们倒吸了一口冷气:那里面的惨烈程度甚至不像是一个活人的躯体,癌细胞像野草一样疯长,肝脏表面爬满了黄豆大小的转移灶,脊椎骨被蛀得酥脆不堪,而那颗还在此时早已停止跳动的心脏旁,有一个直径15厘米——比心脏本身还要巨大的肿瘤。 就是拖着这样一副被掏空的骨架,他还在生命最后的三个月里,把被单支起来做防虫帐,就着医院昏暗的灯光,完成了Ⅲ型图形发生器的最后图纸修正。 作为骊山微电子公司只有五个人的课题组核心,罗健夫原本是学核物理的,却硬是在西方技术铁幕封锁的七十年代,把自己逼成了搞电子线路和精密机械的专家,那时候搞科研讲究“三件套”:止痛药、膏药、护肝片,可他却似乎连身体的知觉都屏蔽了。 不仅屏蔽了痛觉,他对物质似乎也失去了感知能力,在那个分房、评职称都要争破头的年代,他把好不容易评上的高级工程师职称让给了同事,把3000元的科研奖金全额上交,连单位分配的新房钥匙都转手送了人。 走进他生前的那个被改造为实验室的废弃仓库,你会看到两块水泥板拼成的床,以及办公桌上一盏用纸糊灯罩的台灯,哪怕是在他去世后,家人整理遗物时才发现,这个连陪妻子逛街都只舍得给同事孩子买新布鞋的男人,自己的衣柜里除了发黄的旧衣,就是那顶参军时戴过的旧军帽。 真正属于他的“财富”,全锁在实验室的那个铁皮柜子里——整整23本被药渍和机油浸透的笔记本。 他的妻子回忆送饭时的情景,总是饭菜热了凉、凉了又热,那个男人却像被钉在图纸上一样,因为他比谁都清楚,他手里摆弄的那台样机,就是制造航天芯片的“光刻机”,在那个没有一张完整参考图纸的时代,这一笔一画,就是在为国家甚至还没影子的通信卫星铺路。 在他走后的第二年,也就是1983年,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传来了欢呼声,当第一颗国产通信卫星升空的指令下达时,总设计师手里那本操作手册的扉页上,还留着一行醒目的红色批注:“此处需加装散热片,谨防元件过热。” 那是罗健夫在生命尽头留下的最后一道笔触,他没能看到火箭升空,就像他没来得及把自己那个酥脆的胸骨真正治愈一样。 如果时光倒流,没人知道如果早一点用上止痛药,或者早一点走出实验室去体检,他能不能多活那医生口中的“五年”,但那个摆着被翻烂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桌案已经给了答案,他不怕死,只怕在这场与时间的赛跑里,那个从1969年就开始攻关的图形发生器还没造好,人就先倒下了。 罗健夫并没有在这个世界上留下太多影像,但在今天的航天展厅里,看着他用过的算盘和那双磨破底的皮鞋,你会明白一种超越物理极限的“硬度”,在那些不计其数的深夜里,这个自称身体疼但脑子不能糊涂的工程师,用血肉之躯在绝境中填补了中国航天电子工业的空白,他把自己燃烧得只剩一把骨灰,却把最坚硬的脊梁,留给了后来腾飞的大国重器。 信源:开福开讲│第100期 罗健夫:甘为科研献终生 - 澎湃在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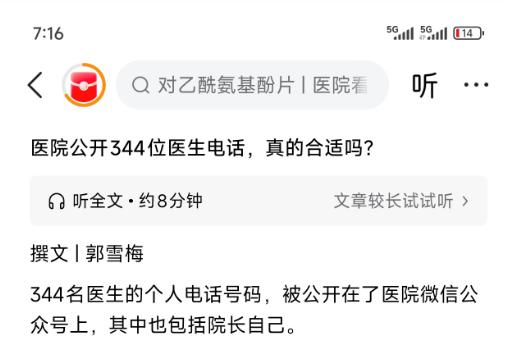
![[点赞]2003年9月11日,邱小强趁妻子洗澡之际,向她的咖啡杯中投入了致命剂](http://image.uczzd.cn/14928907368198797270.jpg?id=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