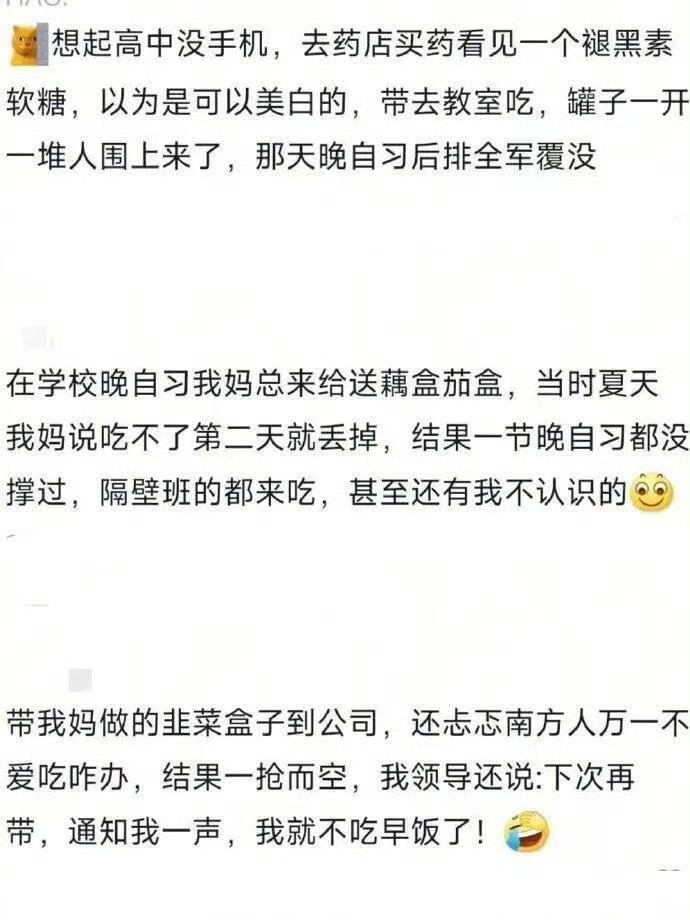在早年间不管是猪杂、牛杂、羊杂这些,吃不上饭、吃不饱的人们没几个看得上。没有油、辣来包裹着,就水煮撒点盐吃,真的寡腥、寡臭,难吃。大家一致看上的是带肥的猪肉,那才是最爱。 2023年,深冬时节在沈阳胡同口,老周家的铁锅正爆得热闹。 蒜苗段裹着猪大肠,食客攥着啤酒瓶喊“再来一盘”。 这盘当年被穷人嫌到踢一边的“猪下水”,如今成了东北小馆的“流量担当”。 可没人记得七十年前,同样是一盘猪杂,是连狗都不愿意凑近的“贱 货”。 五十年代的东北农村,杀猪是全村的节日。 屠夫的刀刚落下,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就被抢光。 那是能炼猪油、烙饼子的“硬通货”。 剩下的猪肝、猪肠、猪肺,堆在案角没人碰,最后贱卖给城里的豆腐坊,或者喂了村口的黄狗。 “那时候谁吃猪杂?嫌腥!” “没油没盐,煮出来一股子屎尿味,吃了准拉肚子。” 萧红在《呼兰河传》里写得更显而易见。 邻居家娶亲,主家蒸了两条松花江鱼,汤清得能照见人,肉薄得刺都扎嘴。 客人吃着吃着就撇嘴,心里骂“小气巴拉的,咋不切块肥猪肉浇热油?” 萧红自己小时候也见过,屯子里的王大爷把猪肠用碱水泡三天,搓掉黏糊糊的杂质,煮出来咬着像橡皮筋,腥味直往嗓子眼钻,村里的年轻人宁可饿肚子也不碰。 为啥没人待见猪杂? 不是味道差,是穷日子里“顶饱”比啥都重要。 肥猪肉热量高,一斤顶三斤猪杂。 那时候人缺油水,吃点肥肉能扛三天饿。 猪杂呢? 蛋白质高是高,可脂肪少,转化能量慢,吃一斤还饿得慌。 加上没调味料,油一斤两毛,辣椒面得从山东运,煮出来撒把盐,腥气直冲鼻子。 更要命的是卫生。 没冰箱,猪杂放两天就变质,寄生虫感染率高达三成,吃坏肚子是常事儿。 档案里记着,三十年代东北农村,猪下水利用率不到两成。 不只是东北。 华北平原的农民日记里,猪杂是屠宰场乞丐的“专属”。 西北牧区的羊杂,得风干成肉脯才敢留。 江南的牛杂更惨,杀牛要报备,杂碎直接扔河里喂鱼。 老辈人说:“穷时候,猪杂是‘边角料’,连狗都不乐意吃。” 而猪杂的命运转折,藏在三个“第一次”里。 第一次,能洗干净了。 六十年代,东北出现了第一家猪杂加工厂。 工人们用碱水漂洗猪肠,面粉搓掉内壁的淋巴,再用白酒焯水。 这招是屠夫传下来的“土办法”,能把腥臭味压下去。 第二次,能入味了。 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家庭厨房有了煤气灶。 东北阿姨们试着把卤好的猪杂再爆炒,加蒜苗、豆瓣酱,把腥味逼出去,把香味炒出来。 老周家的爆炒猪杂就是这么来的。 “以前卤完直接吃,现在爆一把,蒜苗的香裹着猪大肠的油,连我家那口挑嘴的老头都爱吃!” 第三次,懂营养了。 九十年代末,营养学普及开来,猪肝的铁含量是猪肉的18倍,猪肺含丰富的胶原蛋白,猪肠的膳食纤维能促消化。 人们突然发现当年嫌的“下水”,居然是“营养宝库”。 现在超市里的猪杂,都标着“高蛋白、低脂肪、补铁”,连健身房的白领都抢着买。 如今再看爆炒猪杂的做法,每一步都藏着“对过去的回应”。 清洗用面粉加小苏打,搓掉淋巴和杂质,解决“腥臭”的根。 焯水加白酒去异味,比当年的“清水煮”强十倍。 卤煮再爆炒把猪杂的“死腥”变成“活香”,符合现代人的口味。 老周家的餐馆开了三十年,他说:“以前客人点猪杂,是图便宜;现在点,是图好吃。你看那大肠,嚼着香而不腻;小肠嫩得能咬出汁;猪肺混着蒜苗,鲜得掉眉毛。” 更有意思的是,当年抢肥肉的年轻人,现在成了点猪杂的主力。 从“避之不及”到“排队抢吃”,猪杂的翻身仗,打的是七十年生活改善的账。 当年穷人抢肥肉,是因为“能吃饱”。 现在人吃猪杂,是因为“吃得好”。 就像老周说的:“不是猪杂变金贵了,是咱兜里有俩钱了,敢讲究点了。” 如今,早就没人记得七十年前的腥臊,只记得现在的油香。 这大概就是生活最实在的模样。 主要信源:(青海日报——民国时期的羊杂 碎)


![谁说韩国吃不起肉,那是爱美。[无奈吐舌]](http://image.uczzd.cn/12733719206496597648.jpg?id=0)

![肉肉大米这么火的嘛?下午一点多了,就这个排队[???]不就是铁板汉堡肉配几颗西蓝花](http://image.uczzd.cn/10057003805028149490.jpg?id=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