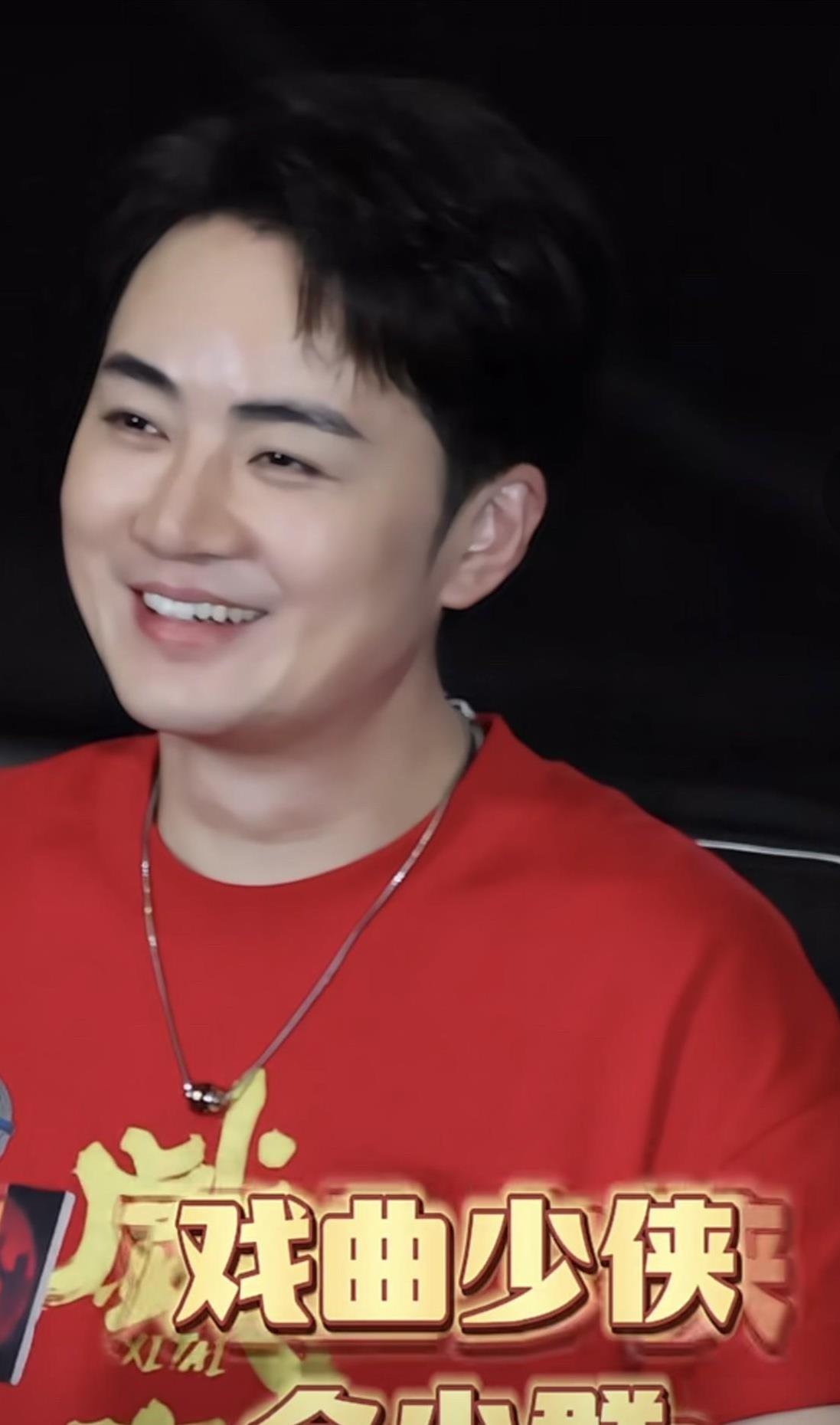1918年,天津的一家戏院里,观众已开始焦躁了,纷纷质问演员什么时候能重新上台,就在这时,一个看起来七八岁的小女孩走上台。
在中国古代,男尊女卑的现实曾令女性处于极为低贱的地位。尽管在梨园学习戏曲是男子的常事,但若是女子进入梨园,却往往会被视为“下九流”,遭受歧视。然而,历史上总有例外,正是在梨园这个男多女少的环境中,有一位女性硬生生闯出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她便是被称为“一代冬皇”的孟小冬。 1927年农历正月二十四,孟小冬与梅兰芳结婚。那场婚礼简单低调,没有传统的合八字、选吉日,也没有烟花爆竹、花轿乐队,婚礼上只有亲朋好友的陪伴。婚后的梅兰芳依旧忙于演艺事业,继续登台唱戏、拜访朋友,而孟小冬则逐渐隐退,过上了更加封闭的生活。她开始学习骑自行车、弹奏钢琴、绘画、书法,偶尔也会练习嗓音和身段。 虽然生活平静,但她与梅兰芳共同度过的那些时光依然让她感到幸福。记得有一次,梅兰芳带回了一架相机,孟小冬拿着相机给他拍照,梅兰芳在墙上留下了影像,她问梅兰芳:“你在那里做什么?”梅兰芳笑着回答:“我在做鹅影呢。”这段对话温馨且亲切,成为了她们婚后最甜蜜的回忆。 1930年,梅兰芳的大伯母梅雨田夫人去世。孟小冬剪短发,戴上白花,穿着素衣,来到梅府门前为婆婆守孝。然而,就在她准备进入梅府时,却被仆人拦住。仆人冷冷地喊道:“孟小姐请回。”虽然梅兰芳想让孟小冬进来,但却被福芝芳威胁:“如果让她进来,我就和孩子一起死。”梅兰芳处于两难境地,最终选择不再干涉家事,而孟小冬的心彻底伤透了。从此,她明白了自己在梅府的地位,她不过是一个外人,始终无法融入这个家庭。
1918年,天津的一家戏院里,观众已开始焦躁了,纷纷质问演员什么时候能重新上台。在后台的争议声中,孟鸿群坚持要重返舞台。他已经缓过一口气,脸色也有了些许好转,但周围的人都劝他要以身体为重。一场戏的成败固然重要,可也不能置演员的性命于不顾。然而,作为一个老戏班的演员,孟鸿群深知观众的期待有多重要,尤其是在天津这个地方。 就在众人争执不下之际,一个瘦小的身影悄然走到父亲身边。这个七八岁的小女孩,正是孟鸿群的女儿。她虽年纪尚小,却在戏班中长大,耳濡目染间早已熟悉了戏曲的规矩。父亲的身体状况显然不适合重新登台,这一点她看得很清楚。 琴师正在台侧准备着,舞台上的烛火映照着幕布,观众的喧哗声透过帘子传来。小女孩突然开口,提出要替父亲去台上清唱一段。这个提议让在场的人都愣住了,不等大家反应,小女孩已经迈着坚定的步伐走向了舞台。当她掀开幕布,走上台去的那一刻,台下的喧哗声渐渐平息了。 观众们都被这个意外的场面吸引住了。只见小女孩先是向台下深深鞠躬,然后简单解释了父亲身体不适的情况,并提出要清唱一段《捉放曹》。她的声音清脆,话语间透着一股让人意想不到的沉稳。说完,她又转身向琴师致意,示意开场。台下的观众从最初的惊讶,渐渐转为认真倾听,直到掌声和叫好声此起彼伏。十年后,当孟小冬再次来到天津时,已是声名鹊起。
孟小冬的最后一次公演发生在1947年8月30日,地点是杜月笙的六十大寿宴会。为了这场公演,孟小冬精心准备了三个月,这次演出为公益性质,所有所得的善款都将用于赈灾。梅兰芳也应邀出席,但由于孟小冬并不愿与梅兰芳见面,杜月笙特意安排了演出的顺序,梅兰芳先唱前八天,而孟小冬则在最后两天上场。 这场为期十天的义演,筹集了超过二十亿的善款,外加三十多亿的寿礼。即便在今天,这依然是一笔巨款,更不用说在当时。孟小冬的义演吸引了成千上万的观众,甚至连黄牛票都买不到。人们纷纷涌向剧场,大家都想亲眼见证五年没有登台的孟小冬是否依然能保持她的演技。就在所有人以为他们将有更多机会听到孟小冬的演唱时,没想到这次《搜孤救孤》会成为她的绝唱。 孟小冬移居台湾后,过上了隐居的生活。她不再去杜月笙的坟墓,也没有联系杜月笙的后裔或徒弟们。她住在台南的一个小城市,那里依山傍水,远离尘嚣,邻居们甚至不知道她是曾经红极一时的坤伶“冬皇”。她自己也避免出风头,平日里自称“孟家妈妈”,唯一的女仆则负责家务。 在这个安静的地方,孟小冬时常怀念她的恩师余叔岩,回忆起余叔岩身患膀胱癌,却依然忍受着剧痛,一字一句地教她唱戏,勉强站立,用微弱的力量支撑着孟小冬的每一个动作。她与几位知己商议后,决定免费教授余派唱腔。很快,几位年轻人慕名而来报名学习。尽管年事已高,孟小冬依然每天为学生们精心准备。 每晚,她戴上老花镜,把自己保存的剧目唱词一字一句地誊写好,第二天早上,学生们来上课,她不计酬劳、不畏辛劳,像昔日余叔岩教她那样,一字一句、一腔一调地反复教导。在她严格要求下,学生们逐渐掌握了余派唱腔的精髓。后来,章士钊前往香港邀请孟小冬回大陆,但她婉拒了,解释道自己因健康问题,常常不敢活动,因此无法接受邀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