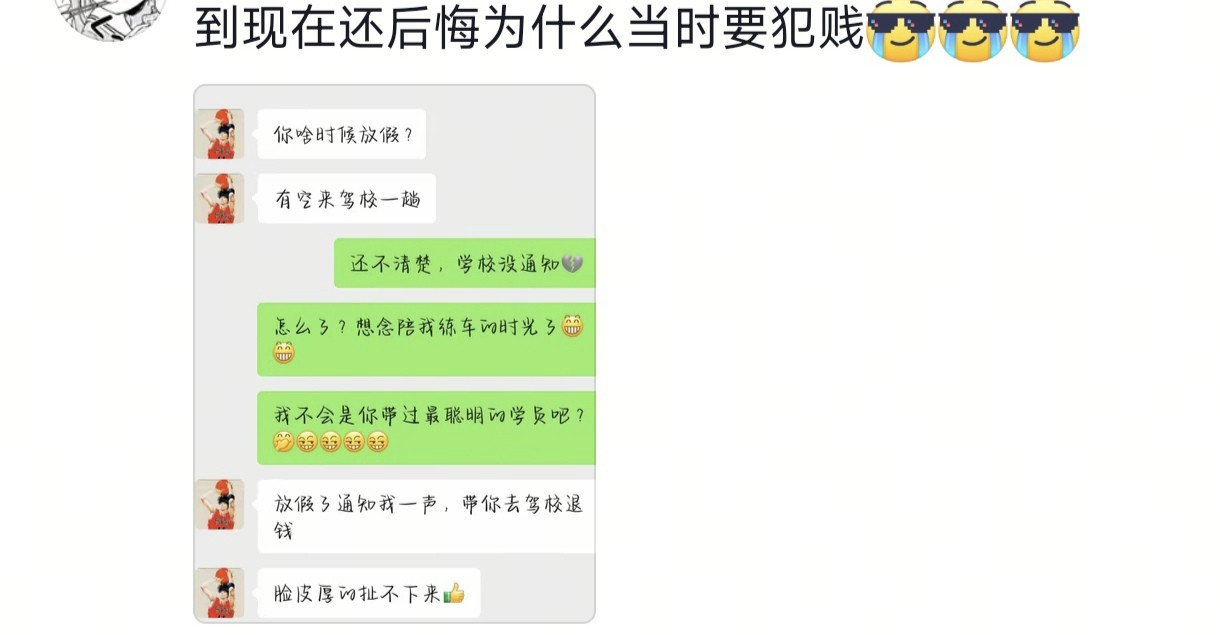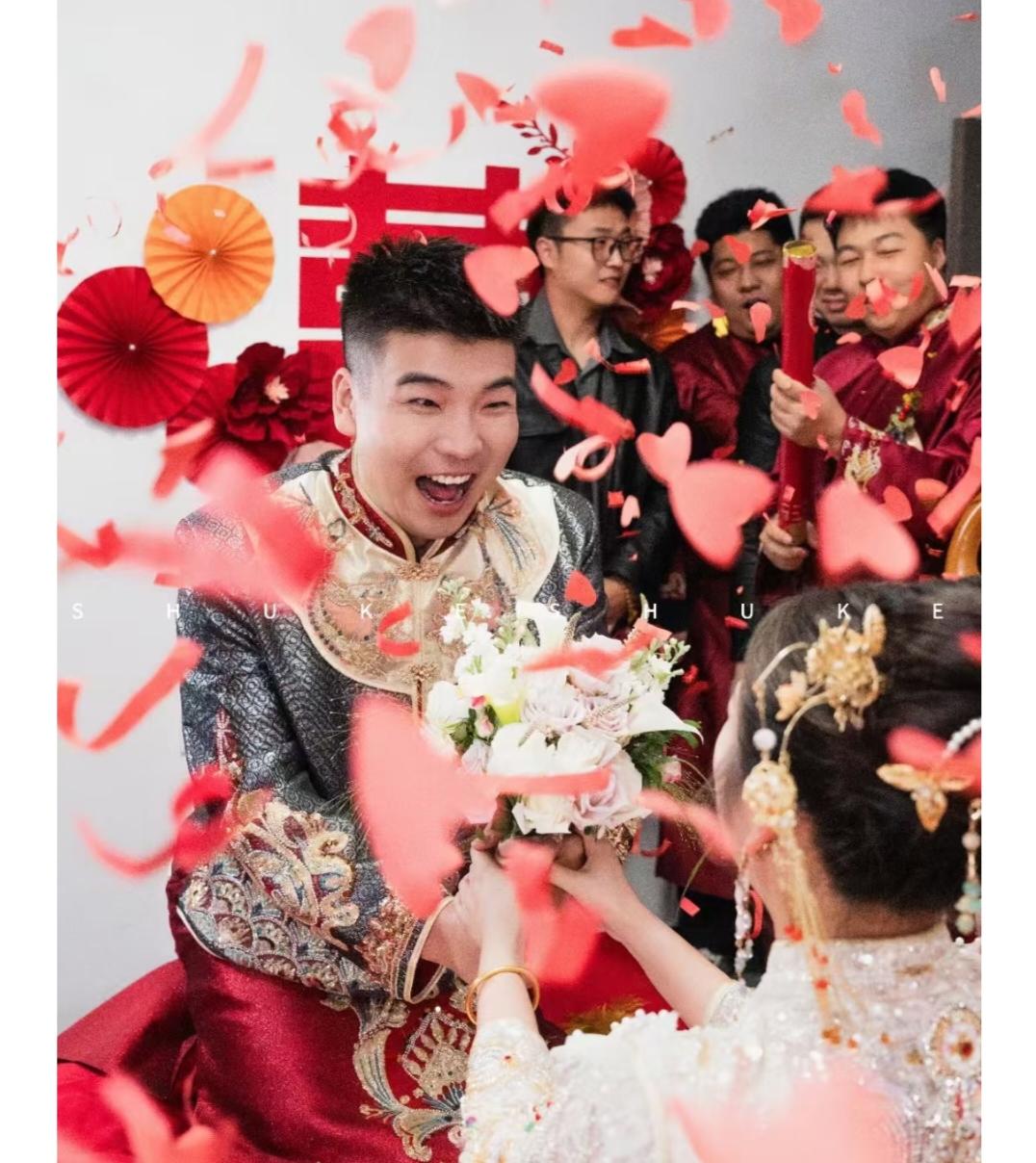2007年,16岁的冯霞在学校爬墙跟一陌生男人跑了,自此杳无音讯,15年后,母亲找到她时,冯霞穿着褪色的短袖,磨平底的拖鞋站在一户门前,手脚还在不停地抖动。 在这个被极度物质化挤压的生存空间里,一条人命究竟价值几何?对于冯霞而言,这个问题的答案残酷得令人窒息——也许还抵不上几碗廉价的面条。 当她被像处理过期垃圾一样被推出家门时,手里唯一的全部身家,只是一个装着旧衣裳和身份证的劣质塑料袋。 这不仅仅是一次家庭纠纷的驱逐,更像是对她这一生彻底贬值的宣判。那副躯体已经很难被称为“有着生命力的人”。 晚期脑瘤在颅内疯狂压迫,而甲状腺功能的极度亢进像一台失控的引擎,让她瘦得脱了形,面色如同失去了所有血色的黄蜡,四肢不受控制地剧烈颤抖,每迈一步都像是赤脚走在刀刃上。 这种地狱般的生理折磨,原本并非完全没有喘息的机会。医生并不是没有给过方案,只要先控制住甲亢,脑部手术的希望尚存。 而这道“救命门槛”的入场券——抗甲亢药物,每周的开销仅仅五十元。但这笔甚至不够在这个城市吃顿像样午饭的钱,却成了冯霞无法逾越的天堑。 与她生育了三个孩子的丈夫朱平,在这道生死的算术题前,给出了一个冷血至极的零分。他拒绝支付。 这五十块钱的吝啬,直接掐断了后续所有手术的可能,也将冯霞推向了医生口中“最多只能活三个月”的绝境。 这种被抛弃的宿命感,似乎在冯霞的人生剧本里写满了讽刺的注脚。把时间轴拉回十几年前,她也曾是一个想要掌握自己命运的“叛逆者”。 那一年她才十六岁,父亲早逝的阴影叠加母亲改嫁带来的被背叛感,让这个身处江苏某职校的少女做出了一生中最决绝也最幼稚的反抗。 她翻越了学校的高墙。那时的她天真地以为,逃离了母亲汪桂香的管辖,翻过去就是自由,殊不知那是通往更深囚笼的入口。 惩罚来得比预想中更快且狰狞。她以为的“新世界”迅速坍塌成三年的黑暗监禁,一个陌生男人用暴力粉碎了她对自由的所有幻想。就在那个至暗时刻,朱平出现了。 现在的刽子手,当年曾是她的“超级英雄”。是朱平把她从第一个泥潭里拽了出来,那种绝处逢生的感激,让冯霞产生了一种致命的错觉:她以为遇到的是救赎,其实只是从狼穴跳进了虎口。 为了报恩,她在这个男人身边停泊,甚至以为这一纸婚约是避风港。但现实撕下面具甚至不需要太久,曾经的温情迅速剥落,取而代之的是拳脚与冷眼。 直到她病入膏肓,这位“恩人”撕破了最后的体面,不但不愿出一分钱救命,更急不可耐地宣称早已毫无瓜葛,将濒死的她扫地出门。 她在寻找爱的路上,连续两次狠狠摔进深渊,把自己撞得粉身碎骨。而在她一生都在试图逃离的起点——那位被她记恨、甚至想通过出走来“报复”的母亲,却在命运的废墟中徒手挖掘了整整十五年。 从冯霞翻墙消失的那一刻起,母亲汪桂香的人生就只剩下了两个字:寻找。 这位母亲把自己活成了流浪者,为了不错过任何一丝线索,她辗转在江浙一带的各个城市,车站冰冷的水泥地睡过,救助站的角落蹲过。 她做着最底层的苦力零工,把所有的尊严和汗水都换成了车票和寻找的路费。她的口袋里,始终揣着一张冯霞童年的照片,那照片已经被摩挲得边角起毛、画面模糊,却成了支撑她走过五千四百多个日夜的唯一图腾。 当“宝贝回家”志愿者的介入终于把这条断裂的纽带重新接上时,这对母女的重逢没有任何电影式歇斯底里的质问。 看到眼前这个被病魔啃噬得不成人形、被丈夫当做垃圾丢弃的女儿,汪桂香没有一句责备“你当年为什么跑”,甚至没有抱怨一句这些年的苦。 她做得最果断的一件事,就是接盘了那个被所有人放弃的生命。 那个为了五十元药费就能将妻子判处死刑的丈夫早已不知所踪,而早已一无所有的汪桂香,却为了给女儿筹集那天价的医疗费,义无反顾地变卖了自己赖以生存的房子,四处低头借债。 在这场注定赔本的赌局里,母亲押上了自己仅剩的一切,只为了给那个只有三个月期限的生命,争取多哪怕一分一秒的尊严和温暖。 这或许是世间最讽刺的对比:年轻时拼命想要逃离的母亲,最后成了唯一的依靠;曾经视为恩人和归宿的爱人,最后成了催命的阎罗。 在生命即将燃尽的最后时刻,冯霞那一半不仅属于病理上的癌变,更是关系里的恶性肿瘤。 而母亲汪桂香用失去了房子和十五年光阴换来的守护,才勉强为这出悲剧涂抹上了一层人性仅存的暖色。对于冯霞来说,这条回家的路,走得实在是太痛、太久了。 信息源:《16岁女孩在学校爬墙私奔杳无音讯,15年后母亲找到时,她手脚抖动生命垂危》搜狐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