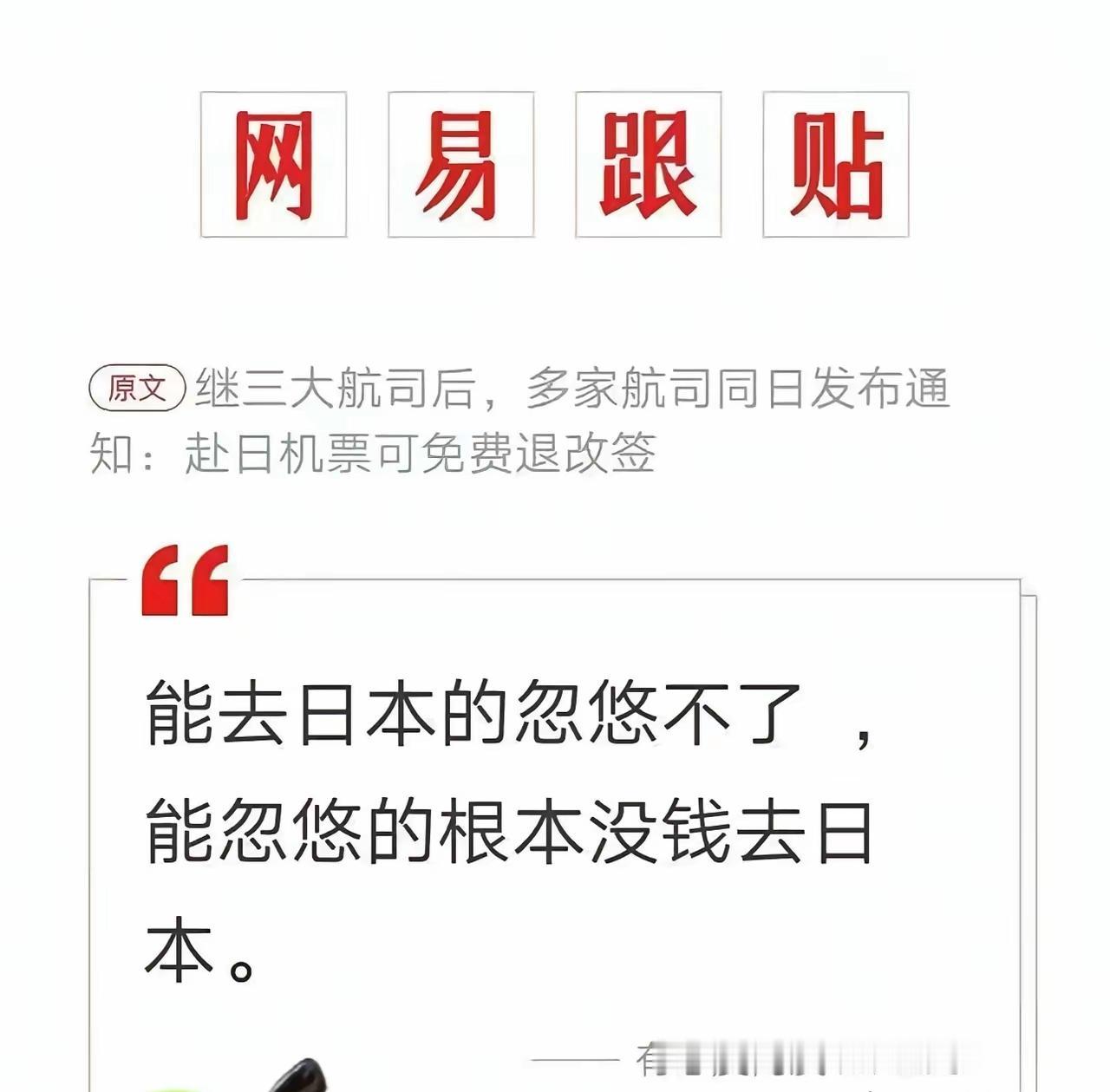“大佐”这个称呼,在中国上至耋耄老人、下至垂髫孩童,恐怕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甚至这个词本身就是一幅幅狰狞画面。对国人来说,这个词语代表的不仅仅是调侃、戏谑,更多的是对那个兽性群体的憎恶和痛恨。而如今,“大佐”可能要回来了!就在11月13日,日本政府放出这个风声,并不是简单把军衔改个称呼——从“1佐2佐”改成“大佐中佐”,连基层士兵的称谓都要往二战旧日军那边靠拢。尽管表面说是“跟国际接轨”,但明眼人都看得出,背后藏着更大的盘算。

日本自卫队1954年成立时,受制于国际法约束,并为了躲避世人眼中的“侵略军”形象,不仅刻意避开了“军队”名号,还特意把军衔也进行了“去日军化”,从“大佐”“中佐”改成数字序号,职种名称也改成“普通科”“高射特科”这种非军事化的叫法。这套用了70年的规矩,本来就是要淡化军事色彩,符合和平宪法“专守防卫”的定位。但如今,自民党和维新会联盟一拍板,连步兵炮兵的职种都要改回“步兵科”“炮兵科”,统合作战司令部的高官甚至能挂上“大将”军衔。这哪是什么“接轨”,分明是在给自卫队“脱胎换骨”铺路。
对于这个做法,就连日本防卫省内部都有人摇头:军衔翻译成英语就能对接国际,急吼吼改个称呼是为了什么?说白了,这就是右翼势力“借尸还魂”的套路。看看近些年日本的操作:2022年新“安保三文件”通过,2025年军费直接飙到8.7万亿日元,远程导弹、轻型航母、两栖攻击舰这些进攻性装备噼里啪啦“下饺子”。现在连军衔都要“复辟”,分明是在给自卫队从“自卫武装”往“正式军队”转型造势。毕竟“大佐”在二战时可是能指挥几千人的联队长,是战场上的关键角色,这个称呼一恢复,自卫队的“自卫”属性就淡了一分,“侵略军”的形象已跃然纸上。

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这种操作反而暴露了自卫队的尴尬。日本防卫省去年数据白纸黑字写着:2023年自卫队实际招募人数只完成计划的51%。招兵都招不满,靠改个“大佐”名号就能让年轻人抢着入伍?这逻辑怕不是从旧日本陆军学来的。
如前面所言,这种“复古”操作也令自卫队更像“侵略者衣钵传承者”。二战时中美苏朝都曾击毙过日军“大佐”,1945年更是击毙最多的一年。这些历史伤痕,不会因为换个称呼就消失。日本右翼总抱怨“自虐史观”,可真正“自虐”的恰恰是他们——非要捡回“大佐”这个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称谓,反而让周边国家更警惕:这哪是“与国际接轨”,分明是军国主义阴魂不散。
说到底,日本这波操作不是孤立的军事动作,而是“政治军事大国”布局的一环。从允许自卫队海外救援、击落无人机,到成立统合作战司令部,日本军事扩张的脚步就没停过。如今军衔改制,本质上是军事战略从“专守防卫”向“主动防御”甚至“海外投送”的转型信号。

对历史记忆尚未远去的亚洲邻国来说,这不是“技术调整”,而是赤裸裸的军事扩张信号。二战时日本军国主义的灾难记忆犹在,如今“大佐”归来,怎能不让人担心历史重演?正如有学者说的,日本右翼的“小心思”终究是短视——与其费尽心思改军衔,不如好好解决自卫队招兵难、装备效率低的问题。这些热衷给侵略者招魂的右翼保守势力,包括高市早苗在内,一直以日本的 “自虐史观”为耻。殊不知,恢复“大佐”等旧称其实才是真的“自虐”。
这场“大佐”复辟的闹剧,最终会如何收场?是成为“正常国家”,还是被历史反噬跌回军国主义老路?答案不在国会山,而在日本能否正视历史、尊重周边国家的安全关切。毕竟,真正的实力不是靠改个军衔就能把握的,这需要经济、军事的后盾,更需要对战争的敬畏和正义的追求,需要民族的反省和忏悔、野心的收敛和自律,但从目前情形看来,这些恐怕都必定成为奢望!
此刻,亚洲的警钟已经敲响。我们迫切需要对日本军事扩张野心保持高度警惕,在必要的时刻,采取雷霆的手段,把试图复辟的“大佐”们永远扫进历史垃圾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