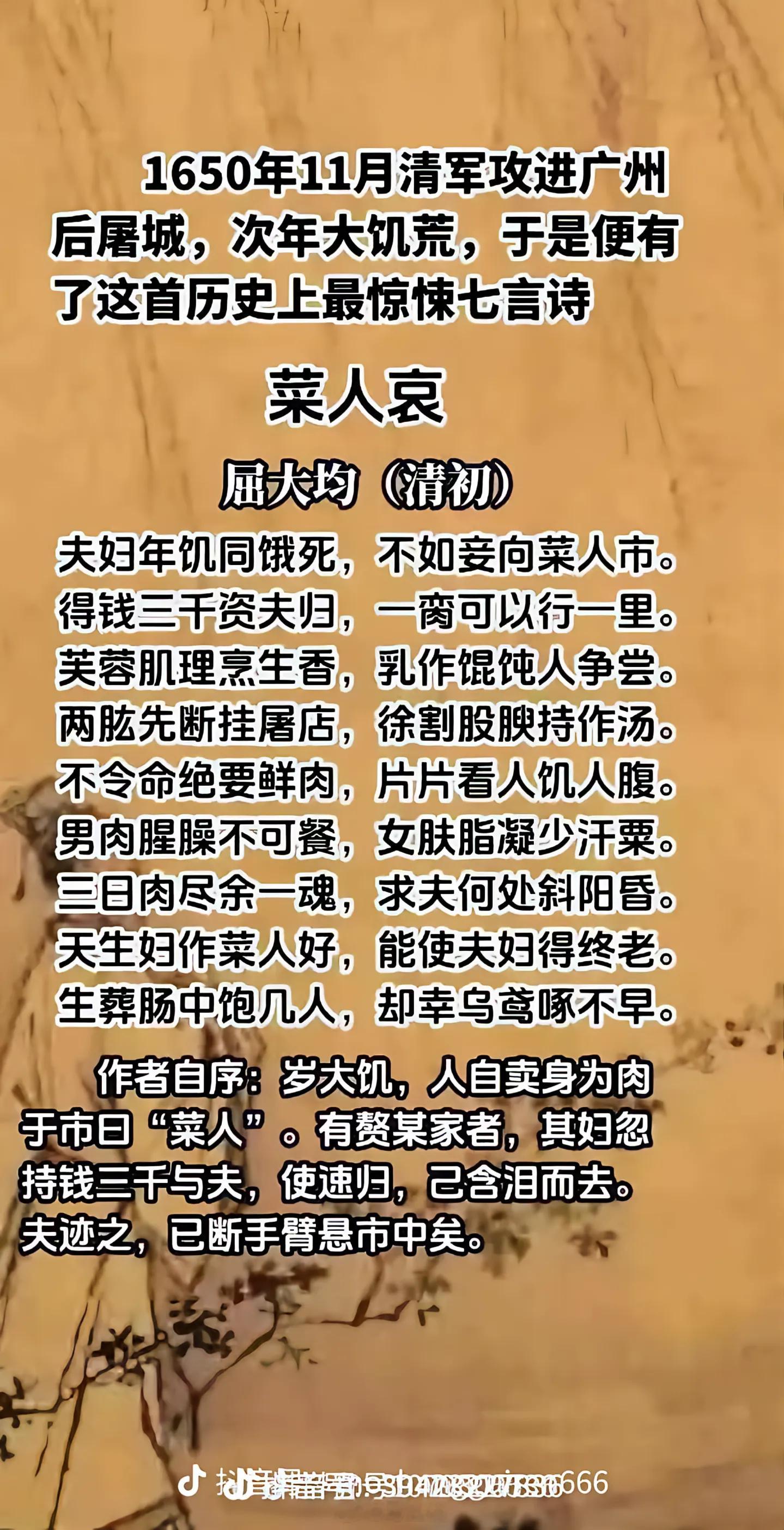宜兴丁蜀镇的黄龙山,自古藏着一把火——泥与火淬炼的紫砂,自北宋发端,在明清绽放,却在近代几经浮沉。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二十世纪中叶,七位紫砂匠人如北斗列宿,以匠心为引、技艺为翼,将这门“方非一式,圆不一相”的民间工艺,托举至“东方艺术明珠”的高度。他们,便是后世敬称的“紫砂七老”。
那是一个大师与时代同频共振的黄金年代。七老之中,有承前启后的“壶艺泰斗”,有独辟蹊径的“花器圣手”,有深耕创新的工艺先锋,更有并肩携手的同道知己。他们用一生诠释:所谓“星光熠熠”,从不是孤星的闪耀,而是一片星群的辉映。
一、黄龙山下的觉醒:从“匠”到“家”的时代注脚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开始系统整理传统工艺。宜兴紫砂合作社成立,分散的手艺人有了“组织”。彼时的紫砂界,虽有零星高手,却多以“做壶谋生”为念。直到一群年轻人的出现,改变了轨迹。
顾景舟时年三十余岁,已在沪上仿制古壶名动江湖。这位后来的“壶艺泰斗”,带着对传统的敬畏回到丁蜀,一头扎进合作社的工坊。他教徒弟“看泥色要像中医搭脉”,刻款识需“笔笔有来历”,连烧窑时观察火色都要分“蟹壳青”“茄皮紫”。有人笑他“太严”,他却说:“我们不是做壶,是在给紫砂写史。”
与他同辈的蒋蓉,则在花器领域开宗立派。这位出身陶艺世家的女匠人,把童年在荷塘边看藕节、蹲在菊丛旁数花瓣的记忆,都揉进了壶里。她的“荷花壶”用段泥拼贴花瓣,筋络根根分明;“荸荠壶”取法老荸荠的斑驳肌理,憨态可掬。合作社的老艺人回忆:“蒋师傅的壶,连外国人都看痴了,说‘这不是泥做的,是从地里长出来的’。”
时代的春风,吹醒了紫砂的“匠魂”。七老中的徐汉棠、高海庚、李昌鸿、沈遽华、周桂珍,或拜入顾景舟门下,或在合作社切磋技艺,终于从“手艺人”成长为“艺术家”。他们不再满足于复制古壶,而是用现代审美重构传统——徐汉棠将石瓢壶的线条削得更利落,李昌鸿把青铜器纹样嵌进壶盖,沈遽华则用“绞泥”让壶身流淌出云纹……紫砂,第一次有了“当代性”。

七老的魅力,不仅在于个体的璀璨,更在于他们彼此照亮。
顾景舟与蒋蓉,一个是“光素器之王”,一个是“花器之后”,看似风格迥异,却常凑在一张泥凳前讨论:“你的荷花要配我的石瓢,才算圆满。”有一回,合作社接下出口订单,需设计一套“四季茶具”,顾景舟画了梅枝的轮廓,蒋蓉便依势捏出腊梅的蓓蕾;徐汉棠雕了竹节的壶把,沈遽华便用绞泥填上霜色。这套“四季壶”后来成了国礼,外宾惊叹:“每把壶都像一首诗,合起来是中国人的四季。”
高海庚与李昌鸿、沈遽华夫妇,则是“技术革新派”的代表。高海庚曾在中央工艺美院深造,带回“陶瓷工艺学”的理论,拉着李昌鸿琢磨“泥料配方与烧成温度的关系”。他们改良了“方器”的拼接工艺,让壶身的棱角更挺括;沈遽华则尝试将釉料融入紫砂,创造出“色釉装饰”的新语言。这些探索或许在当时看来“离经叛道”,却为后来的紫砂创新埋下了种子。
最让人动容的,是他们共有的“传承自觉”。顾景舟晚年收徒,必让七老轮流授课:蒋蓉教花器的仿生造型,徐汉棠讲方器的线条比例,李昌鸿授铭刻与装饰……周桂珍记得,有次顾景舟带他们去看明代时大彬的古壶,“他说‘我们今天多走一步,后人就能少绕十里路’。”

七老的时代,没有流量,没有炒作,有的只是对技艺的虔诚、对传统的深情,以及对“中国紫砂”的使命感。
顾景舟晚年病重,仍强撑着为“顾景舟紫砂艺术馆”绘制设计图;蒋蓉九十高龄,还蹲在泥凳前教小徒弟“如何让花瓣的卷边更自然”;徐汉棠把工作室命名为“汉棠陶艺馆”,坚持“只传艺,不卖名”……他们用一生回答了一个问题:什么是“大师”?不是身价几何,而是能否让一门手艺,在自己手中活成文化。
如今,七老均已作古,但他们的作品依然在拍场屡创天价,他们的弟子遍布行业,他们的理念融入每一把新壶的基因里。丁蜀镇的老人们说:“从前看壶,只觉得好看;现在看壶,能看出七老的影子——顾老的严谨、蒋老的灵秀、徐老的扎实……”
那个星光熠熠的年代,或许早已远去,但黄龙山的泥还在,龙窑的火还旺,七老用匠心点亮的紫砂之光,正穿过岁月,照亮更多人。
他们是紫砂的星辰,更是文化的灯塔。所谓“紫砂七老”,从来不是一个称号,而是一种精神的坐标——提醒我们:有些光芒,一旦点燃,便永远不会熄灭。(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