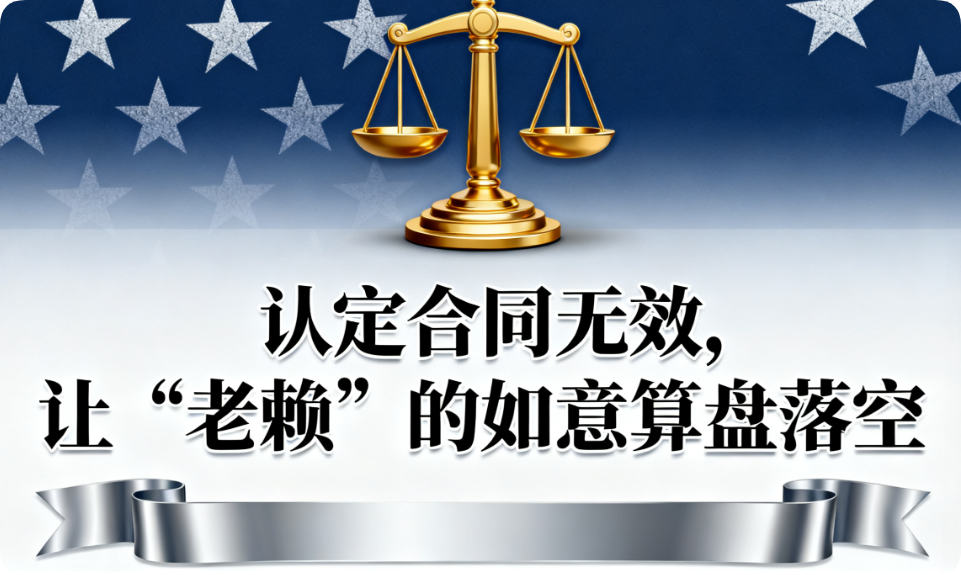
一份白纸黑字、双方签字画押的合同,是否就坚不可摧、神圣不可侵犯?在现代社会,合同是市场经济的基石,是民事主体间意思自治的体现。然而,法律赋予合同效力的前提,是其内容与目的的合法性。当合同沦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工具时,它便如同一件“皇帝的新衣”,无论形式上多么完备,其虚假的本质终将在法律的审视下暴露无遗,并被从根本上否定。
本文将通过一则已经生效的判决(入库案例),深入剖析债务人家庭成员之间如何通过一系列精心设计的“房屋买卖”来试图规避执行,而法院又是如何运用严谨的逻辑推理和法律规则,层层剥茧,最终认定合同无效,让“老赖”的如意算盘落空。
一、【参考案例】:抽丝剥茧,还原“假买卖、真逃债”的真相
以“等价换房”为幌子,行恶意转移财产之实
在“刘某诉程甲等确认合同无效纠纷案”【案号:(2022)京01民终8867号】中,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终审判决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精准打击虚假交易、保护债权人利益的范本。
●案情回顾
债权人刘某因民间借贷纠纷将债务人朱甲诉至法院,并获得胜诉判决,确认朱甲应偿还其本金91万余元及利息。然而,就在该案一审判决作出后不久,一系列围绕房产的“资本运作”悄然上演:
1、债务人妻子卖房给姐姐:债务人朱甲的妻子程甲,将其名下的一套房产(已被另案生效判决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以50万元的价格,“卖”给了自己的亲姐姐程乙,并火速办理了产权过户。
2、姐姐“卖”房给外甥女:几乎同时,程乙也与程甲的女儿朱乙(即债务人朱甲的女儿)签订合同,将自己名下的另一套房产以100万元的价格,“卖”给了朱乙。
3、无资金流水的“交易”:在整个过程中,程甲与程乙之间、程乙与朱乙之间均未发生任何实际的款项支付。她们的解释是,这是一场“等价的房屋互换”。
4、转手后的离婚:完成上述操作后,程甲与债务人朱甲协议离婚,协议中明确约定双方名下“无房产、无债权债务”,意图制造债务人已无财产可供执行的假象。
面对这一局面,债权人刘某果断提起诉讼,请求法院确认程甲与程乙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
●法院的“X光”:虚假交易如何被层层识破
法院的裁判过程,如同一台精密的X光机,穿透了被告方精心编织的“房屋买卖”外衣,直击其“恶意串通”的本质。其论证逻辑严密,层次分明:
1、时间的异常关联性:转让行为恰好发生在债权人刘某与债务人朱甲的官司一审判决之后。这个时间点过于敏感,绝非巧合,而是具有强烈的规避债务执行的动机指向。
2、对价的虚伪与不合常理:被告方辩称的“房屋互换”逻辑上无法成立。真正的互换,应当是程甲与程乙之间直接交换产权。而本案中,程甲的房产给了程乙,程乙的房产却给了第三方——程甲的女儿。这种交易结构不符合正常的市场逻辑,且全程无任何资金往来,进一步印证了价格的虚构和交易的虚假性。
3、当事人身份的特殊性:交易发生在债务人的配偶、姐妹、女儿之间,均为具有重大利害关系的近亲属。在此类主体间进行的非正常低价或无偿转让,是司法实践中重点审查的对象,其恶意串通的盖然性远高于普通市场主体。
4、后果的直接损害性:涉案房屋是债务人朱甲的夫妻共同财产,是其对外承担债务的“责任财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程甲的转让行为,直接导致了可供执行财产的减少,对债权人刘某的合法权益造成了实质性的、直接的损害。
5、陈述的自相矛盾:在法庭上,对于为何将房产登记在女儿名下,程甲在不同诉讼中的解释前后不一(时而称“规避限购”,时而称“避税”),这种无法自圆其说的矛盾陈述,严重削弱了其言辞的可信度,反向印证了其行为的非法目的。
●裁判结果
基于上述严密的逻辑链条,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均认定,程甲与程乙的行为构成恶意串通,损害了第三人刘某的合法权益,其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自始无效。程乙须将房屋所有权恢复登记至程甲名下。
二、【法理深度解析】:为何“恶意串通”的合同自始无效?
本案的判决,根植于我国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和一项核心制度。
●诚信原则:民事活动的“帝王条款”
诚实信用原则是民法典确立的基本原则,被誉为“帝王条款”。它要求所有民事主体在从事民事活动时,应秉持诚实,恪守承诺,公平行事,不得有任何欺诈、恶意规避法律或损害他人利益的行为。本案中,程甲等人利用合法的合同形式,掩盖其逃避债务的非法目的,是对诚信原则的公然违背。
●法律的利剑:《民法典》第154条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五十四条明确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这一条款是认定此类合同无效的直接法律依据。※它包含三个核心构成要件:
1、主观上的恶意:即合同双方明知或应当知道其行为会造成他人合法权益的损害。在本案中,程甲作为债务人配偶,对丈夫的债务情况明知;程乙作为其姐妹,在不支付对价的情况下接受房产,亦难言善意。
2、客观上的串通行为:双方相互配合,共同实施了虚假的房屋买卖和产权转移行为。
3、结果上的损害:该行为实实在在地减少了债务人的责任财产,损害了债权人刘某的合法权益。
当这三个要件同时满足时,法律便给予最严厉的否定性评价——无效。
三、【法律的变迁与衔接】:从《合同法》到《民法典》
本案的法律行为发生在《民法典》生效前,因此一审法院适用了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该条规定与《民法典》第一百五十四条的精神内核完全一致,体现了我国在规制恶意串通、保护第三人利益方面法律精神的一贯性和稳定性。《民法典》的规定,是对既有法律规则的整合与确认,使得法律体系更加清晰、完善。
四、【无效的后果】:“竹篮打水一场空”
合同被确认无效,意味着它从订立之时起就没有法律约束力。根据《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七条,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这意味着:
●物归原主:程乙必须将房屋产权恢复登记到程甲名下,使得该财产重新纳入债务人的责任财产范围。
●状态复原:法律效果上,视为这场交易从未发生过,一切恢复到交易前的状态。
五、写在最后:给社会大众的法律忠告
法律的天平,衡量的是实质的正义,而非形式的伪装。刘某诉程甲等确认合同无效纠纷案,以一个生动的实例向全社会宣告:
1、法律重实质而非形式
不要迷信一纸合同的外壳。法院将穿透形式,审查交易的真实目的与实质内容。任何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行为,终将被法律识破。
2、诚信是最好的“护身符”
面对债务,积极履行、坦诚协商是唯一的正途。任何试图通过转移财产、虚假诉讼等“技术性”手段赖账的行为,不仅徒劳无功,更会带来额外的法律风险和道德谴责。
3、亲情不是违法行为的“挡箭牌”
协助亲属恶意转移财产,同样是违法行为。这不仅无法真正帮助亲人,反而可能将自己卷入不必要的诉讼之中,得不偿失。
归根结底,法律为诚实守信者保驾护航,也为虚伪失信者布下天罗地网。尊重规则、敬畏法律,方是个人与社会行稳致远的根本之道。
(免责声明:本文仅为基于法律规定及公开案例的个人解读和普法分享,不构成法律意见。由于个案情形千差万别,如遇具体法律问题,请咨询专业律师。)
【更多细节】请参阅原文
原文出自:微信公众号【法律知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