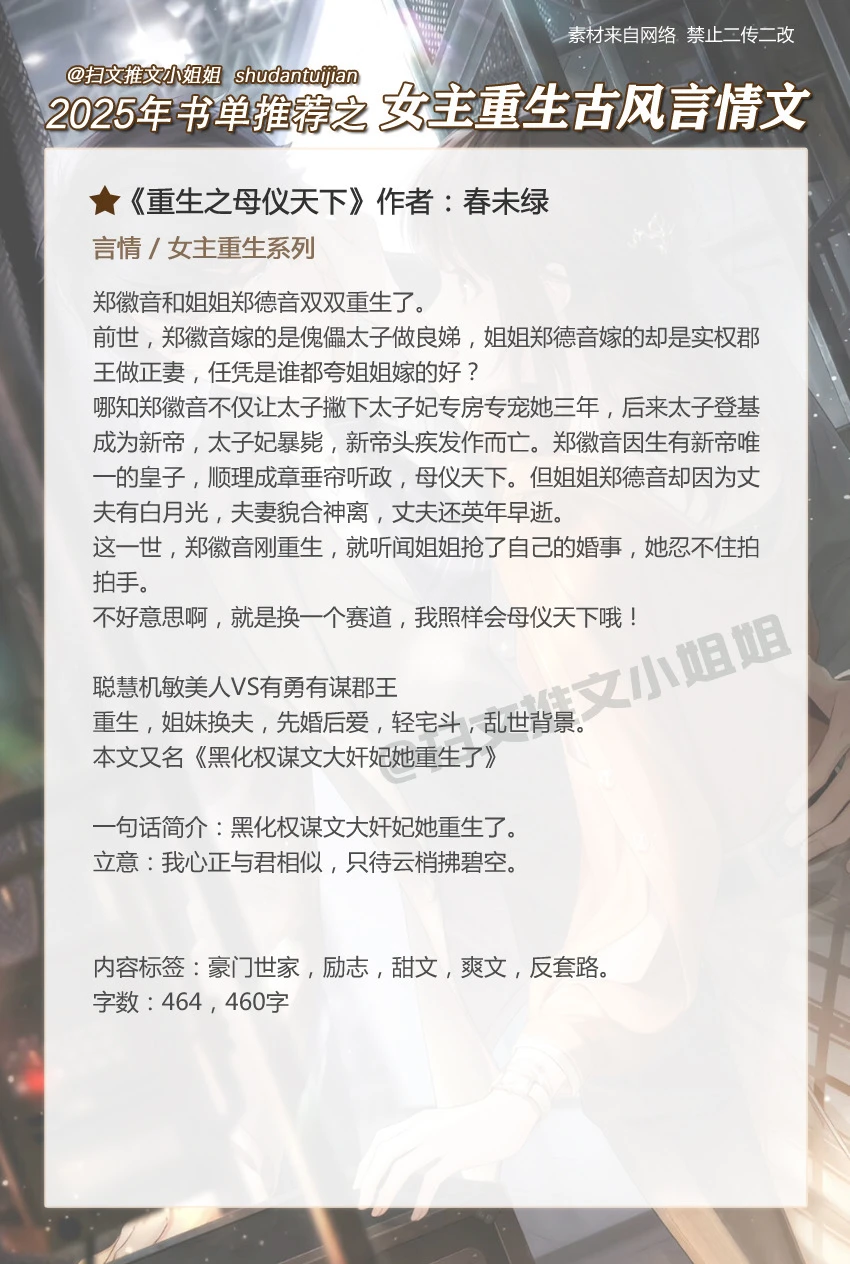兄长来接我时,我正趴在营帐中的脏污草席上。
武将朝着我啐了一口,
“真他娘的晦气!”
说着顺手拎起军棍,重重砸向我的后腰。
我猝不及防,痛苦的闷哼溢出嘴角。
那武将被我的反应取悦。
“再多叫几声我听听。”
三年前,哥哥为给真千金裴婉儿出气,将我打断筋骨送入边疆磨砺。
从此,我成了不堪的存在。
这三年的屈辱彻底碾碎了我对亲情的妄念,却没磨灭我的求生欲。
就在这人越来越过分时,营帐的帘子被掀开了,
“裴饮溪,裴小将军来接你了。”
1
我恍惚抬头,还以为自己听错了。
直到穿着旧袍子被送到营帐门口,看到那架熟悉的马车时心脏终于再次泛起了刺痛。
三年前,裴婉儿作为真千金被高调的接了回来后,我这个假千金就几乎没有一天的好日子过。
虽然爹娘和兄长都曾承诺,即便我非他们亲生,但情分依旧。
可不过三月,裴婉儿就弄破了父亲的兵书,嫁祸给我。
他们一致称,裴婉儿柔弱,我却从小沉迷武功,这必然是我所为。
裴墨宸执鞭当众将我抽得遍体鳞伤,又给我灌下一碗药,废了我的武功。
父亲当时冰冷的话言犹在耳:
“你那三脚猫功夫却确实有辱我裴家名声,既然那么喜欢,就从头开始吧。”
然后,他们毫不留情地将我扔进这北境炼狱,让我体会真正的军纪。
从那天开始,我就沦为了后营里最低贱的奴隶。
操练场上,我被当成了人肉沙包,演习赛上,我又成了敌国俘虏。
本就残破的身子更加脆弱,身上也留了无数伤口。
又因为我是女子,更有无数人借着各种理由试图羞辱我。
我的身体遍布鞭笞、烙印与各种刑求留下的伤疤。
若在三年前,兄长策马而来,说要接我回家,我定会泣不成声,扑向他诉说所有委屈。
只是这三年血肉模糊的教训早已刻入骨髓。
我深知,他,他们,都已不是我的归处。
我低着头挪到马车离他最远的位置,低声开口:“有劳裴小将军亲临。”
裴墨宸眉头骤然锁紧,语气不悦:
“我是你兄长!三年戍边,如今连人都不叫了?”
我怔了片刻。
是了,他是我唤了十五年的兄长。
曾在我病榻前不离不弃,也曾手把手教我挽弓,赞我箭术精准。
可后来,也是他明知不是我所为,却还是把我丢到这里不管不问三年。
裴墨宸并未等我回话,而是继续冷声开口:
“这三年了,你可知错了?”
我指节收紧,唇瓣轻抿。
知错?悔改?
我错在何处?
错在不是裴家亲生却占了裴婉儿十五年的位置?
错在她栽赃时我没有跪地认罪?
错在我曾天真地以为十五年的亲情能与血脉比肩?
我的沉默激怒了他,他一把打翻了杯盏:“果然冥顽不灵!”
“家族养你十五年,锦衣玉食,即便你铸下大错,也只是小惩大诫,送你至此磨去劣性!你不知感恩,反倒心存怨怼?”
“既然你死不悔改——”
他抬起脚,狠狠踹在我心口。
我整个人摔出马车帘子,直接掉进桥下冰冷刺骨的河水里。
河水疯狂地涌入耳鼻,窒息感扼住喉咙。
最后听到的,是他厌弃的骂声,
“自己不上道,就别怪我不念旧情!”
2
冰冷的河水刺透粗布袍,肺腑间的空气被挤压出去,腥甜的液体涌上喉咙。
求生的本能压倒了一切。
我在湍急的河流中挣扎,不知过了多久,我才从下游一处浅滩艰难地爬上岸。
可裴府还有我不得不拿的东西,于是我咬着牙一步一顿地朝京城的方向走去。
天色微亮时,我终于走到了裴府那朱漆大门前。
这本该是我家的地方。
门房看到我,先是惊疑,待认清是我,脸上立刻露出毫不掩饰的鄙夷。
仿佛我是什么不洁的秽物,此时竟敢玷污裴府的门楣。
他没拦我,也没通传,只厌恶地别开眼,任由我踉跄着自行入内。
穿过庭院,还未进正厅,便听到里面传来阵阵温软笑语。
前厅里,母亲与裴婉儿正并肩而坐,母亲正往她嘴里喂蜜饯。
裴墨宸也含笑在侧。
他看到我,竟然装出一幕好人嘴脸:“妹妹回来了,一路上可还顺利?”
他转头对母亲解释:
“妹妹说在军中修炼成果甚佳,主动请缨步行回府,我便也顺了她的意思。”
我没有理会他,只站在大厅微微颔首:“裴夫人。”
母亲怔了一瞬,旋即蹙眉:
“你喊我什么?我是你娘亲啊……”
我没有回应,只是盯着她怀中温顺依偎的裴婉儿。
那才是她真正的女儿。
而我,不过是个不知好歹的外人。
母亲眼中含泪:“饮溪……你还是在和我们赌气吗?”
“就算你不是我亲生,我也说过,你永远是我的……”
我打断她:“裴夫人,您的亲生女儿正在您怀里。我再称呼您为娘亲,于礼不合,于情也不妥。”
裴婉儿闻言,眼眶立刻泛红,挣开母亲的手走到我面前。
“姐姐,别这样啊……”
“我们是一家人,你何苦说这些生分的话?娘亲会伤心的。”
她伸手覆上我肩头,假意惊呼:“呀,姐姐,你的衣裳怎么都湿透了?”
她声音娇怯,指尖却精准地掐进我手臂上一处刚刚结痂的烙伤。
我疼得倒抽一口冷气,下意识缩手想要挣脱。
但下一刻,她便往后一仰,一屁股摔倒在地。
她难以置信地仰头看我:
“姐姐……你为什么推我?我只是想劝你不要生娘亲的气……”
“我知道你不喜欢我,想赶我走,可是,可是我不能没有爹娘和哥哥啊……”
“婉儿!”裴墨宸一个箭步冲上前,小心翼翼地将裴婉儿扶起,
看到她手肘处擦出的红痕,立刻转头瞪我,那眼神恨不得将我生吞活剥:
“裴饮溪,你这个贱人!婉儿好心安慰你,你竟敢对她动手?”
根本不容我分辩,他扬手便是一个耳光扇来。
我被打得头一歪,嘴角溢出血丝。
我还未来得及站稳,他已抬脚踹在我小腹。
我本就虚弱不堪,再也支撑不住,蜷缩着倒在地上,五脏六腑仿佛移位般绞痛。
他怒骂:“裴家养你十五年,你狼心狗肺,恩将仇报!”
“我们好心接你回家,你呢?”
母亲也起身,手忙脚乱地去扶地上的裴婉儿:
“婉儿莫哭,别怕,你姐姐只是心性不稳……不敢真害你的。”
说着,她冷冷地瞥了我一眼。
“她总不敢违抗她父亲。”
裴婉儿依偎在母亲怀中,梨花带雨地抽泣着:
“我没事的……都是我不好,惹姐姐生气了……”
话是宽慰,可她眼尾余光扫过我时,却闪过一抹胜利的笑。
这一幕,何其熟悉。
三年前,是她弄破兵书,泪眼汪汪地假装替我说话,说我不是故意的。
三年后,她依旧用同样的伎俩。
更可笑的是,这一家子人照单全收。
我伏在地上,拼命地咳嗽,血沫点点溅落在地上。
我的下体更是旧伤未愈,被裴墨宸这一脚踹得伤口破裂,鲜血流出来染红了衣衫。
裴墨宸看到地上的血,脸色微变:“你……”
但裴婉儿抢先说:“啊呀,姐姐这是来月事了吧?”
裴墨宸的担忧只出现了一瞬,便又换上了冷峻的表情。
就在我以为自己快要昏死过去的时候,厅外传来脚步声,以及一声轻笑。
“裴将军府上,今日倒是热闹。”
我听到这声音,心脏骤然一紧。
父亲不知何时站在了门口,而他的身旁,立着一个身着玄色暗纹锦袍的男人。
看到他,巨大的惊恐瞬间冻结了我所有的感官和思维。
他怎么会在这里?
怎么会出现在京城?出现在裴府?
3
父亲跨入厅堂,目光落在我狼狈的身影上。
“裴饮溪,你回府第一日便闹得鸡犬不宁,这就是你的礼数吗?”
“不成体统!还不快起来!”
裴墨宸立刻上前一步:
“父亲息怒,顾将军勿怪。不过是小妹任性,欺负婉儿。为兄稍微给了她一点教训而已。”
他边说,边警告地瞪了我一眼。
男人轻笑一声,缓步上前,弯下腰朝我伸出手来:
“饮溪姑娘,你还好吗?”
那只骨节分明的手就悬在我眼前。
记忆中,这只手曾慢条斯理地用匕首划开我的衣衫,
曾轻佻地抬起我的下巴,逼我咽下混着沙土的馊饭,
曾握着马鞭,欣赏我如何在他的命令下被拖行得血肉模糊……
我记得他笑着压下我头颅时的冷语,记得他羞辱我时的残忍。
他是这三年里我最不愿再听见名字的人。
顾云。
可如今,他竟堂而皇之地出现在京城,在裴府,在父亲身侧。
“不……别碰我!”
我失声尖叫,狼狈地后退几步。
父亲脸色一沉,厉声呵斥:
“饮溪,你这是做什么?顾将军好心相扶,你竟如此失礼!”
我浑身颤抖:“他……他对我……”
顾云直起身笑道:
“无妨。裴小姐在北境三年吃了不少苦,性子烈些,也是常情。”
父亲面色歉疚:“让顾将军见笑了。”
“这孽女在北境,多亏了将军看顾教诲,否则还不知要野成什么样子。”
母亲眼角也挂着泪:“三年辛苦,若不是顾将军相护,你怎能活着回来?饮溪,你可懂得知恩图报?”
我身子一僵,脑海嗡嗡作响。
他们在说什么?恩人?
裴墨宸施恩一般看向我,轻笑道:
“裴饮溪,你现在知道了吧?爹娘虽然表面上把你送去军营,但心里是牵挂着你的。”
“婉儿特意安排了顾将军关照你。”
“再看看你,一进门便对我们横眉立目,我们真是白疼了你。”
我浑身冰冷,胃里翻江倒海。
那些暗无天日的折辱,那些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管教……
竟然是他们特意安排?
这就是养育我十五年的亲人?家人?
顾云对爹娘拱手道:
“裴大人,裴夫人。三年风雪,饮溪姑娘不免心性执拗,但她也有她可爱的一面。”
“顾某愿纳饮溪姑娘为妾,对她负责到底。”
妾?负责到底?
顾云的暴戾和荒淫,谁人不知?
他的后院里,抬进去多少女人,又能有几个活到今日?
被他看上的女子,要么是玩腻了赏给下属,
要么是稍有忤逆便被打断腿扔进营妓帐中。
更有甚者,只是因为他醉酒后心情不佳,便被活活鞭挞至死,草席一卷丢去了乱葬岗!
现在,他居然要娶我?
父亲紧绷的脸色缓和了些许,他讨好地看着顾云:
“顾将军愿纳了小女,是她的造化。只是这丫头顽劣不堪,怕是会辱没了您……”
“裴大人过谦了。”顾云笑得温文,“饮溪姑娘的‘好处’,顾某深知。”
母亲用帕子按了按眼角,欣慰笑道:
“饮溪啊,顾将军肯要你,这是天大的恩典啊。”
她转向父亲,软声道:
“老爷,虽说为妾,但终究是咱们裴家嫁女,场面也不能太难看,便以义女的名份出嫁吧。”
“我再拨出五匹锦缎,两副头面,风风光光地送她出门,也算全了我们一场母女情分。”
五匹锦缎?两副头面?
他们把我折磨得体无完肤,毁了我的一生,
如今竟想用这微不足道的施舍,把我塞回顾云的魔窟,还要摆出施恩的嘴脸?
我直直瞪着父亲,咬牙道:“我不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