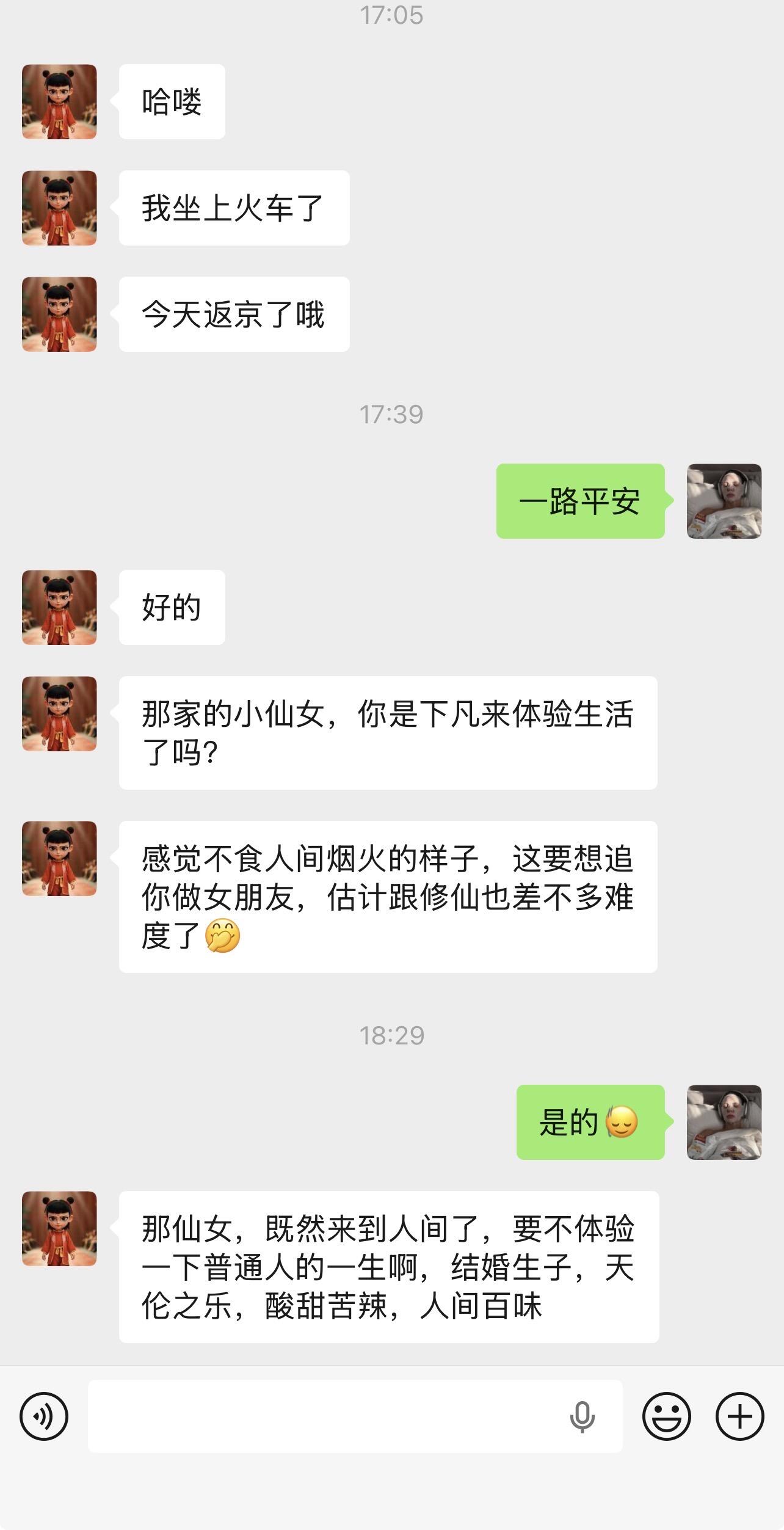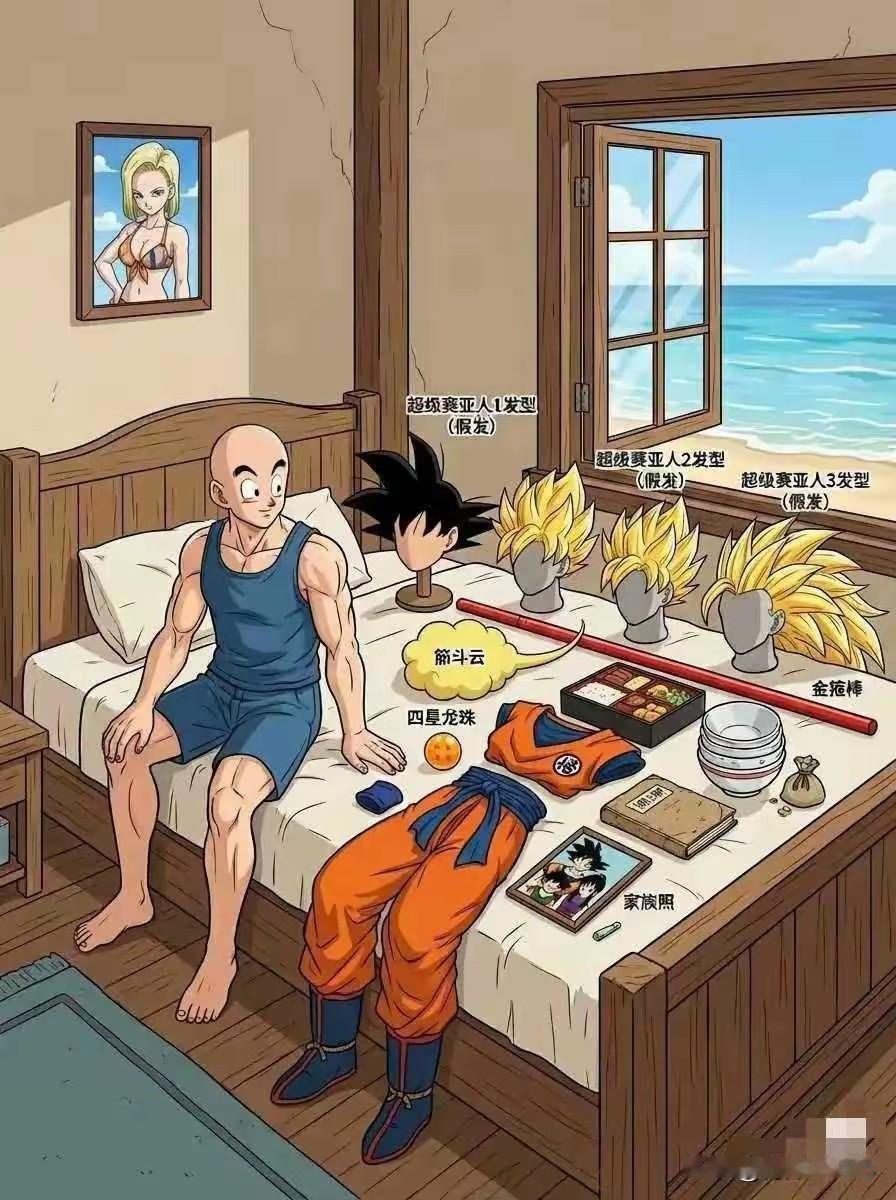长子崇庆寺的青砖缝里,藏着明嘉靖二十七年的风。那年工匠们带着凿子和泥塑,在十帝殿里一凿一捏,把人间帝王的影子揉进了阴曹的神台。如今推开那扇吱呀作响的木门,十六尊彩塑在幽暗里立着,身上的颜料褪了层皮,却依然能看出当年落笔时的力道。

佛坛正中的地藏菩萨最是沉静。他披的袈裟不是庙里常见的明黄,而是暗赭色,像被香火熏了几百年。衣褶垂下来,不是刻意堆出的飘逸,倒像真的有重量,压得菩萨的肩膀微微沉着。右手捏着的锡杖头生了层绿锈,可杖杆挺得笔直,穿过袈裟的褶皱,像根定海神针。这尊像不笑,也不怒,眼皮垂着,好像在看脚边的蒲团,又好像在看更远的地方——那些跪在蒲团上求告的人,大概从没想过,菩萨的目光里藏着工匠的心思:把慈悲捏得这样克制,才更像见过生死轮回的模样。


环墙的神台上,十帝阎君各占一方。他们不穿戏文里的蟒袍,官服的颜色透着股旧气。秦广王的红袍袖口磨出了白边,像穿了几十年的老衣裳;楚江王的紫袍上绣的不是龙凤,是些说不出名字的纹样,针脚粗粝,倒比精致的绣品更显实在。最特别的是五官,没有一尊是标准的“帝王相”。有的眉骨突出来,眼窝陷着,看人时带着股狠劲;有的脸颊肉坠着,下巴圆滚滚的,倒像邻村那个爱琢磨事的老秀才。后来才知道,这些脸都是有来头的——工匠们偷偷把唐宋明清的帝王模样拆了,再按阴司的规矩重新拼。就说那个五官周正的宋帝王,鼻梁挺直,嘴唇抿着,像极了史书里写的宋仁宗,可眼角那道细纹里,又多了点判官的冷。

六曹判官站在阎君身边,更像一群办事的老吏。他们的官帽翅是硬的,斜斜插在脑后,像是刚从案牍前抬起头。有的手里攥着竹简,竹简边缘被捏得发亮,上面的字模糊了,可能看出刻得极深,一笔一划都透着股较真。有个判官的手指关节突着,指甲缝里还留着点泥色,大概是捏泥塑时,工匠顺手按上的自己的影子。他们不看阎君,也不看香客,都盯着自己的差事:管户籍的盯着竹简,管刑罚的摸着腰间的令牌,连站在最边上的那个,都在低头整理袖口,好像下一秒就要转身去翻卷宗。


最让人挪不开眼的是头顶的悬塑。工匠们没在梁上画云彩,而是直接捏出了层层叠叠的阴曹景象。黑灰色的泥塑堆出城墙的垛口,垛口后站着些小泥人,有的举着刀,有的拖着锁链,都是寸把高,可姿态里全是劲。城楼下有个小小的奈何桥,桥板歪歪扭扭,像被人踩了几百年。桥边的鬼卒没有青面獠牙,就是些瘦骨嶙峋的模样,胳膊腿细得像柴禾,可抓着锁链的手,指节捏得发白。这些悬塑离地面高,得仰着头看,看久了脖子发酸,倒像是真站在了阴曹的城楼下,得低着头才能过那座窄桥。

彩塑身上的颜料是真材实料。红的是朱砂调的,黑的掺了松烟,白的里混着铅粉。几百年过去,朱砂褪成了暗红,松烟黑得发乌,只有铅粉还亮着,在阎君的帽翅尖、判官的腰带扣上,透着点冷光。有尊阎君的胡须是真的麻丝做的,现在断了几根,垂下来搭在衣襟上,像老先生没梳好的胡子。这些细节没人特意维护,就这么带着残缺立着,倒比那些新刷了漆的佛像更让人心里发沉——原来神仙鬼怪,也和人一样,会老,会旧,会带着岁月的疤。


殿里的光线总不太好,太阳斜着照进来,只能在地上投块亮斑。光斑移过阎君的靴底,移过判官的衣摆,最后落在地藏菩萨的锡杖上。这时才能看清,锡杖上刻着极小的字,不是经文,倒像句口诀:“泥胎塑骨,人心定魂”。想来当年工匠刻下这话时,手里的凿子定是抖了一下,不然那“魂”字的最后一笔,不会拖得那么长,像条线,一头连着泥塑的身,一头牵着看客的心。

来这儿的人大多直奔大佛殿,觉得十帝殿里的阴曹景象不吉利。可那些真正懂行的,会在殿里多站会儿。看阎君眼角的皱纹怎么随着光线变深,看判官手里的竹简怎么在风里轻轻晃,看悬塑里的小泥人怎么被烟尘遮了半张脸。这些彩塑从不会说话,可站得久了,能听见嘉靖二十七年的锤子声——一下,又一下,敲在青砖上,也敲在人心上。

出殿时再回头,十六尊像在暗处立着,像一群守着秘密的老人。他们见过明清的香客,见过民国的兵匪,见过现在举着手机拍照的游人。身上的颜料掉了就掉了,麻丝断了就断了,反正那点从人间帝王身上借来的风骨,早被工匠捏进了泥里,成了比颜料更经得住时间的东西。这大概就是十帝殿的妙处:它不装神弄鬼,就把人间的模样拆了,重组成阴曹的样子,让每个进来的人,都能在那些泥塑的眉眼间,看到点自己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