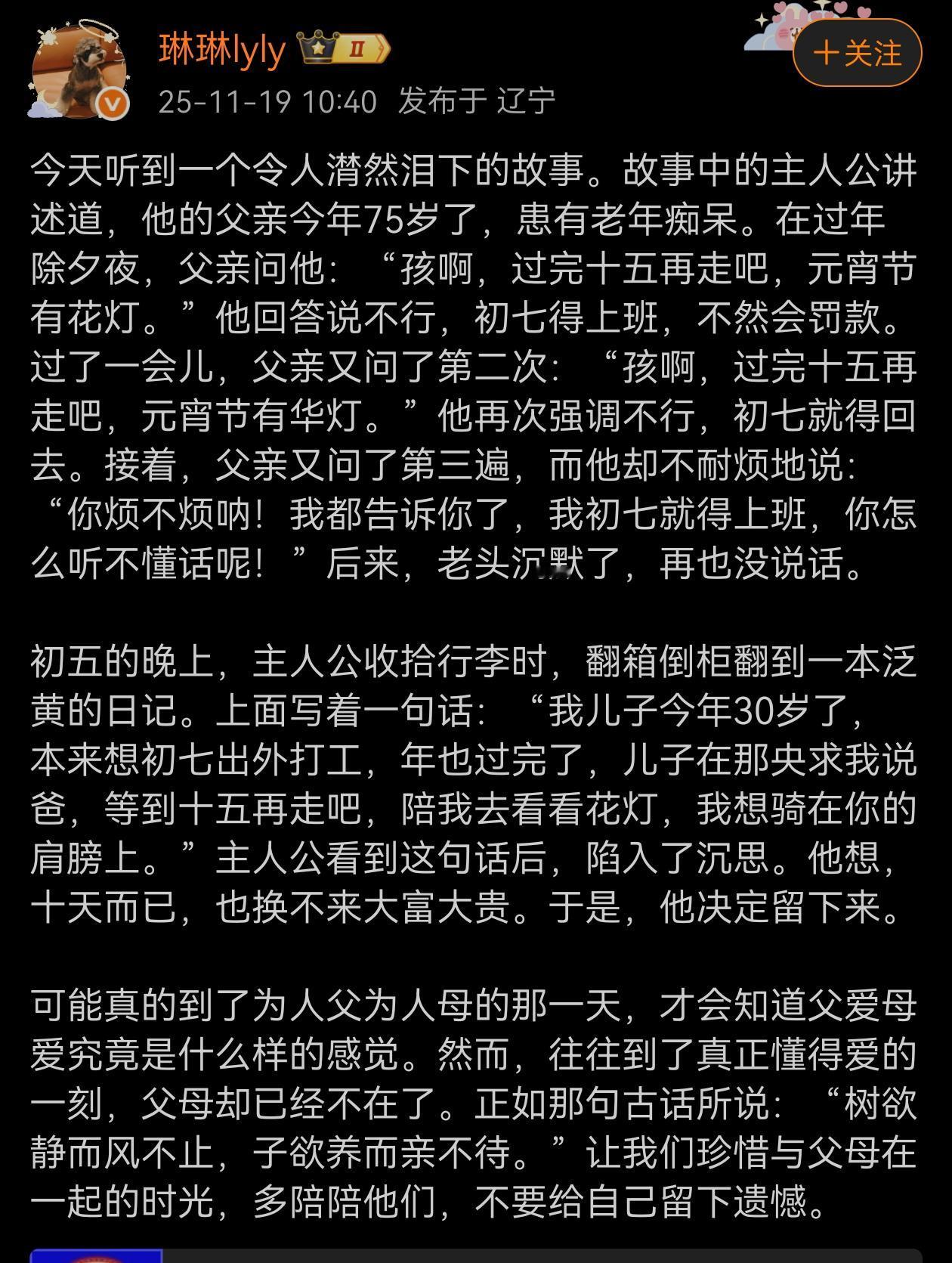元贞年间的崖州,晨露还沾在木棉叶上,黄道婆的纺车已经转了起来。她坐在竹编的蒲团上,右腿踩着踏板,木质的纺车轴发出嗡嗡的轻响,像崖州海边的风。左手捏着棉絮,右手摇着纺锭,三缕银丝般的棉纱从指尖绕出,缠在锭子上 —— 那锭子是她用硬木削的,比当地黎家织女的多了一锭,脚一踩,三个锭子一起转,棉纱出得比从前快了两倍。

她的手指关节粗大,指腹上的茧子厚得能磨破棉絮,那是几十年织出来的。有片棉絮粘在她的袖口,白得像崖州清晨的霜,她没在意,眼睛盯着锭子上的棉纱,生怕哪一缕断了。旁边的黎家阿婆端来陶罐装的凉茶,笑着说:“阿婆,您这手艺,连天上的织女都要学哦。” 黄道婆停下摇柄,接过陶罐,指尖碰着冰凉的罐壁:“不是我手艺好,是这工具得改。你看,原先一锭纺车,一天纺不了半斤棉,现在三锭,能纺两斤,乡亲们就不用再穿露肉的粗布了。”

她想起二十年前逃到崖州的那个晚上。那时她还是乌泥泾的童养媳,婆家待她苛责,天不亮就要舂米、织布,织不出布就用藤条抽。那天她织坏了一匹土布,婆婆把她关在柴房,没给一口饭。夜里她撬开门缝,揣着一把剪布的铁剪子,跟着赶海的船家逃了出来。船在海上漂了三天,她趴在船板上,看着海水从黑变蓝,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要找个能好好织布的地方,再也不挨冻受饿。

船到崖州时,她身上只剩那件打补丁的粗布衣。黎家寨的织女阿珠看见她,把她领回了家。阿珠教她用 “捍弹纺织之具”—— 捍是轧棉的木杖,弹是弹棉的弓弦,纺是单锭纺车,织是提花的布机。第一次摸到弹棉花的弓弦时,黄道婆的手都在抖,弓弦一拉,棉絮飞起来,落在她的头发上,阿珠笑她:“你这北方来的姑娘,倒比我们黎家人还爱棉。” 她当时没说话,只是把棉絮拢得更紧 —— 在乌泥泾,她从没见过这么软的棉,这么好用的工具。

接下来的十几年,她跟着阿珠学遍了崖州的纺织手艺。看到黎家织女纺棉时要一手摇锭、一手喂棉,忙得顾不上擦汗,她就想:能不能多装个锭子?她试着用硬木削了双锭纺车,可摇起来太费劲,棉纱总断。有次她看见阿珠用脚踩踏板舂米,突然想起:能不能用脚踩踏板带动纺锭?

她找了村里的木匠,让他在纺车下面装了踏板,连在纺轴上。第一次试的时候,踏板踩下去,纺轴转得太快,三个锭子歪了两个,棉纱缠成了一团。木匠挠着头说:“阿婆,这不行,脚哪有手灵活?” 黄道婆没灰心,把纺轴改细了些,又调整了踏板的长短,每天天不亮就试,手上被纺锭磨出了血泡,就用布条缠上。试到第二十三天,踏板踩下去,三个锭子稳稳地转起来,棉纱顺顺当当绕在上面,她坐在纺车前,眼泪突然掉了下来 —— 这一下,乡亲们织布就快多了。

元贞元年,黄道婆听说乌泥泾还是老样子,乡亲们靠种棉织布为生,可工具落后,织出的粗布又硬又厚,冬天不保暖,夏天不透气。她收拾了行李,带着改良的纺车图纸、轧棉的木捍,还有一把用了十几年的弹棉弓,踏上了回松江的路。

回到乌泥泾时,村里的老房子大多还在,只是更破了。她找到当年的邻居王阿婆,王阿婆见她回来,又惊又喜:“道婆?你还活着!这些年你去哪了?” 黄道婆拿出纺车图纸,铺在王阿婆的破桌上:“我去了崖州,学了好手艺,咱们把纺车改了,以后织布快,布也软和。”

可村里的织户们一开始并不信。有个叫李大叔的织户,拿着自己的单锭纺车说:“道婆,咱们祖祖辈辈都用这纺车,改了要是织坏了布,一家子吃什么?” 黄道婆没辩解,第二天就找木匠做了一架三锭脚踏纺车,在村里的晒谷场上演示。她踩着踏板,纺车转起来,三个锭子同时出纱,不到半个时辰,就纺出了一斤多棉纱,比李大叔用单锭纺车一天纺的还多。李大叔凑过来,摸了摸纺出的棉纱,软得像云:“这…… 这真能行?” 黄道婆笑着说:“你试试,踩习惯了,比用手摇省力。”

她还教大家用轧棉的木捍 —— 原先轧棉要用手剥,一天剥不了几斤,木捍一轧,棉籽就掉了,效率快了十倍。又教大家弹棉的技巧,用粗弦的弹弓把棉絮弹得蓬松,织出的布就软和。《南村辍耕录》里后来写这事:“人既受教,竞相作为,转货他郡,家既就殷。” 说的就是当时的情景 —— 乌泥泾的织户们学会了新手艺,织出的布又软又细,卖到苏州、杭州,家家都赚了钱,再也不用穿露肉的粗布了。

有次她去镇上的布庄,看见掌柜的拿着乌泥泾织的棉布,跟客人说:“这是黄道婆教织的布,比松江府里的官布还好!” 她没上前,躲在街角看着,心里又暖又酸 —— 想起当年在柴房里挨饿的日子,想起在崖州海边学织布的夜晚,现在能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值了。

晚年的黄道婆,还在琢磨改进织布机。她的屋里放着好几架不同的织机零件,有她削的木梭,有改的综线,还有一块画满花纹的布样 —— 她想织出带花的棉布,让乡亲们穿得更体面。有天夜里,她坐在纺车前,手指摸着冰冷的纺锭,突然想起婆家的柴房,心里竟有点恍惚:要是当年没逃出来,现在会是什么样?可马上又摇了摇头 —— 要是没逃,就遇不到阿珠,学不会手艺,乡亲们也穿不上好布。她拿起旁边的弹棉弓,弓弦拉了拉,还是那么有劲儿。

她去世后,乌泥泾的乡亲们为她建了祠堂,把她的三锭纺车、弹棉弓供在里面。后来松江成了全国的棉纺织中心,人称 “衣被天下”,很多织户都说是黄道婆给他们带来了好日子。
现在的松江,还有非遗传承人在学黄道婆的纺织手艺。有个年轻的姑娘,拿着复刻的三锭脚踏纺车,踩着踏板,纺车转起来的声音,和几百年前崖州的那架纺车一模一样。姑娘的手指上也开始长茧,她摸着茧子说:“黄婆婆当年织出的不只是布,是让老百姓能暖衣饱食的希望。”

就像崖州的木棉每年都会开,黄道婆的手艺也没断过。她的纺车,她的木捍,她指腹上的茧子,都成了布衣里的温度 —— 那温度,从元贞年间的崖州棉田,传到松江的织户家,再传到今天的非遗工坊,暖了一代又一代人。她这辈子没留下什么诗,没做过什么大官,可她用一架纺车,把 “衣被覆苍生” 的心愿,织进了每一寸棉布里,比任何文字都长久。
![榜一大哥该哭死在卫生间了吧是一个人吗?网红原来是人贩子[捂脸哭]](http://image.uczzd.cn/12083804139537505745.jpg?id=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