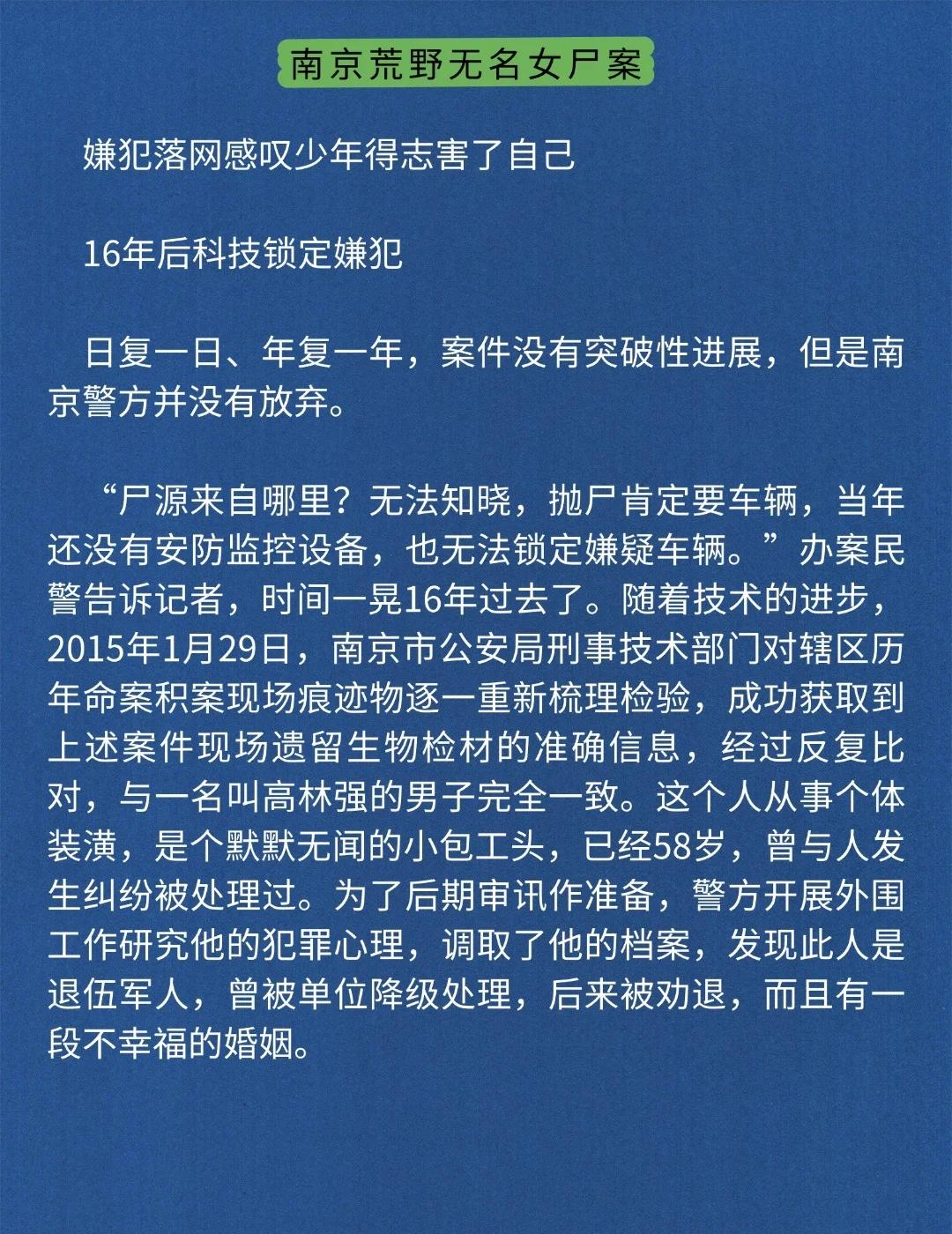金陵论道
晨雾未散,江南的钟声悠悠传来。金陵城外,云气浮动,一僧缓步而行。
他身披红袈裟,鬓发微白,目若澄泉。此人,乃自天竺而来的高僧——菩提达摩。
一路行来,尘不染衣。他闻梁地佛法昌盛,王者笃信三宝,遂欲以“禅宗”之法度人,以“明心见性”之道启世。
梁武帝闻其名,欣然召见。

那日,金殿香幕高垂,金灯如昼。梁帝披轻纱袍,目带敬诚,问曰:“朕即位以来,造寺数千,写经万卷,度僧无数。尊者以为,朕之功德几何?”
达摩合十,低眉答道:“陛下,此无功德。”
帝心一震,声色俱厉:“无功德?何出此言?”
达摩平声言道:“陛下所行,不过人天小果。真功德,非筑塔写经,非施舍供养;功德在心,明心见性,不住于相。若求相中之功,终为空耳。”
殿中静极。梁武帝神色微黯。他一生虔诚所为,竟尽属空相?
良久,帝抬手一挥,淡淡道:“尊者既有此志,不妨另寻有缘之地传法罢。”
达摩合十而立,眼神宁然如海:“善哉。”
转身之际,袈裟轻扬,宫门外的风,似为他送行。

江上孤影
离金陵数十里,江水浩荡,浪光万顷。
达摩立于岸边,天色沉沉,雁阵南飞。船夫避风浪,不肯启行。
老船夫拱手劝曰:“尊者,今日之水,不宜渡也。”
达摩不语,只凝望北岸。那一片山河,云烟苍茫,正是北魏之地——或许,佛法真种当在彼方生根。
风过衣袂,尘念微起。
他俯身,看见岸边一株芦苇,在风中轻摇。芦苇柔弱如丝,却立于波畔,不折不沉。
达摩微微一笑,轻语道:“缘起于心,舟亦由心。”
指尖轻拈,摘下一叶。
随手一掷,芦苇入水,不沉不漂,微光流转。
达摩阖目而立,步上水面。
浪起,风啸,天地苍茫。而他衣袂不动,神色安然。
一叶芦苇,载一僧身,如青鸟浮水,缓缓北去。江波映红天际,夕阳如血。船夫呆立良久,忘了呼吸。
世人只见那僧人立于苇上,渐行渐远,直与天一线,终隐于云烟。

少林面壁
北上之途,风雪漫天。
达摩至嵩山,寻得一洞,名曰“面壁洞”。洞外松影如铁,洞中石冷如骨。
自此,他静坐九年。
九载光阴,草木荣枯,云月更替。冬雪压松,春水复涨。
山中人见之,或惊或叹:“祖师何思?”旁僧答曰:“思无所思。”
九年之后,一僧名慧可至,立雪请法。寒风割面,冰雪覆身,而其志不退。
达摩不言。
慧可咬牙割臂,以血为诚。
达摩方开目,叹曰:“汝已得我心。”遂传以衣钵,道曰:“吾法以心传心,不立文字。”
自此,禅宗之火,于中土初燃。
江上之悟
岁月流转,江月依旧。
少林山脚,一老僧夜行,偶见月色洒水,心忽有所感。
他忆起昔年,一叶芦苇浮江之景。
那并非神迹,那是“心定则水平”的化现。
若心如镜,无风可扰;若道在心,何须舟渡?
江流不息,世事如浪。唯有一念真心,方能渡己,亦能渡人。

碑下江声
后人于江畔立像,镌刻四字:一苇渡江。
碑下草长莺飞,江水依然东流。
千载之后,行人立于岸边,凝望那无形的渡口。
有人叹曰:“大师渡江,乃神迹也。”亦有人轻声道:“大师所渡者,岂是江水,而是尘心。”
《江不止流,法不止传》
江有涯而心无涯,水东流而道常在。达摩一渡,非越波涛,乃越尘念;一苇之轻,载万古之悟。
后世传灯不息,法脉流行,虽隔千载,犹闻江声。世人或记其迹,而忘其心;然心法一线,明如秋月,湛若止水。
江仍东去,风仍南来。行人立于岸畔,若能自省一念,则此江,不复为隔;此岸,已是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