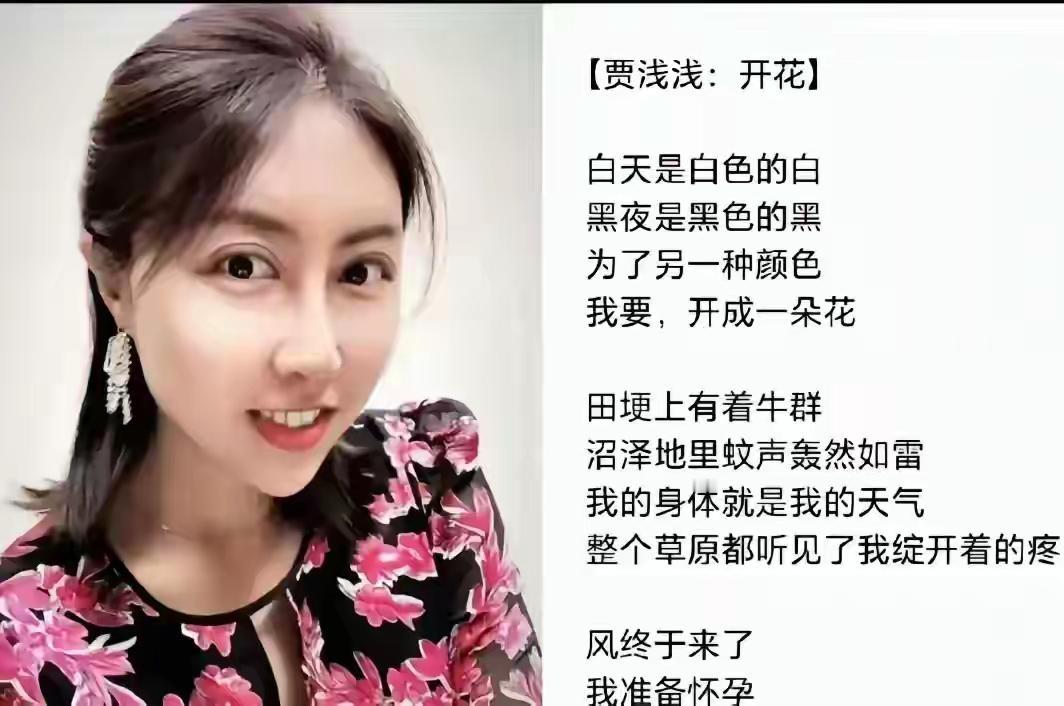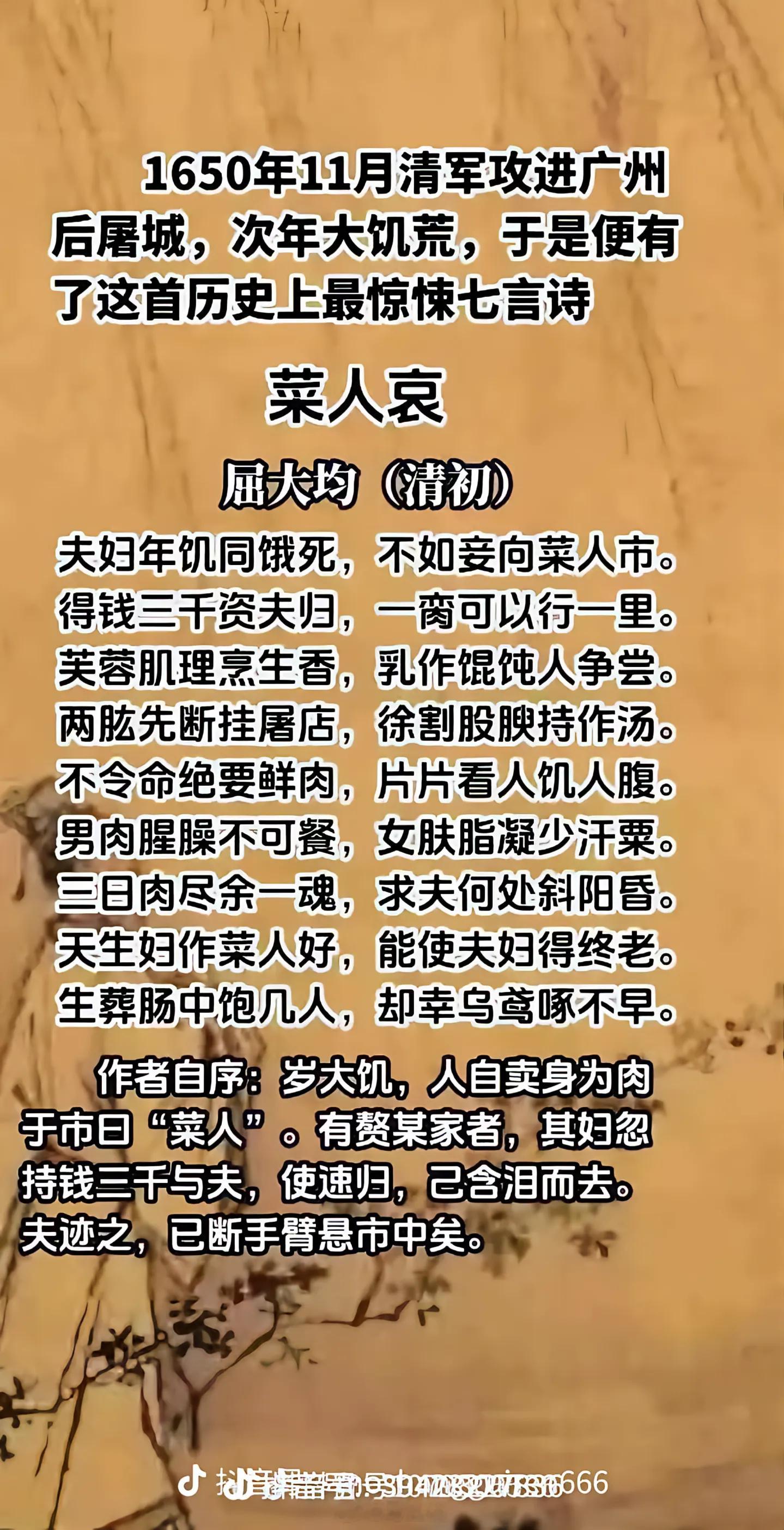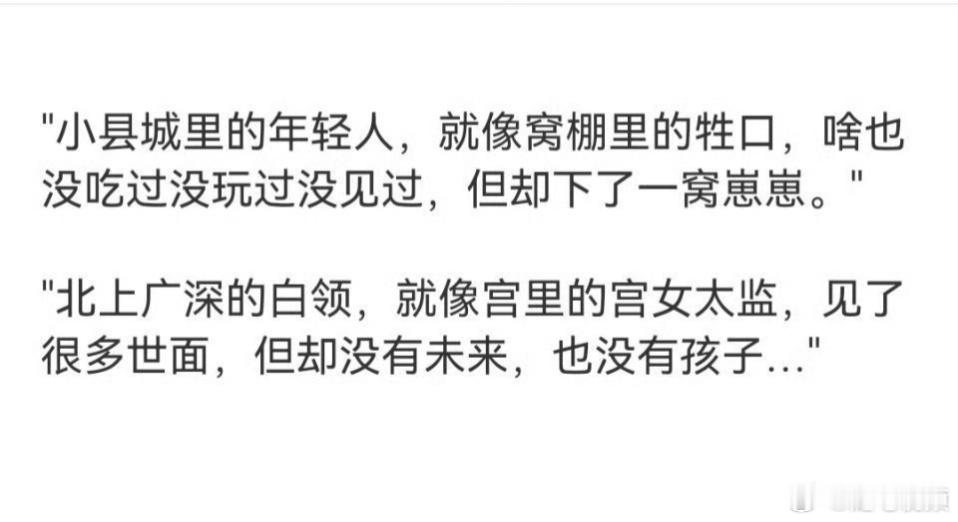黄帝时代的黄土坡上,仓颉的腰上总系着一串绳结——大结记大事,小结记小事,打猎的收成、部落的盟约全在这绳上。可某天暴雨冲垮了绳堆,半年的狩猎记录全乱了,老人急得直拍大腿:“绳结断了,日子就像断了线的风筝。”《说文解字序》里写“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这便是仓颉造字前,先民困在“无文”里的真实模样。
作为黄帝的史官,仓颉揣着断绳走遍部落。他见猎人循着兽蹄足迹追猎物,忽然顿悟:“鸟兽的脚印各有不同,若能为万物画‘脚印’,不就能记下一切?”他蹲在地上,照着山鸡的爪印画了三笔,又摹着野兔的豁唇勾出曲线,部落里的人一看就懂:“这是山鸡,那是兔子!”
从此他成了“追着万物画符号的人”:看太阳东升,便画个圆圈加道射线代表“日”;见月亮缺圆,就画个弯月象征“月”;观流水蜿蜒,便描出波浪纹作“水”。这些符号比绳结明白,比手势准确,《荀子·解蔽》载“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说的就是他把零散符号规整统一的功劳。
但难题很快来了:抽象的想法该怎么画?部落要“结盟”,既没有具体模样,又不能用绳结替代。仓颉坐在洛水岸边苦想,忽见一只玄龟游过,背甲上的纹路纵横交错,却各有章法。他猛地站起,在石上画了两个相握的手形,代表“合”,又在旁边加了个“口”,表示“共言”——“盟”字就这么成了。
他把造好的字刻在甲骨和陶片上,挂在部落的议事厅。起初有人觉得不如绳结顺手,可当外出的族人拿着刻有“危险”符号的木牌回来报信,当储存粮食的陶罐上“黍”“稷”的标记避免了错拿,质疑声全变成了惊叹。传说他造字那天,“天雨粟,鬼夜哭”,这不是神话的夸张,是文明突破蒙昧时,天地万物的共振。
仓颉没停下笔,他把部落人口耳相传的故事刻成“史”,把治病的草药形状记成“药”,把耕种的技巧写成“农”。这些文字像种子,落在华夏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如今我们写“文明”二字,“文”是仓颉最初画的纹路,“明”是他摹的日月之光。
从绳结到甲骨,从篆文到简体,文字的模样变了,但仓颉“观象造字”的初心没变——用符号记录生活,用文字传承智慧。当我们写下一笔一划时,都是在延续那场跨越五千年的文明接力,让蒙昧时代的那束光,一直照到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