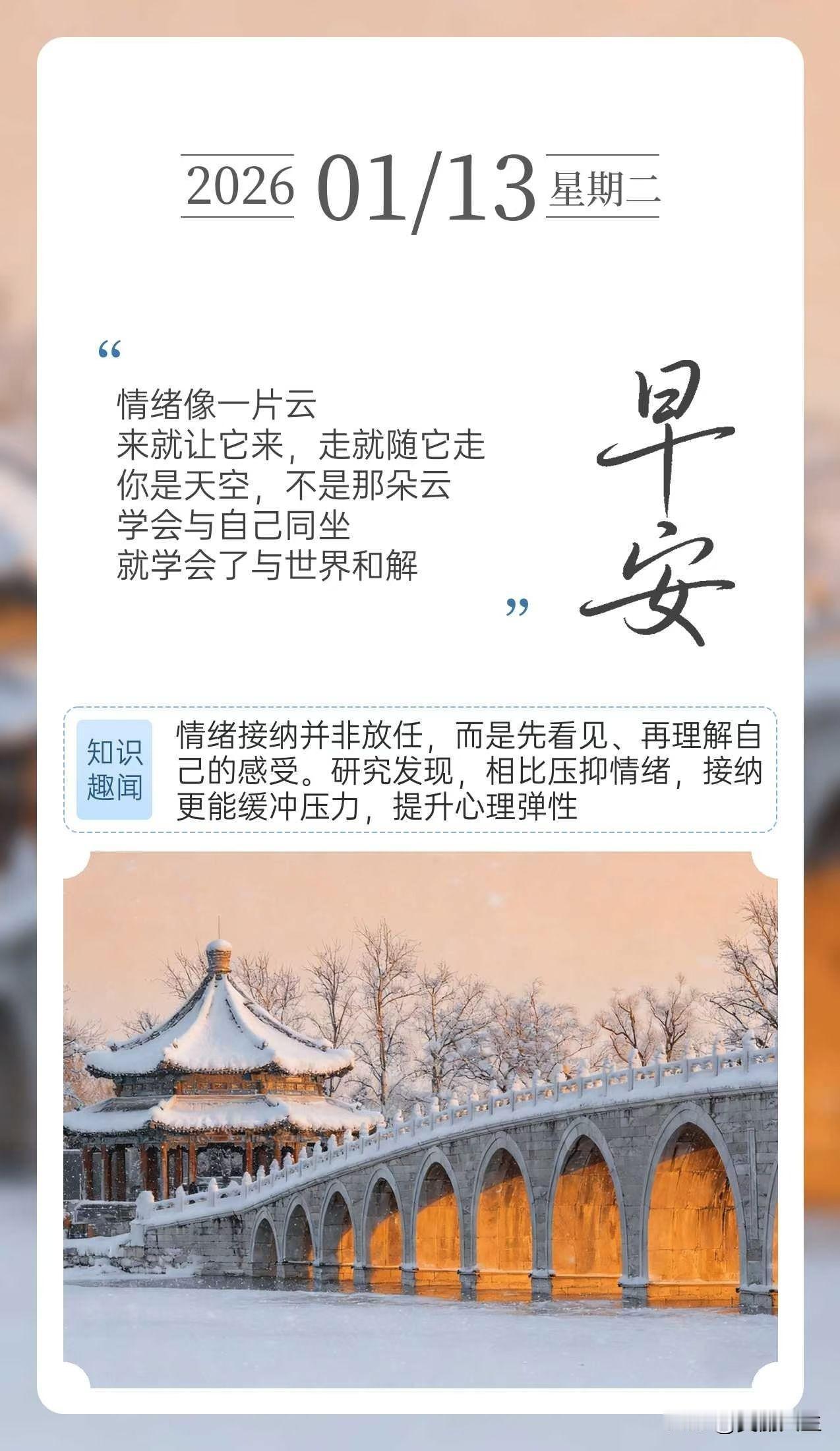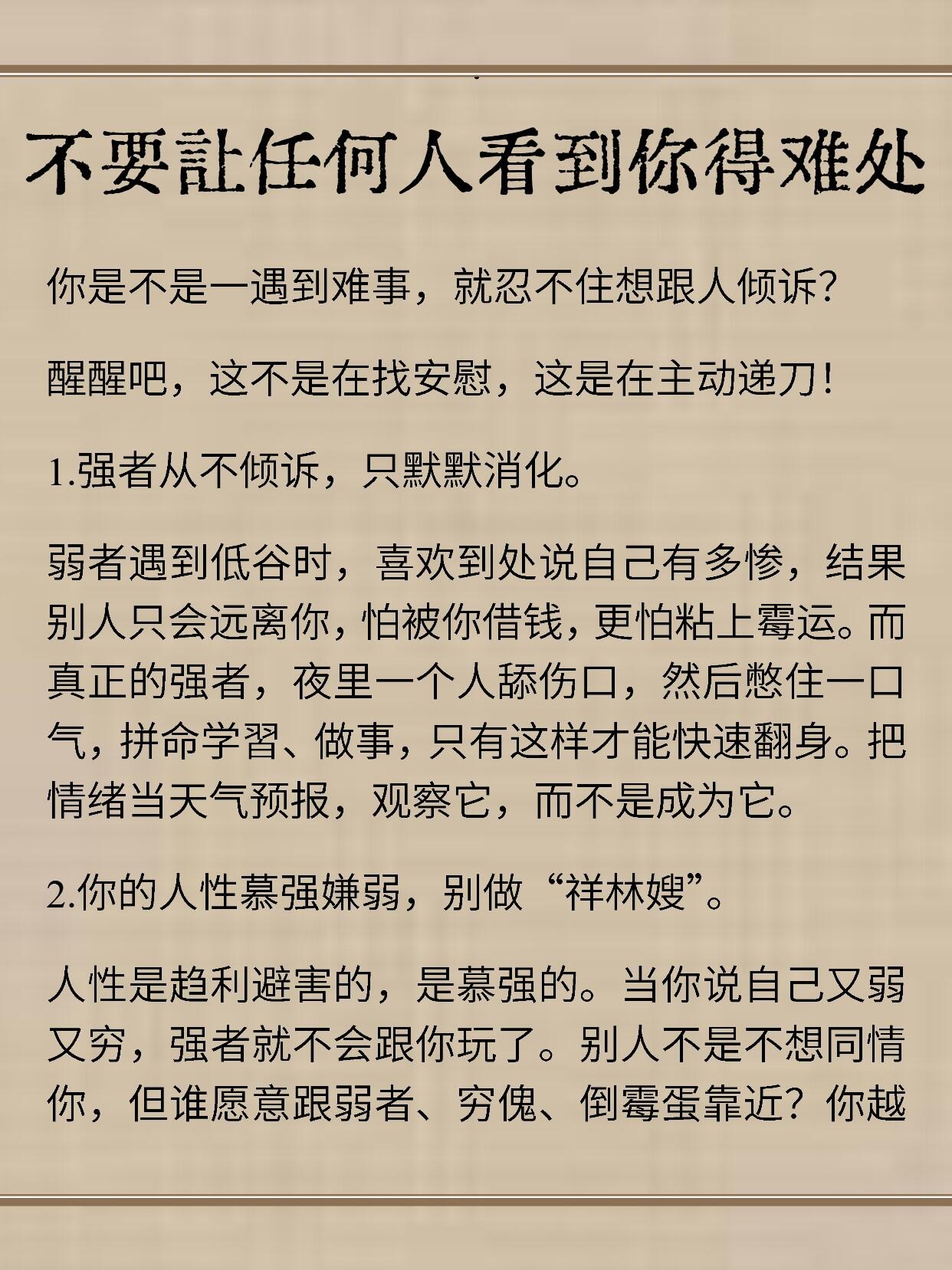夜渐深了,白日里被车马声填满的街道,此刻像装上一层薄薄的、温柔的暗纱。然而这暗并不寂寞,倒像是为另一种光亮预备下的衬底。稍远处,一团暖晕在街角轻铺,伴着一缕细细的、打着旋儿的白烟。走近些,才看清是一处小小的夜宵摊子,安静地泊在路灯疏淡的光影交界处,像一叶渡人的舟。

摊主是个寡言的中年人,只一味地低着头,将菜、配料、筷、碗摆弄出极轻柔的声响。烧水壶里的水一直滚着,咕嘟咕嘟,将那乳白的水汽不断吐出来,笼住他半身,也笼住半盏昏灯。那烟火气便从这里溢出来,不是燃放时的喧腾热烈,是慢火熬出的、带着米麦底香的暖意,丝丝缕缕,钻进人的衣袖里,肺腑里。三五个客人围桌而坐,也不多话,只顾尽情享受这暖心的烟火。

我站在远端看着,心里那些白日里拧着的、理不清的头绪,忽然就松开了,散了。这人间最深最稳的安顿,原来不在高堂广厦,而在这尘灰仆仆的烟火深处,在夜归人一碗暖心的慰藉里,在有人愿意为你,在深夜里留一盏灯、温一炉火的寻常守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