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 年,500 人的日军骑兵与只有 300 人的八路军骑兵相遇。敌军官手持望远镜,望着前方扬起的尘土:“八路一个都别想跑!” 八路军骑兵团长笑了笑:“我有法子让鬼子有来无回! 1942年的华北大地,马蹄扬起的黄土遮蔽了深秋的枯草。透过日军指挥官手中精致的军用望远镜,远处的景象清晰得刺眼:几百名衣衫褴褛的八路军骑兵,胯下的坐骑良莠不齐,有矮小的蒙古马,有耕田的甚至还有拉车的杂色骡子。而在镜头的这一端,是属于华北方面军的五百名精锐骑兵,清一色的东洋高头大马,马刀在日光下森然作冷,甚至马鞍旁还挂着令人生畏的掷弹筒。 无论是装备还是兵力,这都是一场还没开始就似乎注定结局的较量。日军军官轻蔑地收起望远镜,他太熟悉这片战场了,刚洗劫完一个村庄的他们正拖着装满物资的骡马队,士气高昂得近乎傲慢。在他的战术手册里,对面那支看似乞丐一样的队伍,唯一的下场就是被马蹄踏碎。 然而,八路军骑兵团长陈宗尧此刻并没有丝毫慌乱。这位从太行山贫瘠土地里杀出来的硬汉,目光越过敌人的刀光,死死钉在对方绵延的行军队列上。他敏锐地捕捉到了对手的致命伤:傲慢导致了队形的松散,为了炫耀武力和搬运掠夺的物资,日军的骑兵战线拉得过长,首尾难以呼应,而那些满载战利品的驮运骡马,恰恰就是卡死这台战争机器的沙砾。 陈宗尧很清楚,正面硬撞那是拿鸡蛋碰石头。他的底气,藏在身后那道叫“鹰嘴崖”的险地里。这里山壁陡峭如削,只有一条仅容一车通过的窄道。他回头扫视了一眼身后的兄弟们——这些曾经是庄稼汉、打铁匠、甚至有不少是来自河北沧州的武术练家子。他们手中的马刀虽不像日本军刀那样做工考究,甚至有不少是用扒来的铁轨钢在土炉子里千锤百炼打出来的,由于钢口硬,分量沉,虽显笨重,却有着专破精致军刀的蛮横劲力。 这一仗,打的是人心,更是地利。三百名战士迅速拆解成精密的作战单元:一支小队留在正面佯装败退,那略显慌乱的马蹄声演得惟妙惟肖;主力则早早分批隐入两侧的乱石与崖顶,那是专为骄兵准备的口袋。炊事班的老伙计们搬起了早就备好的滚木雷石,而几名视力好的神枪手已经把准星套在了日军前锋军官的脑袋上。 看到八路军“落荒而逃”,日军指挥官彻底被表象蒙蔽。他甚至没想过派出侦察骑兵探路,直接挥舞着那把名贵的指挥刀,嚎叫着发起全线追击。震耳欲聋的蹄声灌进了狭窄的山谷,日军如同贪吃的长蛇,毫无防备地一头钻进了鹰嘴崖的死胡同。 就在最后一匹日军战马的屁股没入阴影的瞬间,陈宗尧手里的驳壳枪响了。这一声清脆之音,恰似一道凌厉的利刃,刹那间扯断了死神那如影随形的缰绳,于寂静中迸发出冲破阴霾的力量,让生的希望陡然绽放。 这一刻,所有战术预想瞬间转化为血腥的现实。崖顶之上,早已蓄势待发的巨石与原木带着呼啸的风声坠落,瞬间将日军原本就拥挤的队形砸得稀烂。紧接着,原本静默的狭道两侧突然杀声震天,埋设的地雷在狭窄空间内不仅炸翻了人马,巨大的回声更是让那些受过严格训练的东洋战马瞬间受惊。 更绝的一招来自侧翼伏兵,他们并不直接与日军骑兵拼杀,而是专挑队伍中间驮物资的骡马下手。受惊的牲畜在狭窄的甬道里疯狂乱撞,顷刻间被自己的物资队冲得七零八落。彼时,那一门门精良的骑兵炮与掷弹筒,恰似沉重枷锁。 还没等日军从晕头转向中回过神,八路军的回马枪到了。 陈宗尧身先士卒,冲锋在前。他手中那柄特制的沉重马刀,于此刻彰显出了令人惊叹的威力,锐不可当之势似要冲破一切阻碍。一名日军军官举刀格挡,只听“哐”的一声脆响,精钢锻造的日军指挥刀竟然被那把土法炼制的重刀硬生生崩断,余势未消的刀锋顺势劈下,直接将不可一世的对手斩落下马。 那个名叫王二小的年轻战士杀红了眼,哪怕自己的坐骑被流弹击倒,他在地上打个滚爬起来接着战,手里那杆老旧的步枪此刻变成了最趁手的烧火棍,狠狠砸向每一个试图挣扎的鬼子。整个鹰嘴崖的谷底,充斥着硝烟味和血腥味,原本趾高气扬的“皇军”骑兵,被死死按在这条尘土飞扬的石缝里摩擦。 这场围猎仅仅持续了不到两个时辰。太阳西斜的时候,原本五百人的日军精锐骑兵中队,除了几十个跪在地上发抖的俘虏外,其余全部化作了黄土垄上的尸体。这支曾经装备精良、耀武扬威的队伍,就这样连同他们的傲慢一起,被一群拿着“万国造”武器的中国农民彻底粉碎。 战士们在兴奋地清点着成堆的战利品:崭新的三八大盖、平时金贵得不得了的弹药、还有那几百匹健壮的东洋马。这无疑是一笔横财,足以让整个骑兵团的装备上好几个台阶。 但在欢呼的人群之外,陈宗尧却显得格外沉默。他蹲在一处被血染红的土坡旁,那是三十几位牺牲战士长眠的地方。他脱下自己满是尘土的军装,轻轻盖在一位年轻战士渐渐冰冷的身体上。那个小伙子生前总念叨着想换杆新枪,如今新枪堆成了山,人却再也摸不着了。 这世界上哪有什么百战百胜的神话,有的只是把命别在裤腰带上的孤注一掷,和那是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的决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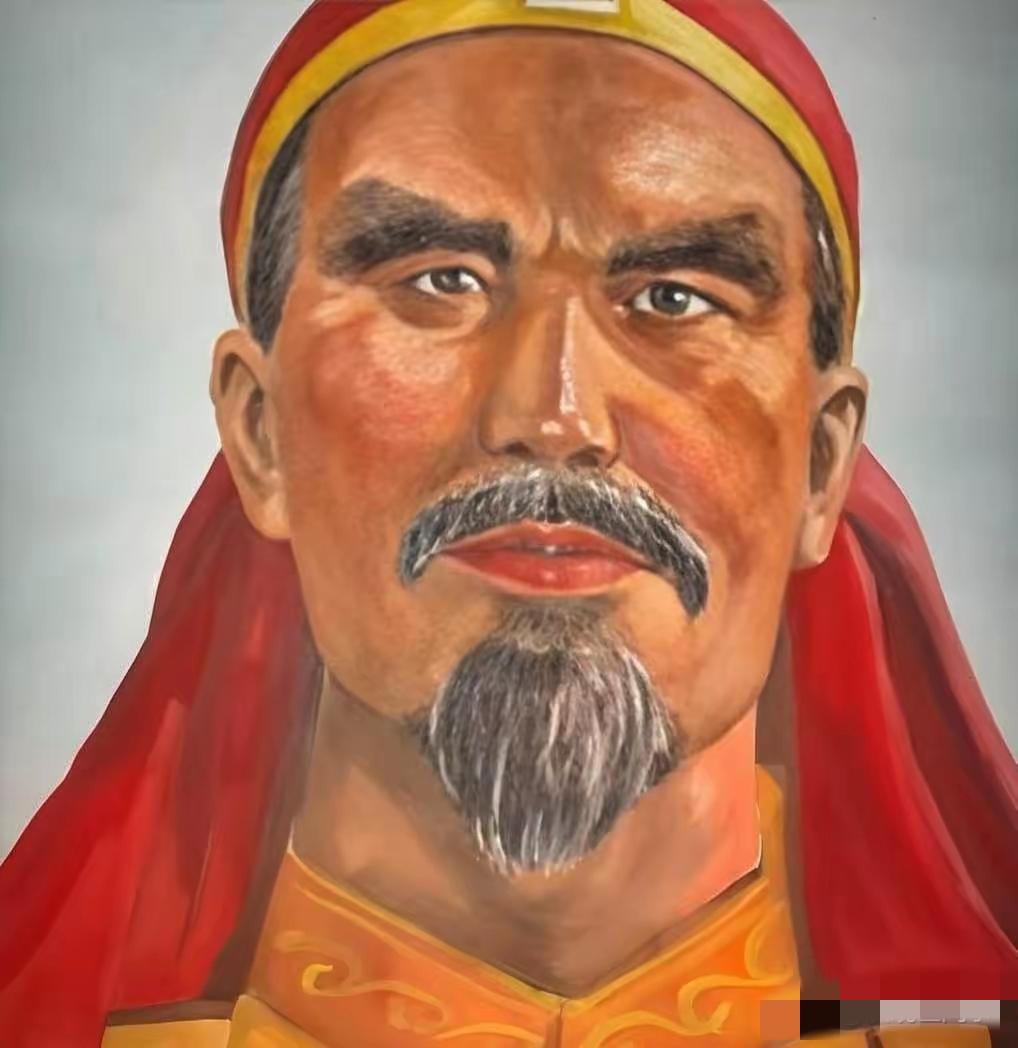




评论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