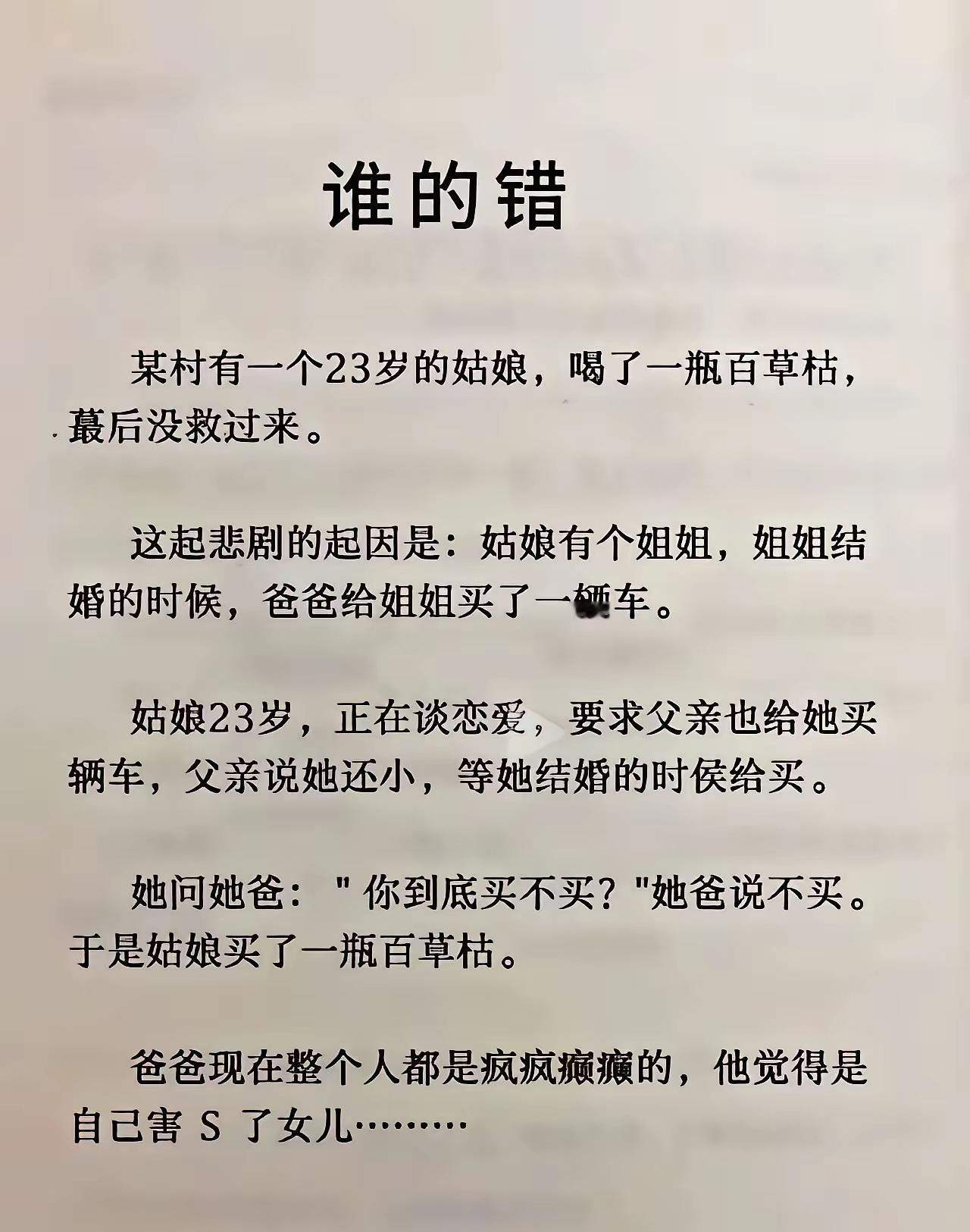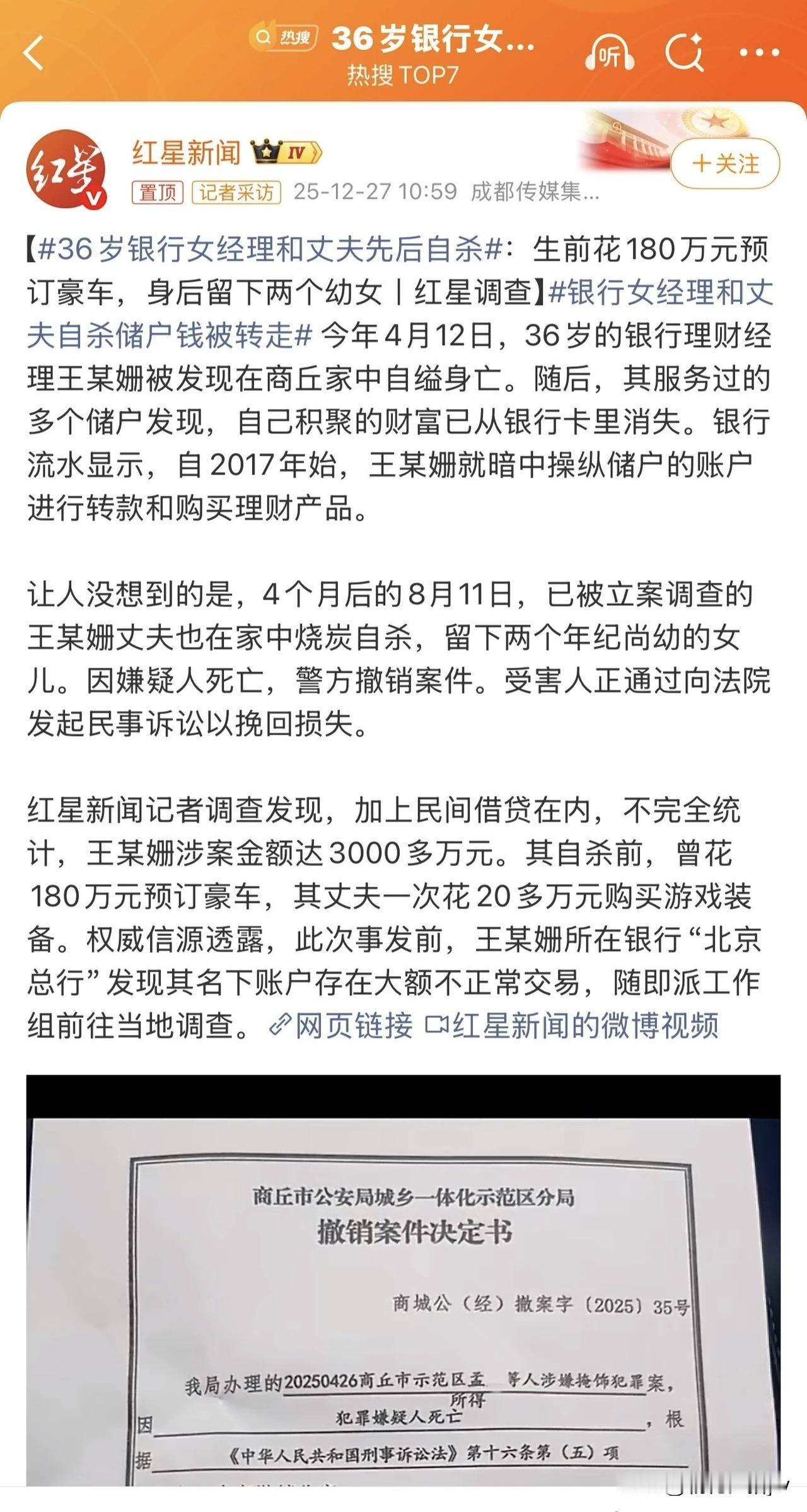1907年,林风眠母亲被族人抓去“沉塘”,年仅7岁的他抓起菜刀就冲向了人群,大声怒吼道:“放开我妈,不然我就不客气了!” 1900年,当这个瘦弱如猫崽的男婴降生在广东梅州的石匠家时,迎接他的不是喜悦,而是父亲嫌弃的眼神和预备丢向荒野的双手,若不是刚分娩的母亲赤足狂奔三里地,从死神手里硬生生抢回这条命,中国画坛便少了一座融合中西的高峰。 家里祖祖辈辈都在与坚硬冰冷的石头较劲,打石碑、做牲口槽,这种稍有不慎便会皮开肉绽的苦力活,原本是爷爷为长孙规划好的宿命,可偏偏,林风眠的魂魄被村口的染坊勾了去,对于一个五岁的山里娃来说,那里简直是个魔幻世界。 赤橙黄绿的布匹在工人的大手中翻飞,如同长了翅膀,染缸里升腾的彩色雾气,比祖父锤下的石屑迷人千万倍,他没日没夜地蹲在门口,甚至捡起工人丢弃的废颜料,在粗糙的石板上涂抹,那时的他还不懂,这便是他一生都在追寻的“光色之梦”。 那个读过书的染坊老板见他痴迷,偶尔教他识文断字,还成了林风眠后来考取梅州中学、遇见恩师梁伯聪的隐形推手,梁老夫子也没看走眼,当他在作业本背面看到那些关于染坊的稚嫩涂鸦时,惊得连眼镜都滑落下来,断言这孩子将来必成大器。 然而,色彩给了他天赋,却也招致了他人生中最惨痛的劫难,对于林风眠而言,世界上最美的线条,曾是母亲梳头时长发垂落的弧度,那位被拐卖到林家的苗族女子,即便被全村人视为异类,遭受着婆家对自己口音和出身的鄙夷,却在给儿子梳洗时流露出唯一的温存。 那一柄沾着山泉水的木梳,划过乌黑如缎的长发,成了林风眠日后笔下仕女图中挥之不去的婉约原型,但美的代价在那个封闭的山村里是致命的,悲剧爆发在1907年的一个晌午,因为想要逃离这种被禁锢的生活,风眠的母亲试图跟随那个教书识字的染坊老板私奔。 却不幸败露,宗族的长老们敲响了象征审判的铜锣,一群壮汉用粗麻绳将这个“不守妇道”的女人捆成粽子,这一幕恰好被正掏鸟窝的七岁林风眠撞见,那是一场足以撕裂灵魂的混乱,看着亲娘要被抬去池塘行刑,年仅七岁的孩子像头疯兽般冲进人群。 他从角落里抄起一把砍柴刀,嘶吼着挥向那些比他高出一倍的大人,当亲生父亲试图上来夺刀时,被逼急的孩子张嘴便狠狠咬住父亲的手腕,鲜血直流也不松口,最后虽然在祖父的干预下,母亲免于被“沉塘”的死罪,却被终生监禁或卖向不知名的远方。 那是林风眠最后一次见到母亲,那个手握柴刀护母的画面,如同一把尖刀插进他往后的每一幅画作里,他后来画《宝莲灯》里劈山救母的沉香,画冲破雷峰塔的白娘子,笔下那些眼神哀伤却姿态决绝的女性,其实都是为了祭奠那个消失在封建黑洞里的身影。 带着这份彻骨的痛与爱,林风眠在艺术的道路上狂奔,15岁那年,他怀揣着家里卖猪换来的学费走出大山,19岁,又凭着卖掉祖宅凑出的200大洋,踏上了驶往法国马赛的邮轮,在巴黎高等美术学院,这位从未见过这种场面的东方少年。 初见裸体模特时羞得躲到画架之后,但很快,西方印象派的光色与野兽派的奔放,与他骨子里沉淀的东方线条发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当他的水墨荷花在巴黎展出时,连当时最负盛名的教授都在惊叹这种东西方神韵的完美结合。 26岁那年,他已是北平艺专最年轻的校长,力排众议请木匠出身的齐白石登上讲台,28岁转战杭州,在西湖边创立了国立艺术院,将赵无极、李可染等日后的巨匠引入艺术殿堂,他在画纸上进行着一场豪赌,试图用西方的色彩改良中国的水墨。 那大红大绿与深沉黑墨的碰撞,像极了当年染坊里的绚烂与家里石碑的厚重,即便在抗战爆发、流亡重庆的困苦岁月里,住在连墙壁都漏风的破仓库,他依然能在一盏孤灯下,日复一日地描绘着心中的丹青。 可是,那场席卷全国的风暴,让他不得不在西湖边的寓所里,亲手销毁了那些像孩子一样的画作,没有人知道,当他把画纸捣烂冲走时,是否想起了多年前母亲消失的那个清晨,同样是无可奈何的毁灭。 直到上世纪80年代定居香港,早已步履蹒跚的林风眠才重新拾起画笔,此时他画里的仕女,眼波中那层雾蒙蒙的哀愁更浓了,仿佛隔着半个世纪的时光,依然在张望那个再也回不去的梅州山村。 1991年,92岁高龄的林风眠躺在病榻上,生命即将燃尽,他意识模糊,嘴里反反复复只念叨着“想回家”守在床边的弟子轻声询问是回杭州的画室还是梅州的老宅,老人却再也无法回答。 弥留之际,他枯瘦的手指在虚空中划出一道极尽温柔的弧线,像是作画,又像是在抚摸什么人的长发,在他离世后的枕边,静静躺着一把断了齿的旧木梳,仔细端详,乌木手柄上那一圈深深的牙印依然清晰可辨。 那是七岁那年,一个孩子为了留住母亲,在绝望中拼尽全力咬下的痕迹。 信息来源:网易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