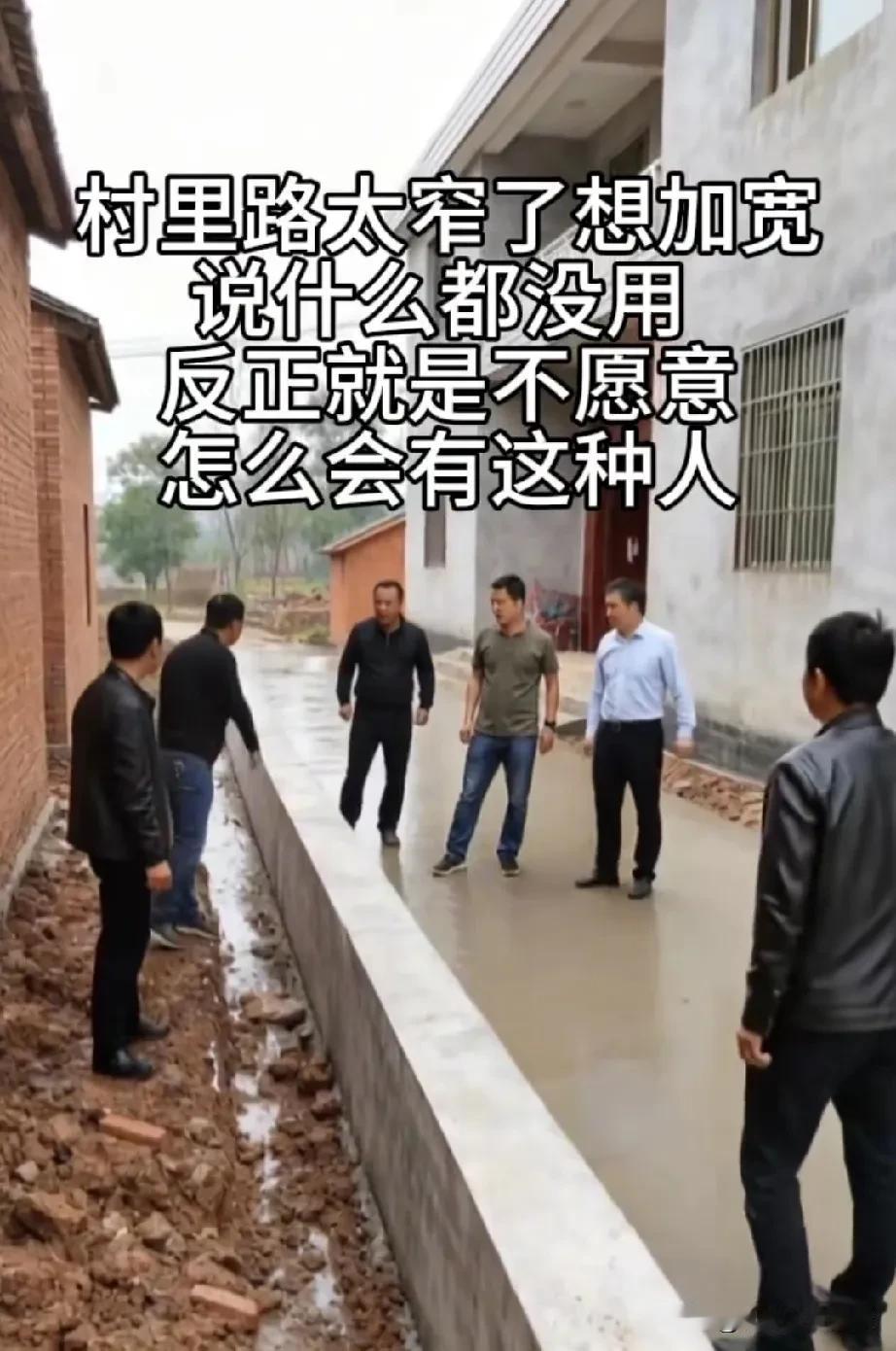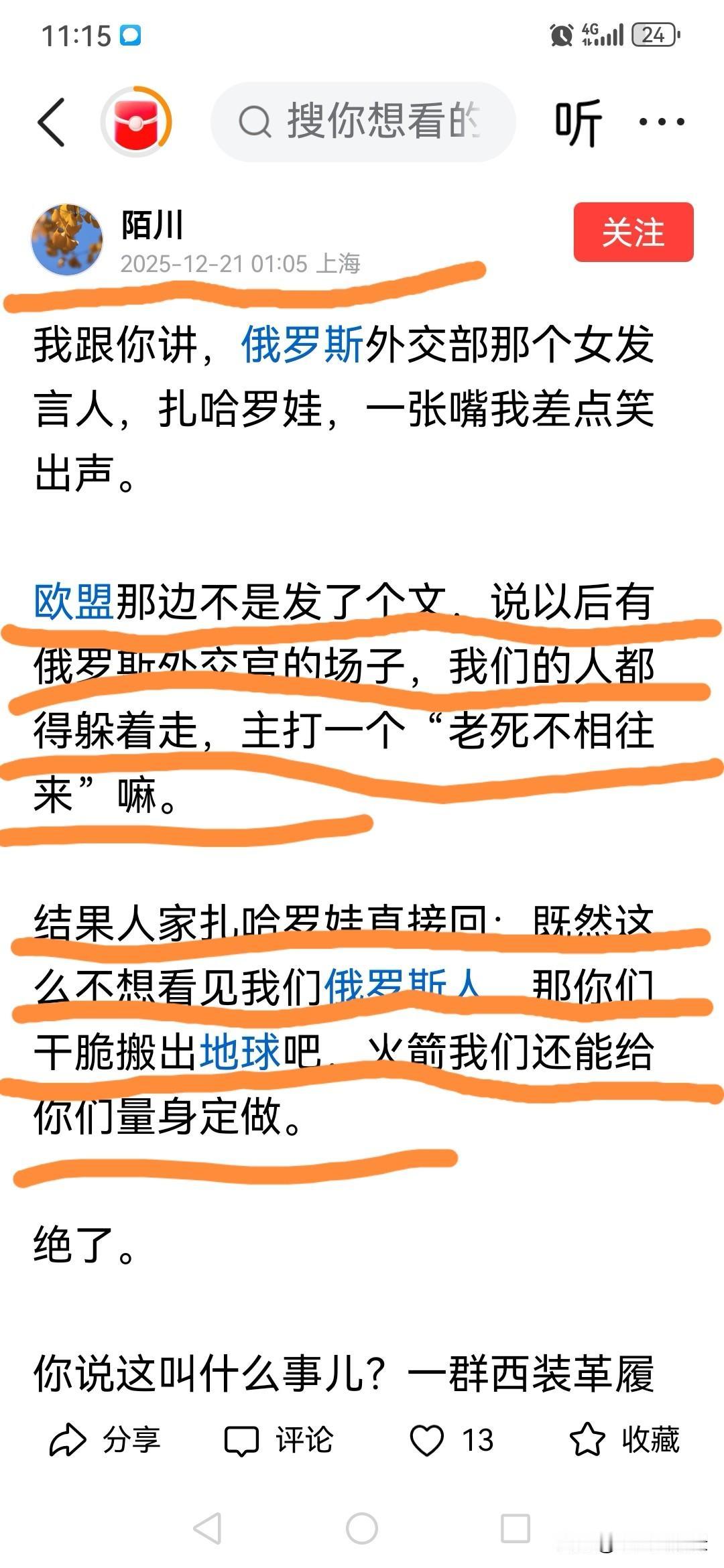三婶很强势,里里外外当家管计,三叔只能唯唯诺诺。村里红白喜事,三婶往桌前一坐,嗓门一亮,端茶倒水、上菜撤盘,指挥得井井有条;家里大小事,从油盐酱醋到堂弟的学费,三叔连句重话都不敢说。 村里都说老陈家是媳妇掌舵,男人掌舵的船早沉了——这话三叔听见了,只会摸出旱烟袋,在鞋底上磕两下,烟丝簌簌落进砖缝里。三婶的蓝布围裙永远系得紧,系带在背后打个死结,像她攥着家里账本的手,指节总泛着白。 那年三叔在砖窑厂摔断了腿,工头卷着医药费跑了,三婶揣着仅有的两块八毛钱,在镇卫生院走廊坐了整夜,天亮时直接闯进院长办公室,拍着桌子说“今天不给治,我就躺这儿当药引子”,后来才知道她兜里除了钱,还有把剪刀——那是她连夜磨快的,说实在不行就“借”血库里的血。 腿好利索后,三叔试着提过想跟人去外地包工程,三婶正在纳鞋底,线绳“噌”地扯断,“你忘了上次从脚手架上掉下来?我在太平间门口守三天,你倒好,醒来第一句问瓦刀找着没——这家里是缺你挣那俩钱,还是缺我给你收尸?”三叔的脸涨成猪肝色,终是没再说一个字,默默把墙角的瓦刀挪到了床底。 村里人只看见三婶在红白喜事上指挥若定,嗓门能盖过唢呐,却没人看见她半夜给三叔揉腿时,指腹在旧伤疤上轻轻摩挲,像抚摸一件易碎的瓷器;只听见她骂三叔“没出息”,没听见她对着账本叹气,说“这月电费又涨了,娃的补课费得省着来”。你说这是强势吗?或许,不过是一个女人把“怕”字嚼碎了,混着眼泪咽进肚子,再用硬气当铠甲。 三叔不是真懦弱。那年发大水,村东头老井塌了,三婶非要跟着去抢险,他第一次拽住她胳膊,手劲大得像铁钳,“你在家看着娃,我去”——后来他在井边泡了两天两夜,回来时高烧不退,三婶守着他,把熬糊的粥倒进泔水桶,自己啃了个冷馒头,没骂一句。有些事,他知道她得扛,有些事,他必须替她扛。 短期看,这日子过得像拧巴的麻花,一个往前冲,一个往后退,倒也没散架;往长了说,堂弟谈恋爱时总跟姑娘讲“我妈凶是凶,但我爸摔断腿那年,她把嫁妆都当了,现在那只银镯子还在箱底压着”,眼里亮闪闪的,没半分抱怨。 其实不用做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就像那天堂弟婚礼后,三叔买了瓶二锅头,倒在两个粗瓷碗里,三婶的围裙还系着,只是背后的死结不知何时松了,系带垂在腰侧,像两只终于歇脚的蝴蝶。“喝啊,”她催他,嗓门还是大,却软了三分,“当年你说天塌了扛,现在天好好的,你倒不敢碰酒杯了?” 三叔端起碗,手没抖。酒液在碗里晃,映着屋顶的灯泡,也映着她鬓角的白头发——原来铠甲穿久了,也会生铜绿;原来退让多了,不是懦弱,是把最软的地方,留给了最亲的人。烟袋锅子早被他收进抽屉了,现在他学会了给她倒酒,就像她当年学会了替他挡事一样,谁也没说破,却都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