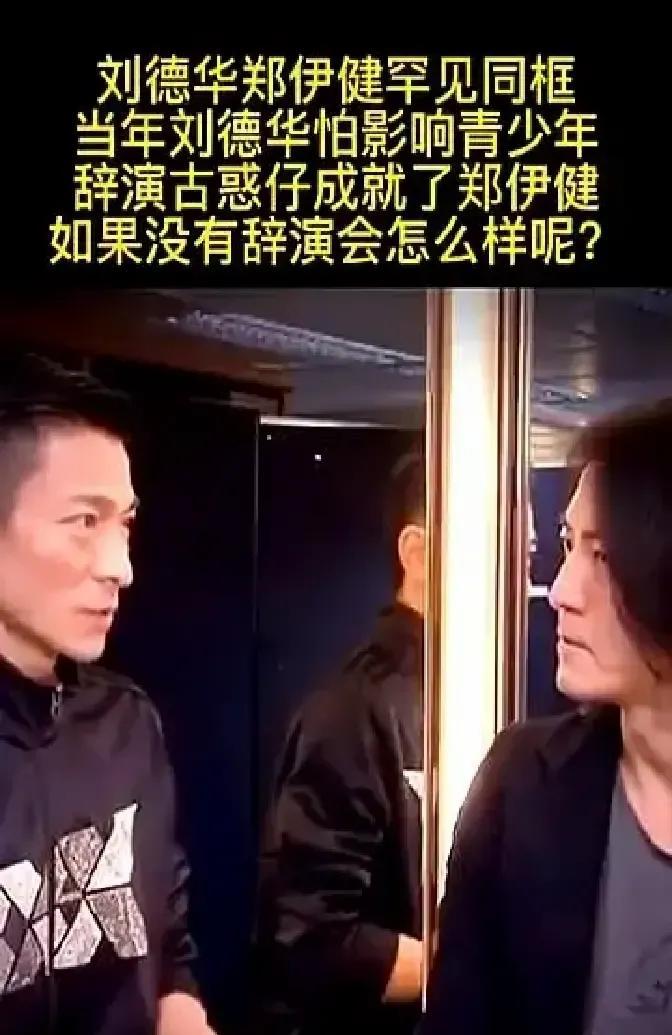2003年,梅艳芳去世不久后,他的主治医生在一次采访中透露:“其实梅艳芳的病完全是有可能治好的,但就因为一件事,她主动放弃了治疗!” 医生盯着报告上的那个数字:85%,在医学上,这已经算是相当乐观的讯号了,对一个肿瘤大小只有三厘米、也没蔓延到淋巴的早期宫颈癌患者来说,这几乎等于“只要按流程做手术,就能继续好好活”。 可偏偏坐在诊室椅子上的梅艳芳,脑子里转的不是“我能不能活”,反倒是飘去了完全不同的方向。 她做人一向认真到近乎挑剔,连面对癌症都如此,手术前,她把厚厚一摞有关癌症和生存质量的研究资料翻了个遍。 还不放心,又打电话越洋去问日本早稻田大学做声学研究的专家,就为搞清楚一个别人可能连想都想不到的问题:摘除子宫,会不会让共鸣变了,哪怕只有一点点? 除了这些专业问题以外,她还小心翼翼地问医生一句特别私人、特别痛的:“如果做了,我还算是一个完整的女人吗?” 医生看的是病灶和数据,可她想起的却是自己小时候那个伤痕累累的小孩。 四岁那年,在荔园游乐场的舞台上,她正唱着《卖花女》,突然被台下一个醉汉狠狠砸了个烂苹果,额头当场破了、血往下淌。 可那个本该保护她的母亲,居然转身去捡地上的零钱,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把她一个人留在台上继续唱。 这种冷得像冰碴子的经历,让她长大后对“亲情”两个字有种填不满的缺口,她的床头一直放着一个不值多少钱的音乐盒,里面转着一对紧紧抱在一起的母女雕像,那其实是在补她小时候没得到的温度。 1990年,她最亲的姐姐梅爱芳因同样的病离开人世。姐姐走之前扶着她的手,声音微弱却抓得死紧:“阿梅,你一定要有个孩子,得有自己的家。” 这句话像钉子一样扎进她心里,从那以后,她始终记着,也正因为如此,当医生把子宫切除的同意书递上来时,她不愿意签。 她不是拒绝治疗,而是死死守着自己最后一点能“成为母亲”的可能性,对她来说,只要子宫在,那个关于家的愿望就还没彻底碎掉。 所以她宁愿不要最佳治疗方案,也坚持选择效果没那么强的放疗加药物,她甚至把这种身体上的折磨,当成创作的一部分、生命最后的投入。 2003年愚人节那天,张国荣从文华酒店跳下去后,她整个人像被抽走力气一样,经纪人说,她回港后对着哥哥的照片把指甲都掐进肉里。 就是那一刻,她决定把余下的时间全用来完成一场真正属于她的“最终谢幕”。 放疗带来的痛说给别人听都没人能理解:皮肤像纸一样薄,稍一碰就可能破、可能流血,可为了最后那场告别演唱会,她硬是要求戴上那顶足足8公斤多的鎏金凤冠。 后台化妆间几乎成了战场,医生和护士得小心到极致地处理每一处破皮的伤口。 下身因为病情难以控制的出血,她只能靠厚厚的止血垫藏在那件华丽到极致的婚纱里。 她上台前那一针止痛剂打进去的时候,应该已经痛到极限了,但灯光一亮,她仿佛瞬间换了一个人:一个身体虚弱、上台得靠人扶的病人,就这么变成了台上光芒四射的女王。 唱到《夕阳之歌》那段,她拖着那条长到像云一样的白婚纱,一步步走上台阶。 那时血已经慢慢渗出来了,但灯光把一切都盖住,她用全部的力气,把“嫁给舞台”这个念头变成现实。那是她最豪华、也是最悲壮的婚礼。 “我试过很多件婚纱,但总觉得没有一件属于我。”她在台上这么说,声音轻轻的,可眼里全是水光。 那时的她,是舞台上的巨星,更是那个从小想听妈妈一句夸奖的小女孩,她保住了自己身体形式上的完整,用只有四十年的生命,换来了一个近乎完美的艺术终点。 后来,那年冬天快到尽头的时候,护士听见她迷糊之间轻轻说的最后一句话里,没有害怕,也没有遗憾。 她像是在跟空气里的某个身影说话:“妈妈,我赚到钱了,可以买大房子了……” 那个被丢在舞台上的四岁小孩,其实从来没有离开过。她用一生努力想证明自己值得被爱,而最后,她还是留在了那个舞台上,继续扮演那个想要讨妈妈欢心的孩子。 对此你怎么看? 信源:搜狐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