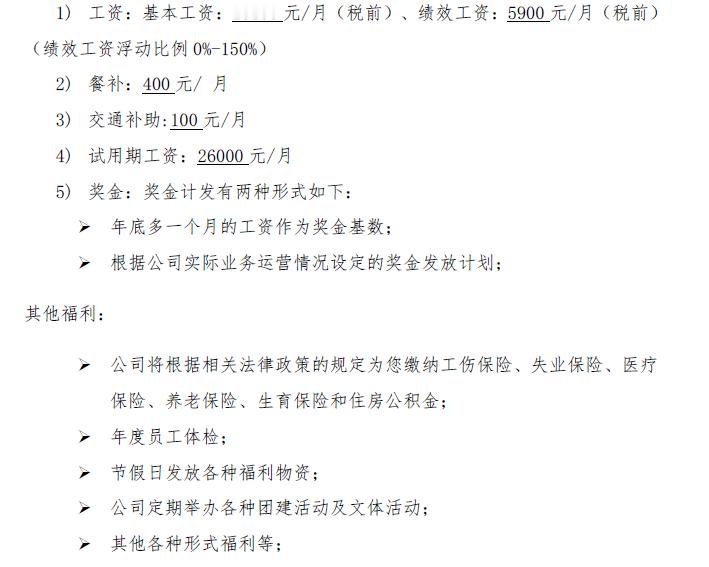姥姥是大户人家正室所生,一生却过得清贫。那些小妾生的弟妹,不是当了大官,就是出了国。同样的出身,境遇却天差地别。 姥姥常说,她小时候是家里最受规矩束缚的孩子。正室母亲活得体面又憋屈,教她凡事要忍让、要端庄,不能争也不能抢,说女孩子家安稳才是福。可小妾们生的弟妹不一样,他们从小就懂得看老爷子的脸色行事,嘴甜会来事,哄得老爷子眉开眼笑,家里有啥好东西,吃的穿的,还有读书的机会,那肯定先紧着弟妹们挑。 后来母亲走得早,家里更没人替姥姥说话了。老爷子心里头偏着小妾生的娃,总觉得姥姥是“正室的孩子,该懂事”,啥好处都轮不到她。十八岁那年,有个留洋回来的先生看上姥姥,说想娶她,还答应送她去学堂念书。可小妾在老爷子跟前吹枕边风,说“女孩子家读那么多书干啥,嫁个本分人家才是正经”,硬是把这门亲事搅黄了。最后姥姥嫁给了邻村一个木匠,就是我姥爷,家里除了一把刨子、几张木凳,啥值钱玩意儿都没有。 那会儿村里人都说姥姥傻,放着大户人家的小姐不当,偏要嫁个穷木匠。姥姥听了也不恼,就坐在门槛上纳鞋底,慢悠悠地说:“安稳日子,是自己过出来的,不是争来的。”她跟着姥爷学木工活,白天帮着拉锯、打磨,晚上就在煤油灯下缝缝补补,家里的衣裳、被褥,全是她一针一线做的。冬天冷,她就把旧棉袄拆了,重新絮上新棉花,姥爷穿上总说:“比城里买的还暖和。” 弟妹们后来混得一个比一个好。二舅姥爷靠着老爷子的关系进了政府部门,没几年就当上了局长,出门小轿车接送,穿的中山装笔挺;小姨姥姥更厉害,嫁了个华侨,跟着去了美国,听说住的房子带花园,光佣人就请了三个。有一年小姨姥姥回国探亲,开着小轿车到村口,看见姥姥蹲在菜园里摘豆角,裤腿上还沾着泥,撇着嘴说:“姐,你看你这日子过的,要不跟我去美国吧,保准你吃香的喝辣的。” 姥姥直起腰,拍了拍手上的土,笑着说:“不去啦,我这菜园子的菜刚浇了水,过两天就能吃;院里的鸡下了蛋,给隔壁张奶奶送两个,她孙子正长身体呢。去了美国,谁给我送新鲜的韭菜盒子呀?”小姨姥姥撇撇嘴,觉得姥姥没见过世面,坐了没十分钟就走了。 其实姥姥不是没见过世面,她小时候住的院子比小姨姥姥在美国的花园还大呢。可她总说:“日子过得舒不舒服,不在房子多大、钱多少,在心里踏实不踏实。”姥爷走得早,姥姥一个人拉扯我妈和舅舅长大,靠接些缝补的活计,还有院子里那几分菜地,硬是没让孩子饿过肚子。邻居谁家有难处,她总会把刚蒸好的馒头分一半过去,说:“都是街坊,帮衬一把是应该的。” 后来二舅姥爷在官场上栽了跟头,听说是为了往上爬,跟人争权夺利,最后被撤了职,在家天天唉声叹气。小姨姥姥在美国也不省心,听说跟华侨老公吵翻了,一个人住在大房子里,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有次打电话给姥姥,哭着说“还是小时候好,姐你总把糖给我吃”。姥姥在电话这头叹口气,说:“那会儿让你吃,是觉得糖甜;现在日子苦,就想想当年的糖味儿,心里就甜了。” 姥姥活到九十岁才走,走的时候很安详,手里还攥着我给她编的草蚂蚱。她一辈子没穿过绫罗绸缎,没住过高楼大厦,可街坊邻居都说,姥姥是村里最有福气的人——吃得香,睡得稳,见人就笑,心里头干净得像块透亮的玻璃。 现在我总算明白,姥姥说的“安稳才是福”,不是认命,是她把日子过明白了。那些争来抢去的,看似风光,心里头却堵得慌;反倒是姥姥这样,不争不抢,守着自己的小日子,把平凡的日子过出了甜味儿。你说,这到底谁过得更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