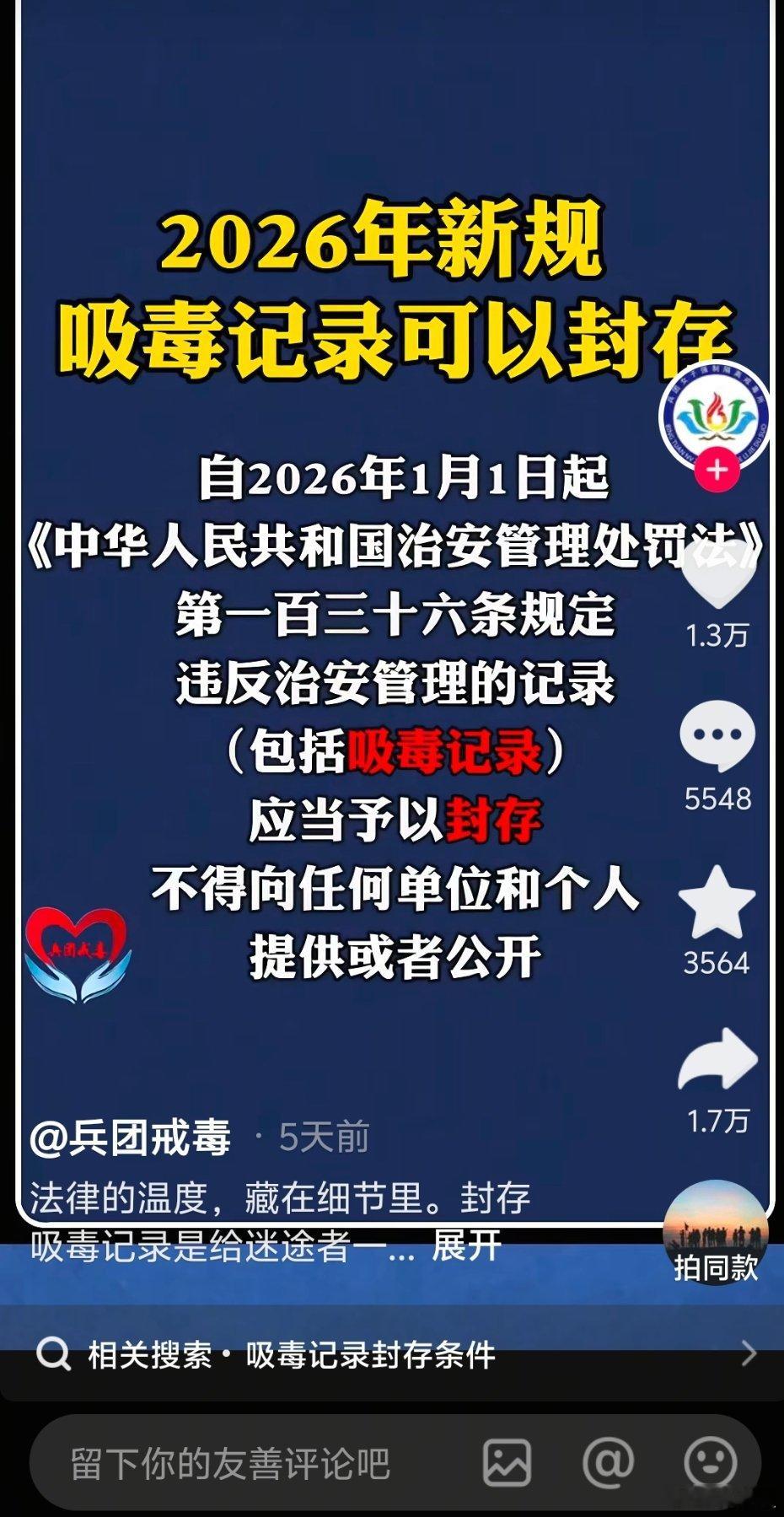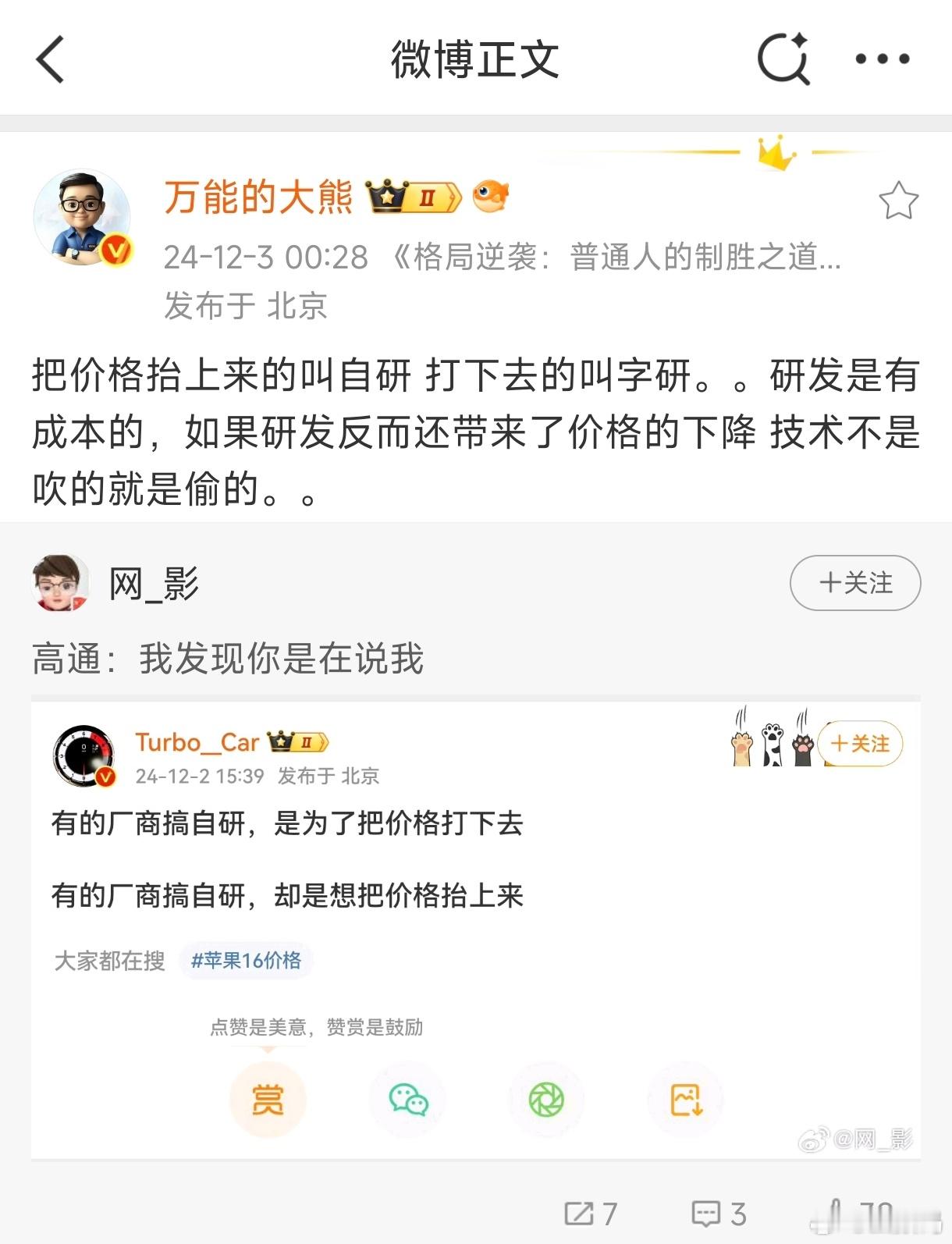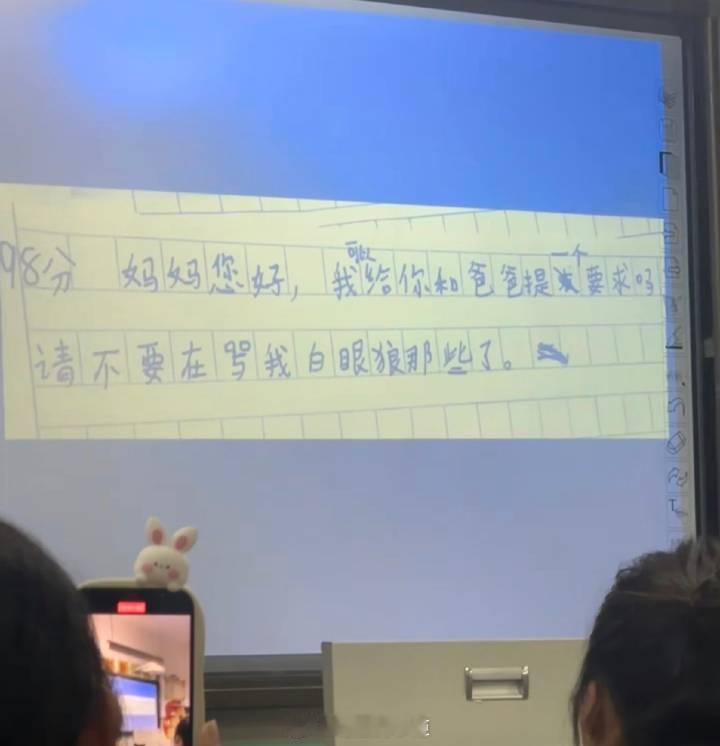非常有道理的一段话: “孩子的衣服可以送人,但有4样东西,再新也别送,别人送你也别要。一、入口的东西,开封了,别送也别要。二、贴身的衣物,穿过了,别送也别要。三、有特殊意义的东西,别送也别要。四、没得到孩子同意的,别送也别要。不随意送东西,也不随意收东西,无论送或要任何东西,原则只有一个:这样东西不要有任何的健康、安全、情感隐患。” 整理女儿衣橱时,我对着那件只穿过一次的粉色羊绒衫犯了难。楼下的林阿姨刚添了孙女,可这件价值不菲的小衣服,领口已经有些起球。 “送人吧?”母亲在一旁说,“这么新的衣服。” 我犹豫着,想起三年前那罐开了封的奶粉。 那时女儿刚满月,对门的张姐热情地送来她孙子喝剩的进口奶粉。“就开了封,孩子转喝母乳了,别浪费。”盛情难却,我收下了。谁知女儿喝了当晚就起红疹,连夜去医院才知是轻微过敏。张姐后来见面总说:“我家孙子喝就没事...”那语气,像根小刺扎在心里。 入口的东西,开封了,别送也别要。 这不是客气,是对生命的敬畏。 最终,我把羊绒衫留了下来,改成女儿的坐垫。有些好意,收下是负担,拒绝才是负责。 上周整理夏装,翻出女儿那套真丝睡衣。去年表姐送的,她女儿只穿过两回,几乎全新。可这次,我直接把它放进了旧衣回收箱。 去年夏天,女儿穿上这套睡衣的第二天,后背起了红点。医生说可能是洗涤剂残留。表姐知道后不太高兴:“我们很注意卫生的...”女儿却悄悄告诉我:“妈妈,衣服上有陌生小朋友的味道,我不喜欢。” 贴身的衣物,穿过了,别送也别要。 这不仅是卫生,更是一种界限。皮肤记得每一个主人的温度,孩子尤其敏感。 最让我痛心的,是那个布娃娃。 女儿三岁时,奶奶把姑姑小时候玩的布娃娃洗得干干净净送给她。那是姑姑最珍爱的玩具,保存了三十年。可女儿并不喜欢,随手扔在角落。奶奶每次来都要问:“娃娃呢?”发现被冷落,总会失落地说:“你姑姑小时候抱着它睡觉...” 后来女儿不小心把娃娃弄脏了,奶奶难得地发了火。那一刻我明白,我们送出的不是娃娃,是一份沉甸甸的期待。女儿被迫成了别人回忆的保管员。 有特殊意义的东西,别送也别要。 每个记忆都该有自己的归宿,不该成为下一代的负担。 上个月,侄女来玩,看中了女儿的绘本机。女儿不在家,我心想反正她最近也不用了,就让侄女带走了。女儿回家后,哭着说那是爸爸去年跑遍全城才买到的生日礼物。 我连夜去弟弟家取回。弟媳脸上写着不满,侄女的哭声在身后响起。那一刻我明白:没得到孩子同意的,别送也别要。 再小的物品,在孩子心里都可能有着特殊的分量。 现在,我家有个“流转箱”。女儿不玩的玩具、不看的书,都会先放进去。如果有小朋友来玩,她主动分享的,我才允许对方带走。那些她舍不得的,就继续留着。 昨天,邻居小朋友看中了女儿的旧滑板车。女儿想了想,说:“这个轮子有点松了,我让爸爸修好再给你吧。” 我欣慰地看着她。六岁的孩子已经懂得:分享的前提是安全,赠送的基础是尊重。 傍晚,我和女儿一起整理她的“宝藏盒”。里面有小石头、枯树叶,还有半截蜡笔。“这些可以送人吗?”她问。 “这是你的记忆,”我摸摸她的头,“你决定。” 她想了想,把一片枫叶书签放进要给小朋友的礼物堆:“这个可以分享,但这片银杏叶要留着,它是和爸爸一起捡的。” 无论送或要任何东西,原则只有一个——这样东西不要有任何的健康、安全、情感隐患。 月光从窗外洒进来,照在那些即将被送走的玩具上。我突然理解了母亲当年的话:物有物的尊严,情有情的边界。真正的善意,是既不让对方感到被施舍,也不让自己觉得被辜负。 《朱子家训》有言:“与肩挑贸易,毋占便宜;见贫苦亲邻,须加温恤。”给予需要智慧,不是廉价的施舍,而是带着尊重的体恤。送孩子旧物时,更要考虑对方的感受,不让人难堪。 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说:“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延伸到育儿领域,即“我可以不认同你的选择,但我尊重你对自己物品的所有权”。孩子虽小,但对属于自己的东西,应有绝对的处置权。 黎巴嫩诗人纪伯伦在《先知》中写道:“你的孩子,其实不是你的孩子,他们是生命对于自身渴望而诞生的孩子。”我们只是他们童年的守护者,而非主宰。他们珍视的每件物品,无论多么微不足道,都值得被尊重。 作家三毛曾说:“我的心有很多房间,荷西也只是进来坐坐。” 每个孩子的心,也有很多房间。有些礼物可以收下,有些回忆需要独享。懂得这一点,才是真正懂得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