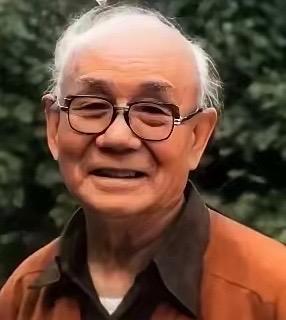1947年冬天,北平冷得能冻裂砚台。李可染夹着一卷画,跟在徐悲鸿后头,心里七上八下——前面就是齐白石的四合院。老爷子正窝在躺椅上晒太阳,眼皮都不抬,活像一尊笑面佛。徐悲鸿刚开口介绍,齐白石只“嗯”了一声,顺手接过画,翻了两页,又合上,客气得跟拒收快递似的。 李可染脸上挂不住,暗暗咬牙:下回再来,得让老爷子“哇”一声! 机会很快来了。隔月,他又夹着新作登门,这回手里有“硬菜”——一幅《牧牛图》。老头照例半躺,画轴展开一半,眼睛忽然亮了,身子嗖地坐直:“拿笔来!”众人还没反应过来,齐白石已经挥毫,在牛背上写下十一个大字:“可与言可染弟画,白石老人愿同游。”写完,把笔一扔,冲李可染乐:“小子,牛背画得比我腰还软,这朋友我交了!”一句话,把屋里寒气全赶跑。 后来?后来这幅题了字的《牧牛图》拍出了7751万,这是后话。当时李可染只觉脑袋嗡的一声,差点给老爷子鞠躬到地板。齐白石拍拍他肩膀:“别谢我,画钱归你,牛归我。”逗得满屋子哄笑。徐悲鸿在旁边挤眼:小子,通行证到手了! 其实那幅《牧牛图》真没那么“艳”——水墨而已,一头黄牛,一个娃,几根柳条。胜在味道对了:牛背驼得软,娃儿笑得憨,柳条像刚被春风剪过,透着湿润的泥土气。齐白石看中的是这股“土腥子”,他自己画虾画蟹,也是这股鲜灵劲儿。老头常说:“画牛得闻牛粪味,画虾得尝海水腥。”李可染的牛,恰好踩在他的“味”上。 更关键的是,李可染把“笨”劲使在了刀刃上。为画牛,他跑去京郊村子,跟放牛娃混仨月,白天骑牛背,晚上住牛棚,一身牛粪味回家。夫人说他“疯”,他笑:“不疯,牛不搭理我。”这股疯劲,齐白石最懂——当年为了画虾,他能在缸前蹲一天,就为看虾须怎么抖。两个“疯子”碰到一块,火花四溅,一幅小画,成了世纪忘年交。 有人吐槽:大师题个字,凭啥多卖七千万?我倒觉得,钱只是放大镜,放的是艺术价值,更是历史温度。齐白石那十一个字,不只是夸奖,是盖章认证——“这小子,我认了”。在当时,齐白石一句话,比十所大学文凭都管用。李可染后来创“李家山水”,牛背图式成了招牌,追根溯源,就是老爷子这一笔“点将”。 再说个插曲。齐白石八十九岁那年,李可染又画《牧牛图》,送去给老头看。齐白石非要自己添几笔,结果手抖,柳条画歪了,急得直跺脚。李可染却笑:“柳条被风吹歪了,正常。”老头哈哈大笑:“你小子,会拍马屁,也会画牛!”这幅“歪柳”版,后来进了中国美术馆,成了镇馆之宝之一。你看,两位大师, 一个敢歪,一个敢认,艺术就这么活过来了。 回到当下。拍卖槌一响,7751万落槌,有人咋舌,有人撇嘴“泡沫”。我倒想,要是齐白石听见,肯定捋胡子乐:“好,牛值钱,比虾贵!”然后转头补一句,“可别让钱蒙了眼,画得好,牛粪也香;画不好,金纸也臭。”这话,送给所有盯着拍槌的人。 对我而言,这幅《牧牛图》不是天价传奇,是一堂公开课: • 想让人叫好,先得让自己叫真; • 想入大师眼,先得把自己丢进泥巴里; • 艺术这碗饭,没有捷径,只有笨路。 正如齐白石那十一个字——可与言,可同游,是邀请,也是考题:你敢不敢牵着牛,一起走进那片柳烟深处?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