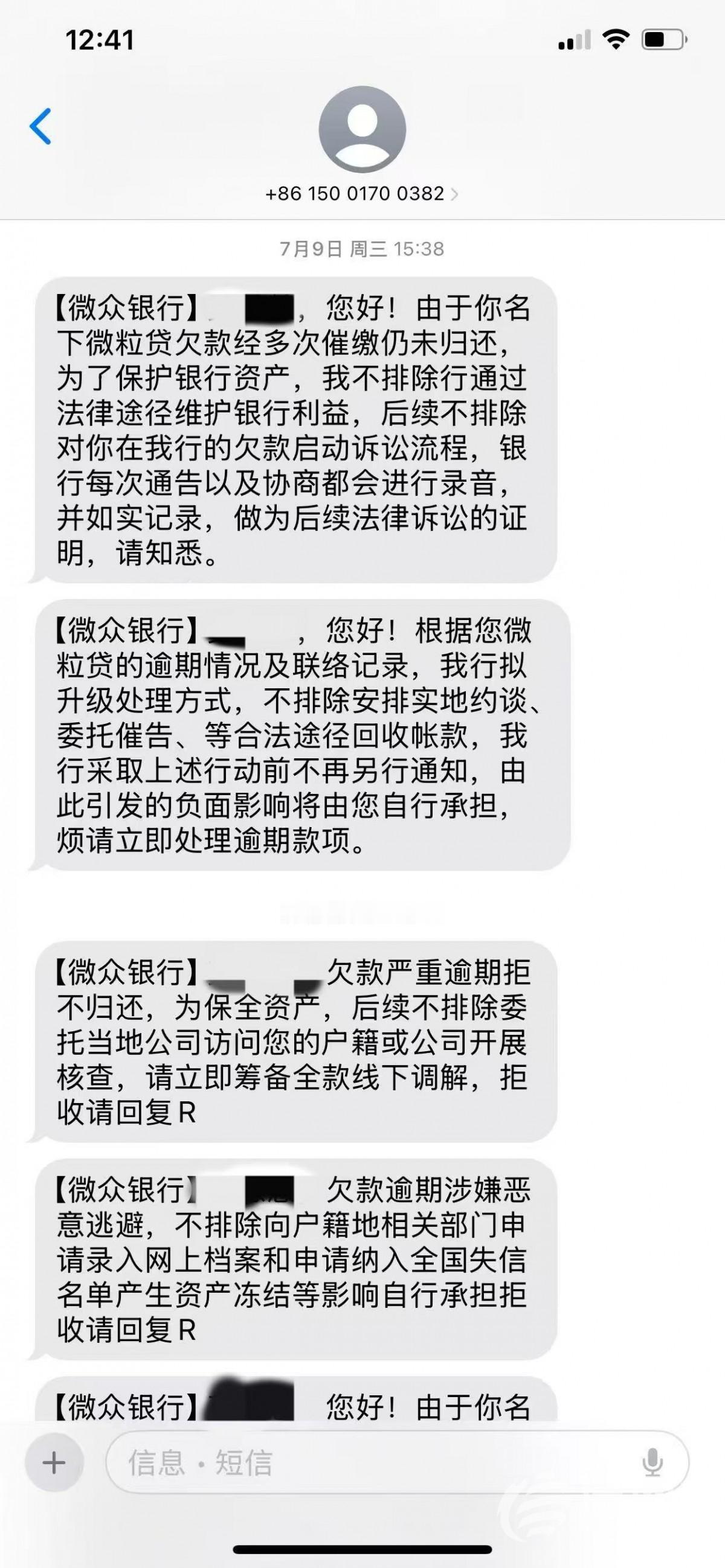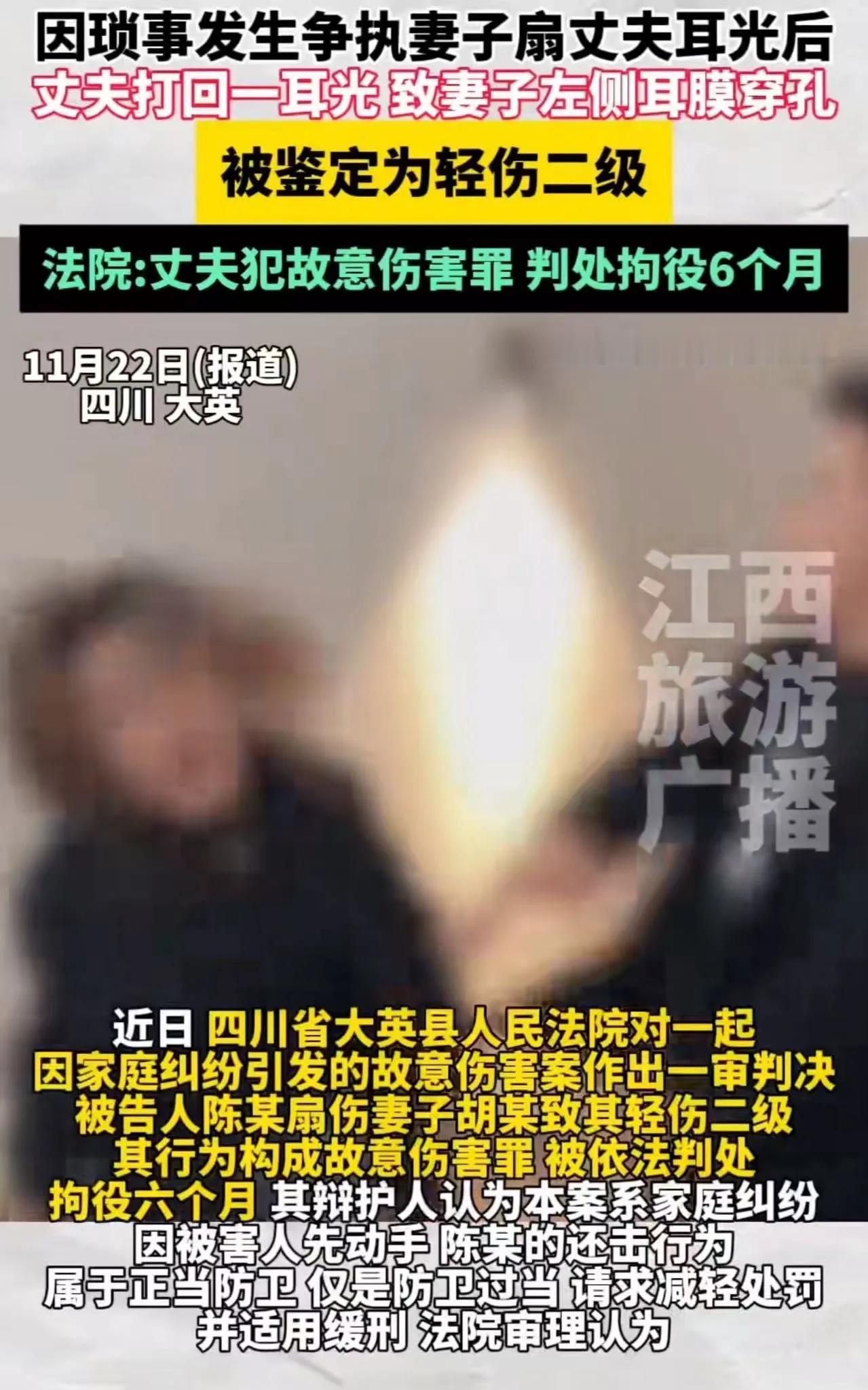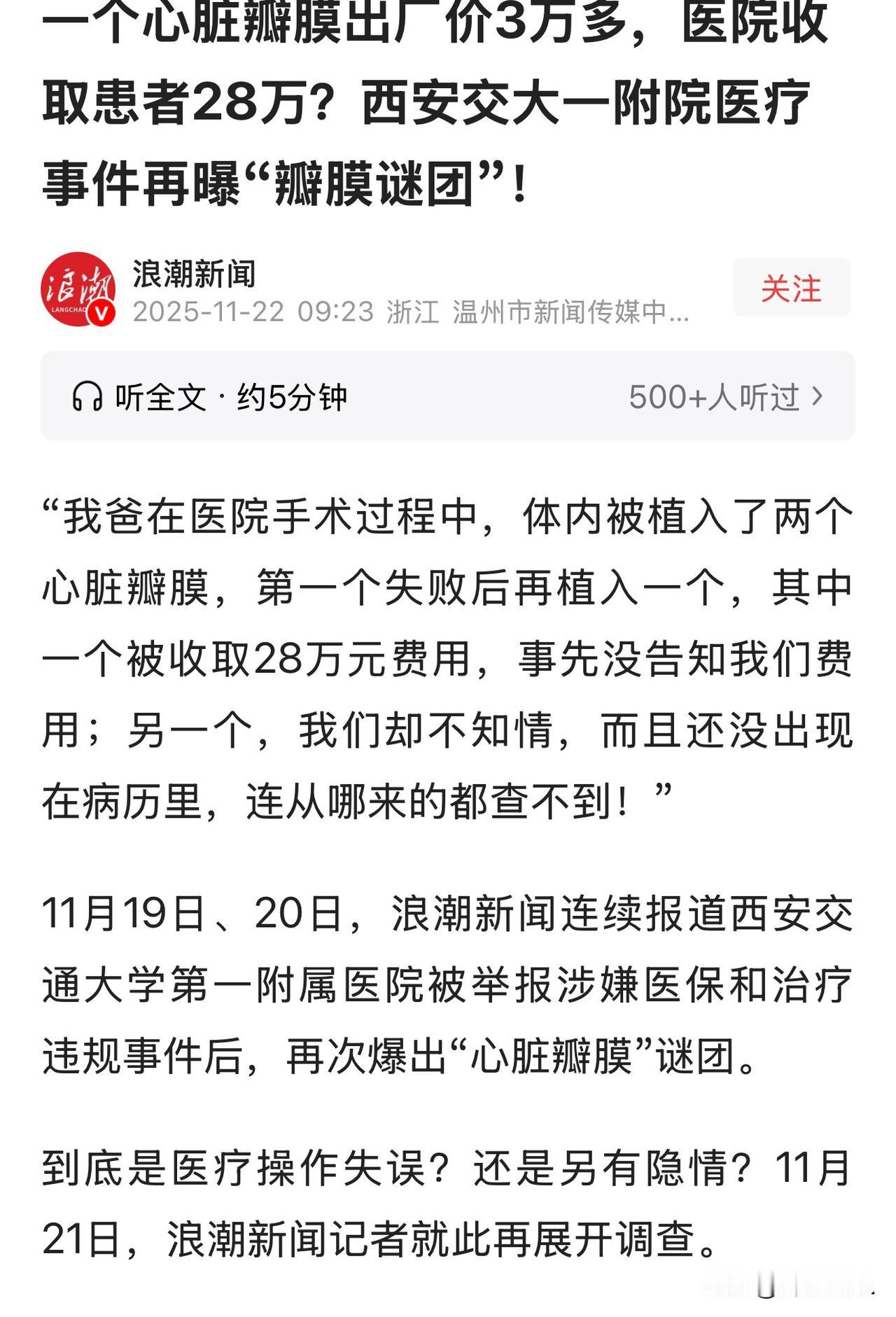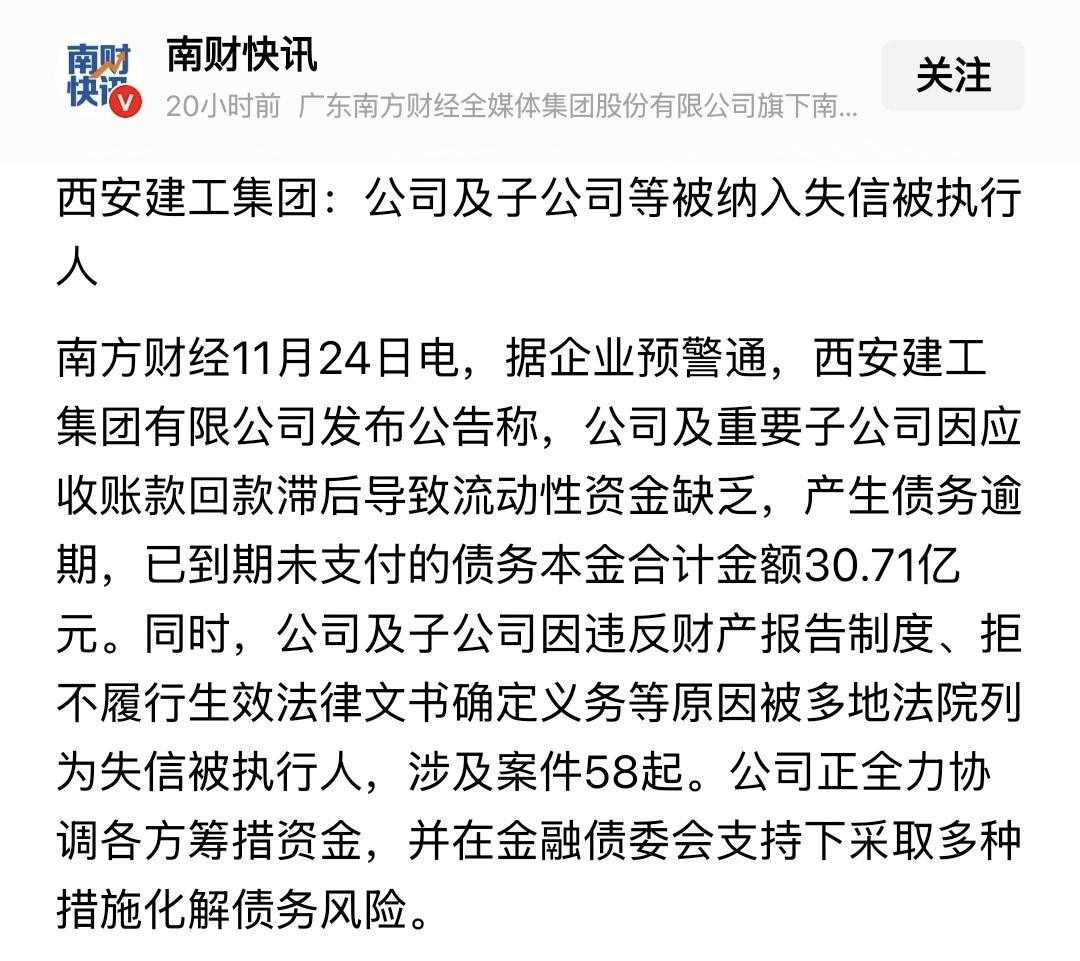1981年11月17日,西安高德隆和妻子偷偷生下了二胎,一个男婴,盼了多年终于如愿。但这份喜悦很快付出高昂代价:他在厂里的职务被撤,夫妻工资从80多元骤降至不足50元,每月还要上交近10元的超生罚款。 那一天刚过立冬,寒气初显。高德隆站在医院门口,脸上写满了复杂的情绪。他刚刚迎来了自己的第二个孩子,一个健康的男婴,心中自然是喜悦的。 可这份喜悦如同被乌云遮住的阳光,还未来得及照亮生活,就被现实的阴影拦腰斩断。他和妻子没有报批,悄悄生下了二胎。 消息传出后,他在国营厂的职务被立即取消。夫妻俩的工资从原本的80多元骤降至不到50元,每月还要扣除近10元作为超生罚款。 在那个年代,计划生育如铁律般横亘在千家万户的命运之上。国家的政策如山一般沉重,每一个背离政策的选择都注定要付出代价。 高德隆不是第一位,也不是最后一位面对这种抉择的人。他所在的机械厂,是典型的国营单位,讲究的是规矩和纪律。他的决定在厂里掀起了不小的波澜,领导层在会上严厉批评,职工们私下议论纷纷。 回望当时的社会环境,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刚刚吹拂,中国正处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关键时刻。 而与此同时,计划生育政策也逐步走向严格。1979年起,全国开始提倡“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政策逐年收紧,宣传标语贴遍城市乡村。对于像高德隆这样的普通工人来说,这不仅是政治要求,更是生活的赌局。 他不是对政策毫无认知,而是顶着压力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家庭的传统观念在他心中根深蒂固。儿子的出生对他而言,是血脉的延续,是家族未来的希望。他知道后果,却依然选择承担。 高德隆的家在西安市郊的一个老旧职工院里,一排排红砖灰瓦的平房,屋内陈设简单,靠着妻子做点缝纫补贴家用。 工资被扣、职务被免后,生活压力骤增。孩子的奶粉钱、家里的煤球费、冬天添置棉衣的支出,每一笔都需要仔细盘算。他们开始缩衣节食,甚至卖掉了家中一件旧收音机,只为补贴家用。 邻居们的态度复杂,有人同情,有人批评,也有人暗暗佩服他的胆量。那几年,街道上经常能看到宣传车,大喇叭循环播放“只生一个好,政府来养老”的口号。 张贴的海报上,红底白字,孩子抱着书本笑得灿烂。可现实中,许多家庭仍旧在子嗣问题上摇摆不定。高德隆的决定,在某种意义上成了那个院子里的一个传说。 生活的重压并没有打垮这个家庭。他的妻子每天清早就坐在缝纫机前,一针一线地赶工。高德隆则转做了厂里的杂工,扫地、搬运、跑腿,什么都干。 他从不抱怨,嘴里常说“孩子是自己的,苦一点怕什么”。在那个物资匮乏的时代,夫妻俩用双手死死守住了家。 然而,命运却在多年后对这个家庭施加了更沉重的打击。1998年11月4日,儿子高明在一起校园相关冲突中不幸被7名未成年人殴打致死。 那一天,高德隆如往常一样去接孩子,却只等来噩耗。儿子的遗体躺在医院的急救室,满身伤痕,已无生气。这个曾违抗政策带回来的孩子,就这样在17岁那年陨落了。 案件经过两年审理,2000年8月宣判。主犯王星因未成年被判处有期徒刑,其他涉案者送往工读学校。高德隆仅获得3.2万元赔偿,其中主犯家属仅赔3000元。 他最不能接受的,是凶手家属始终没有一句道歉。法院的判决像是对他伤口的再次撕裂,让他感到无力与愤懑。 他从此沉默寡言,辞去工作,远离人群,到西安一所寺庙做杂工。他没有剃度出家,只是每天默默干活,挑水、扫地,日复一日。 寺里的僧人说,他常坐在后院石阶上发呆,眼神空洞,像是失去了灵魂的壳。他曾努力通过清修平息内心的痛苦,但悲伤和怨恨却在他体内悄然滋长。 从1998年到2000年,他开始频繁出入五金商店,采买爆炸物材料。他用铵梯炸药、雷管、钢珠等物品制作装置,将仇恨一点点转化为现实的计划。他将目标锁定在那些他认为应对此负责的人身上。 2001年,他制造了两起爆炸事件,造成7人受伤。虽未造成人员死亡,但社会震动极大。警方调查受限,一直未能锁定嫌疑人。 直到2004年1月26日,他制造“1·27连环爆炸案”再次引发关注。礼品盒伪装的爆炸装置被安放在凶手家属住处和医院门口,引发多起爆炸,造成多人受伤和财产损失。 案发后警方迅速追查,最终将他抓获。2004年,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爆炸罪和非法买卖枪支弹药罪判处高德隆死刑。他提出上诉,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维持原判。2005年1月13日,他被依法执行枪决,终年59岁。 从1981年偷偷生下一个孩子,到1998年失去挚爱,再到2005年伏法告别,高德隆的一生仿佛被命运反复碾压。 他曾是一个坚定守家的父亲,也曾是一个努力疗伤的苦人,最终却走向极端。他的命运,终以悲剧收场,却在时间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