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一生养了33个家妓,68岁时,不幸感染风疾。他看着如花似玉的家妓说道:“我已经年老,你们都嫁人去吧!”不料,一个叫樊素的女孩当即跪倒,哭着请求白居易留下她。 唐代士大夫蓄养家妓是当时社会风气,可白居易这次遣散,绝不是一时兴起的决定。风疾发作时,他半边身子僵硬发麻,连抬手翻书都要靠仆人帮忙,更别提像早年那样,和家妓们围坐庭院里赏荷、听曲、赋新词。 他心里算得明白,自己年近古稀,风疾又反复发作,说不定哪天就撒手人寰,这些姑娘最大的不过二十岁,最小的才十五六岁,总不能让她们跟着自己耗到最后,落得无依无靠的下场。他说让她们嫁人,是真真切切替这些女孩的往后打算——那个年代,女子若没有夫家依靠,要么被卖给青楼,要么只能沿街乞讨,日子比烂泥还难捱。 樊素这一跪,把白居易也闹得眼眶发热。这姑娘十三岁就进了白家,天生一副好嗓子,唱《杨柳枝》时,调子婉转得能把院角的柳枝都唱得轻轻晃。白居易早年写“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把她和擅长跳舞的小蛮并提,连好友元稹来访,都要特意嘱咐“让樊素唱首新曲来听听”。 旁人都觉得家妓不过是主人的玩物,可樊素心里清楚,白居易待她不一样。那年她娘在乡下得了急病,是白居易连夜派管家送了五十两银子和御医;她想学写诗,也是白居易每天抽出半个时辰,手把手教她认平仄、辨韵脚。这些年相处下来,早不是冷冰冰的主仆,更像互相牵挂的亲人。 樊素哭着说的不是“求您别赶我走”,是“您现在连端碗药都费劲,我走了谁照顾您?谁陪您说说话?”这话戳中了白居易的软处。他遣散家妓时,满脑子想的都是姑 娘 们的未来,倒忘了自己如今有多需要人陪。 风疾发作时,他常常躺在床上一整天没人说话,连窗外的鸟叫都觉得吵,可樊素在身边时,会读他早年写的诗,会跟他说院子里的牡丹开了几朵,日子就显得没那么难熬。可他还是摇了头,从袖袋里摸出一个沉甸甸的荷包,说“这里面是我给你攒的嫁妆,足够你找个老实人家,不用在我这受这份苦”。 樊素没接那个荷包,依旧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熬药,把药汁滤得干干净净才端到床边;白居易想晒太阳,她就搬个小凳坐在旁边,慢慢给他讲街上听来的新鲜事。 白居易拗不过她,只好不再提遣散的事,只是偶尔看着她忙前忙后的身影,会忍不住叹口气:“是我耽误你了。”樊素总说:“若不是您,我早就在乡下饿死了,哪有现在的日子?” 后来的几年里,白居易又陆续遣散了其他家妓,唯独没再提让樊素走。他的风疾越来越重,有时连话都说不清楚,就握着樊素的手,在她掌心写自己想表达的意思。他晚年写的诗里,好几次提到樊素,有“病共乐天相伴住,春随樊子一时归”的句子,字里行间全是依赖。 直到白居易75岁去世,樊素的名字才从他的诗文中消失。有人说她后来在洛阳的尼姑庵落了发,也有人说她守着白居易的旧宅,把他的诗整理成册,不管哪种结局,都藏着她对这份情谊的看重。 很多人聊起白居易,总盯着他“诗魔”的名号,或是争论他蓄养家妓的对错,却忽略了这些藏在诗句背后的小事。他不是完美的人,蓄养家妓是时代局限,可他能跳出“主人”的身份,替家妓的未来着想;樊素也没有困在“家妓”的标签里,用陪伴回报知遇之恩。 这份在封建等级制度里生出的真心,比“离离原上草”更动人,也让我们看到,无论哪个时代,人与人之间的体谅与牵挂,从来都是最珍贵的东西。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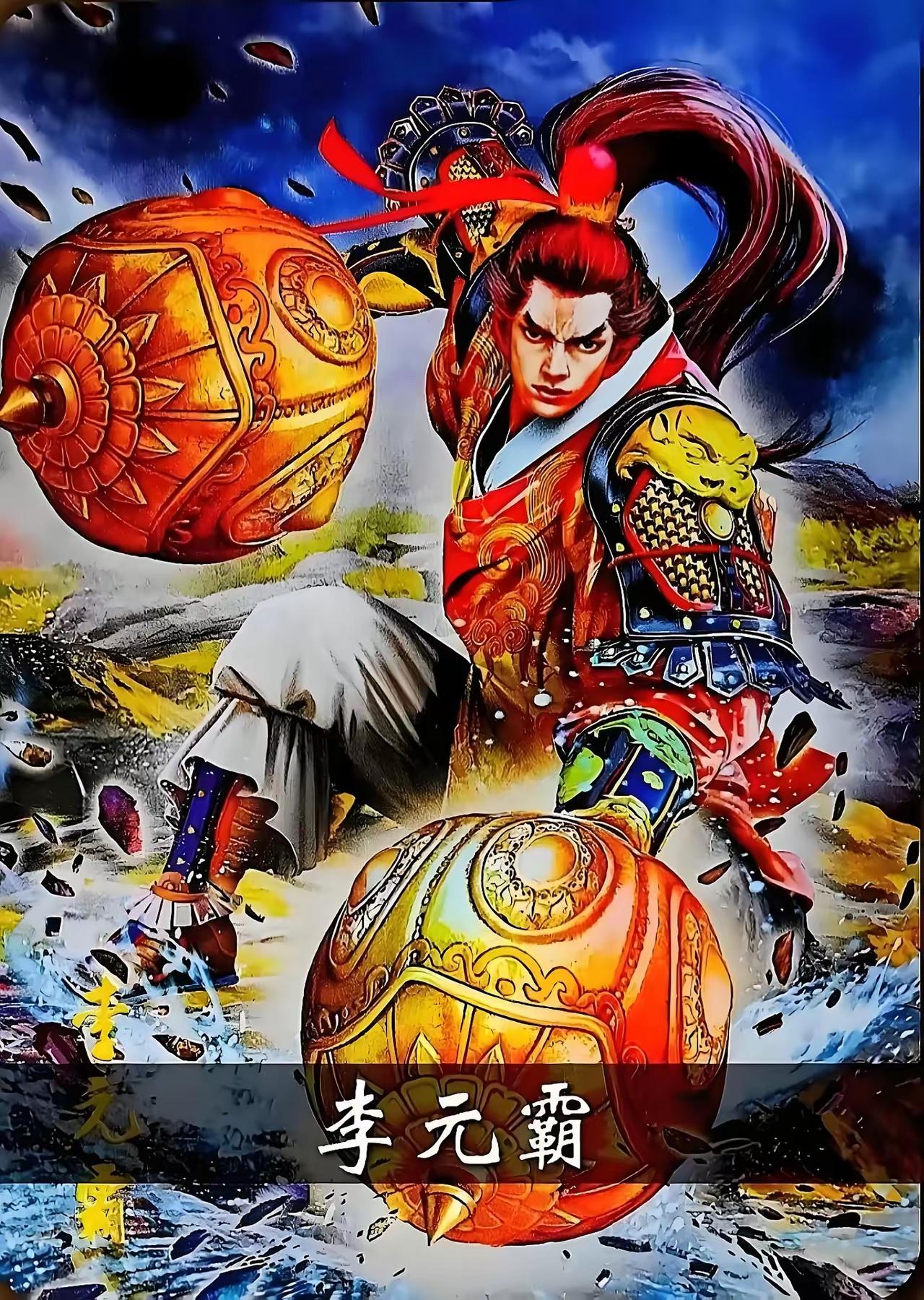
评论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