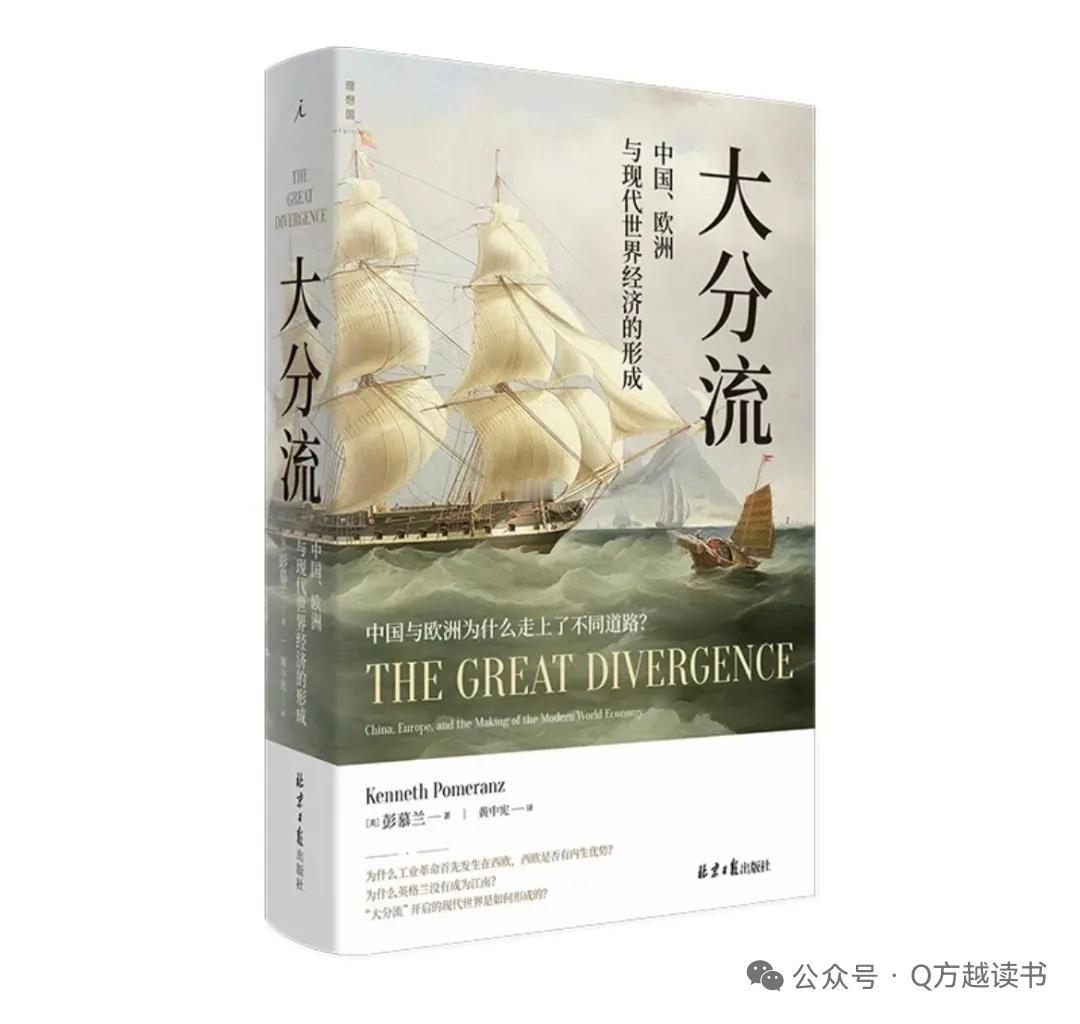你可能很难相信:在工业革命爆发前夜,中国的江南和英国的英格兰,生活水平、农业效率、手工业规模,甚至奢侈品消费水平,都惊人地接近。这不是“强行抬高”,而是美国历史学家彭慕兰在《大分流》中用大量数据揭示的事实。 长久以来,我们被灌输一种叙事:西方天生先进,制度优越、科技领先,注定要引领世界。但彭慕兰反问:“如果欧洲真有那么多优势,为什么直到19世纪才突然甩开中国?”他的答案出人意料——不是制度,不是文化,而是一场“地理与运气的合谋”。 简单说,英国赢在两样东西上:煤和殖民地。英格兰的煤矿靠近工业核心区,开采成本低;而中国最富庶的江南,离山西煤矿千里之遥。更关键的是,美洲殖民地为英国提供了巨量棉花、木材和糖——相当于凭空多出一个“海外国土”,缓解了本土生态压力。 彭慕兰估算,殖民地资源相当于为英国节省了2500万至3000万亩耕地,比英国全国耕地还多! 换句话说,如果没有美洲,英国很可能走上和江南一样的道路: 精耕细作、人口密集、内卷化发展,却难以突破能源与土地的天花板。这颠覆了什么?它戳破了“西方必然崛起”的神话,把历史从“宿命论”拉回“偶然性”。 工业革命不是欧洲文明的自然果实,而是在特定时空下,资源、地理与全球联系共同作用的结果。当然,也有学者质疑彭慕兰“低估了制度的力量”。比如现代企业制度、产权保护、国家能力等,在英国工业化中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但即便如此,《大分流》的价值在于:它让我们重新思考——落后不是原罪,领先也未必是天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