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乌鲁木齐市的一小伙子不顾家人反对,以8万块的天价租下废弃电影院。朋友们都说:“疯了吧,一块没人要的地方能干啥?” 1989年乌鲁木齐街头尘土飞扬,一小伙子背着借来的3万块,推开废弃电影院锈蚀铁门,踩着碎石往前走。家人拉胳膊劝阻,朋友围上来摇头叹气:这破地方年租8万,扔进去准赔光。可他咬牙签下租约,脑中已盘算摊位布局。谁知,这块“没人要的地”竟成亿元帝国起点?一桩看似疯癫的决定,如何逆转人生? 那年头,改革开放的春风刚吹进新疆,乌鲁木齐街头小摊贩多得像过江之鲫。米恩华这小伙子,1958年生在山东泰安一个回族家庭,高中毕业后1979年调到乌鲁木齐,先在“三整顿”办公室干了会儿,1980年转到城管办当市场检查员。每天他骑车穿街走巷,管着那些流动摊点。卖羊肉串的维族大叔,摆布料的汉族阿姨,手工艺人扛着毡帽篮子,东奔西跑。街头乱哄哄,摊位一夜间冒出来,城管追着赶,商贩东躲西藏。米恩华看在眼里,琢磨着得给这些小买卖找个窝,既整顿秩序,又让买卖顺溜。 八年公职,工资不高,日子紧巴巴。米恩华不甘心一辈子铁饭碗,1988年他一咬牙,辞职下海。跟父亲要了700块,东挪西借凑齐3万,注册了乌鲁木齐市华凌工贸公司。先从卖童鞋玩具起步,小铺面里货架上堆满彩球布娃娃,月入勉强过千。可这让他摸清了市场味儿:老百姓要实惠,商贩要稳当。转眼1989年春天,乌鲁木齐经济开发区规划推开,闲置地多起来。米恩华听说南郊红山露天电影院废弃两年,围墙斑驳,银幕架子歪斜,没人问津。他觉得这儿位置好,靠近主路,人流量大,适合办市场。 管理部门负责人徐勋文一口咬定年租8万,不讲价。那数字搁当时,够普通公务员工资50倍。米恩华兜里才3万,还得贷款5万凑齐。家人一听,客厅里锅碗瓢盆乱响,父亲拍桌子说这钱够吃几年,母亲抹着眼泪劝再想想。朋友圈子更热闹,有人上门堵门,端着茶杯摇头:疯了,这破地蚊子成堆,冬天冻成冰,能成啥气候?米恩华听着这些话,没多争辩。他深知风险大,可改革开放大潮下,机会就藏在闲置地里。不试试,一辈子窝着没出路。 就这样,米恩华签下租约,成了这块地的主人。改造红十月市场时,他雇工人清地,刷墙,搭摊位框架。入口拱门用红漆刷亮,里面分200个摊位,走道宽敞,灯光拉线点起。开业前,他挨家访商贩,拉来服装、日用品、小吃摊主。维族阿姨卖手工艺,汉族大叔推羊肉串车,本地农户扛蔬菜筐。市场一开张,人流就涌进来。摊位上孜然味儿飘,布料抖开花样多,玩具区小孩围着转。租金低,管理松,商户尝到甜头,很快满档。 第一年盘账,米恩华坐小桌翻本子,8万租金全收回来,还多出几十万。那是1989年全国职工平均工资41倍,搁谁都得乐。红十月市场名声传开,游客慕名来,买吃的穿的用的,生意红火。米恩华不光收租,还帮商户出主意:办小吃节比手艺,搞手工展销拉人气。商户们说,这地方靠谱,不像街头风吹雨打。市场里汉族、回族、维族商贩混一块儿,买卖兴隆,带动周边经济活络起来。这不光是米恩华的私活儿,更是改革开放下个体户的缩影。 可好景不长,1992年乌鲁木齐规划局通知,原址要建公园。米恩华没抱怨,顺势迁址西大桥一片荒地。那儿风沙大,土坡起伏,他带队平地,钉摊位,几个月新市场拔地而起。位置更好,靠近主干道,摊位从200扩到更多。两年过去,收入达600万,成交额破亿。华凌公司就这样壮起来,从小市场到连锁超市,米恩华一步步走实。改革开放政策好,让像他这样的年轻人有空间施展。市场搬迁两次,没拖后腿,反倒借势升级,促成新疆商贸腾飞。 回看米恩华这路子,接地气。起步时公职稳当,他却敢扔碗下海;租地时别人说疯,他咬牙往前拱;市场红火后,没躺平,又抓规划调整的机遇。8万租金搁今天小菜,可1989年那是真金白银,赌对了就是翻身。华凌集团如今是新疆商界骨干,员工上万,辐射西北。米恩华没忘本,投教育、扶贫困,办助学项目,帮500多个孩子上学。这份担当,合了我们的调性:个人富了带动大家富,实干兴邦。 故事说到底,靠的是顺势而为。改革开放40多年,新疆经济从计划到市场,变了天。米恩华这类企业家,抓住了个体经济起步的尾巴,办市场、建超市,拉动就业,稳民生。市场不是死板摊位,而是活络经济脉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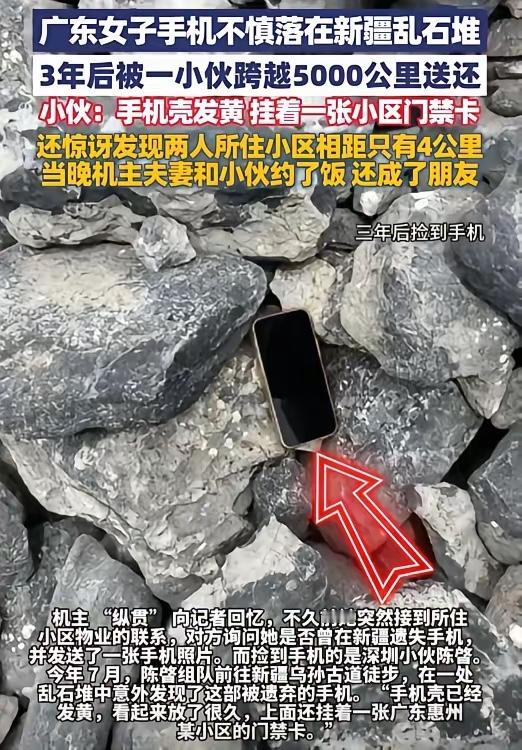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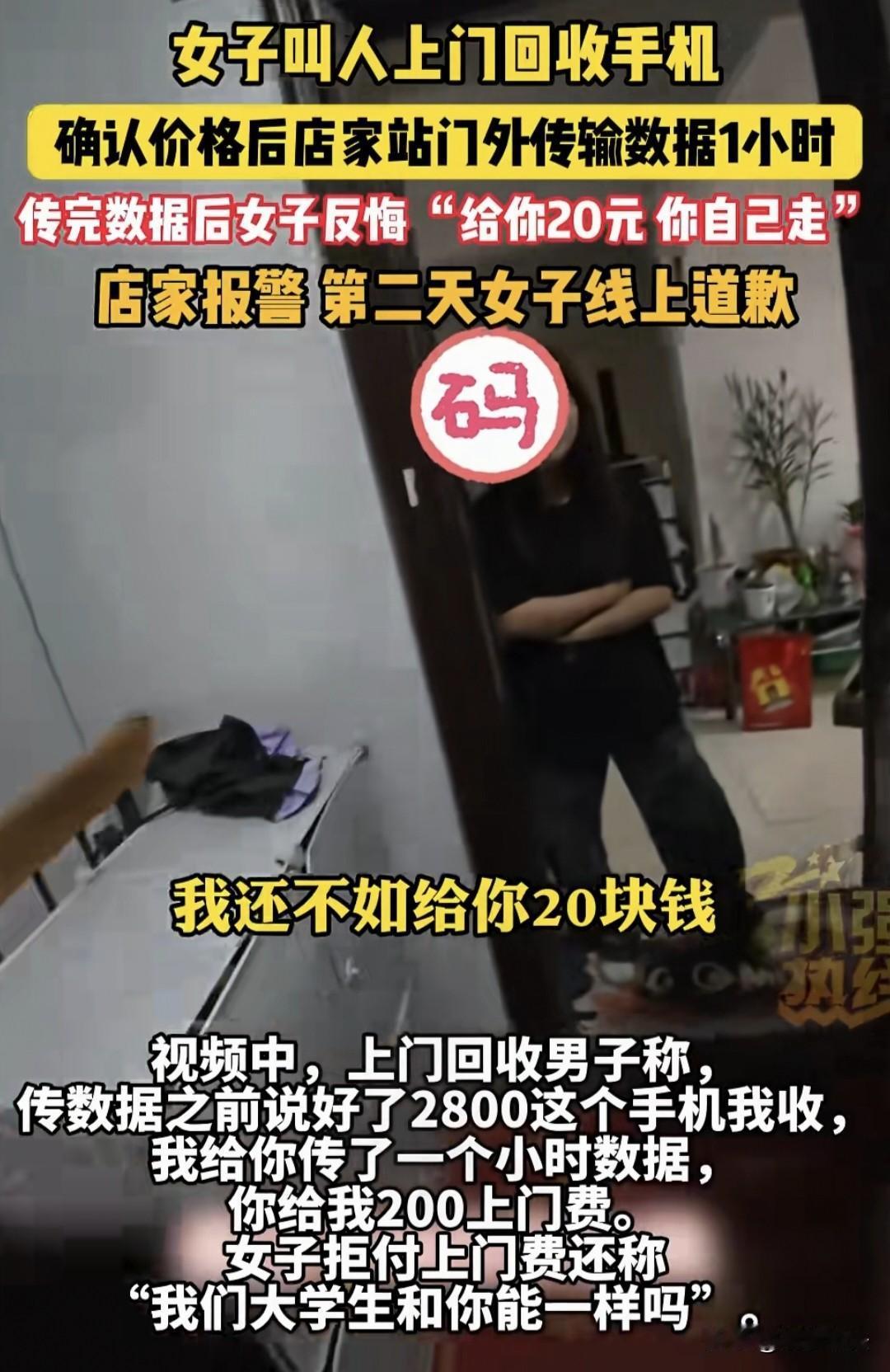



评论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