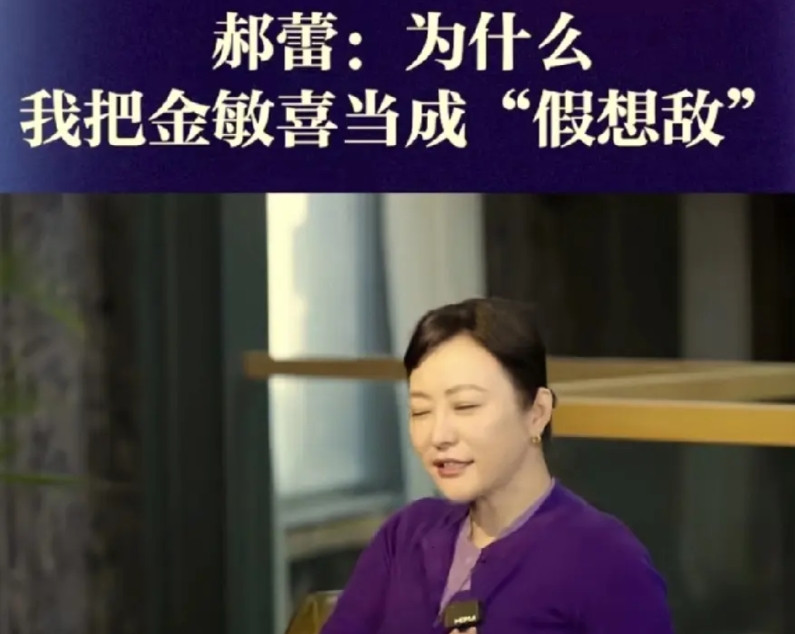演员于和伟说:“我上大一的时候,有天家里来电话,说我大姐去世了,肺癌,听到这个消息后,我愣坐着,没有眼泪,按理说那么亲的姐姐,去世了应该去哭,应该很难过,那我怎么就没有眼泪呢?” 那时候于和伟刚考上上海戏剧学院,是家里第一个走出抚顺老家的大学生。接到电话时,他正和同学在宿舍整理书本,听筒里母亲的声音沙哑得像被砂纸磨过,重复了三遍“你大姐走了”,他才反应过来。手里的《表演基础》啪嗒掉在地上,页面摊开着,可他一个字也看不见,耳朵里嗡嗡作响,宿舍里同学的说笑声、窗外的车鸣声,突然都变得很远很远,像隔了一层厚厚的棉花。 他就那么坐在床沿上,背脊挺得笔直,眼睛盯着地面的瓷砖缝,脑子里一片空白,又像被什么东西塞满了,堵得发慌。按理说,大姐是家里最疼他的人啊。小时候家里穷,兄弟姐妹八个,他排行最小,大姐比他大十多岁,几乎是看着他长大的。家里的窝窝头,大姐总把上面最暄软的部分掰给他;冬天他的棉鞋漏了脚趾,大姐连夜把自己的旧棉袄拆了,给他纳新鞋底;他上学交不起学费,是大姐跟着同乡去砖厂搬砖,手掌磨出一层又一层茧子,硬是凑够了钱,拍着他的肩膀说“弟你要好好学,将来出人头地”。 他上戏报到那天,大姐特意赶了几十里路来送他,手里拎着一个布包,里面装着她连夜烙的饼、缝补好的衣物,还有一沓皱巴巴的零钱。“在外面别委屈自己,想吃啥就买,不够就给家里打电话。”大姐的声音带着乡音,眼里满是不舍,他那时候光顾着兴奋,忙着和同学打招呼,连句像样的道别都没说,哪知道那竟是最后一面。 宿舍里的同学看出他不对劲,递过来纸巾,问他要不要请假回家。他摇摇头,嗓子像被堵住了,发不出一点声音。那几天,他照样去上课,照样和同学一起吃饭,只是吃饭没味道,听课记不住内容,夜里躺在床上,眼睛睁着到天亮,脑子里全是大姐的样子——砖厂里汗流浃背的背影、灯下纳鞋底的侧脸、送他时挥动的手。可无论怎么想,眼泪就是掉不下来,他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铁石心肠,是不是对不起大姐的疼爱。 直到一周后,他收到家里寄来的包裹,里面是大姐生前给他织的一件毛衣,针脚有些粗糙,却是他最喜欢的藏蓝色。他把毛衣抱在怀里,指尖触到那些密密麻麻的针脚,突然就想起大姐打电话时说的话:“弟,毛衣快织好了,等你放假回来就能穿,保暖。”那一刻,所有的麻木瞬间崩塌,他抱着毛衣蹲在地上,哭得撕心裂肺,像个迷路的孩子,积攒了一周的悲痛终于找到了出口。原来不是不难过,是悲痛太重了,重到压得眼泪都流不出来,要等一个契机,才能彻底释放。 后来于和伟在访谈里说,大姐的去世,让他一夜之间长大了。他开始懂得珍惜,懂得责任,知道自己肩上扛着的,不仅是自己的梦想,还有大姐未完成的期盼。他在演艺圈摸爬滚打多年,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只要想起大姐当年的付出,想起那件藏蓝色的毛衣,就有了坚持下去的勇气。他说:“我现在每次回老家,都会去大姐的坟前坐一会儿,跟她说说话,告诉她我挺好的,没让她失望。” 那种突如其来的麻木,从来都不是冷漠,而是最深沉的悲痛。当亲人的离去超出了心理承受的极限,大脑会下意识地启动“保护机制”,用麻木抵挡瞬间的崩塌。而那些没流出来的眼泪,早已化作心底最柔软的牵挂,成为前行路上最温暖的力量。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