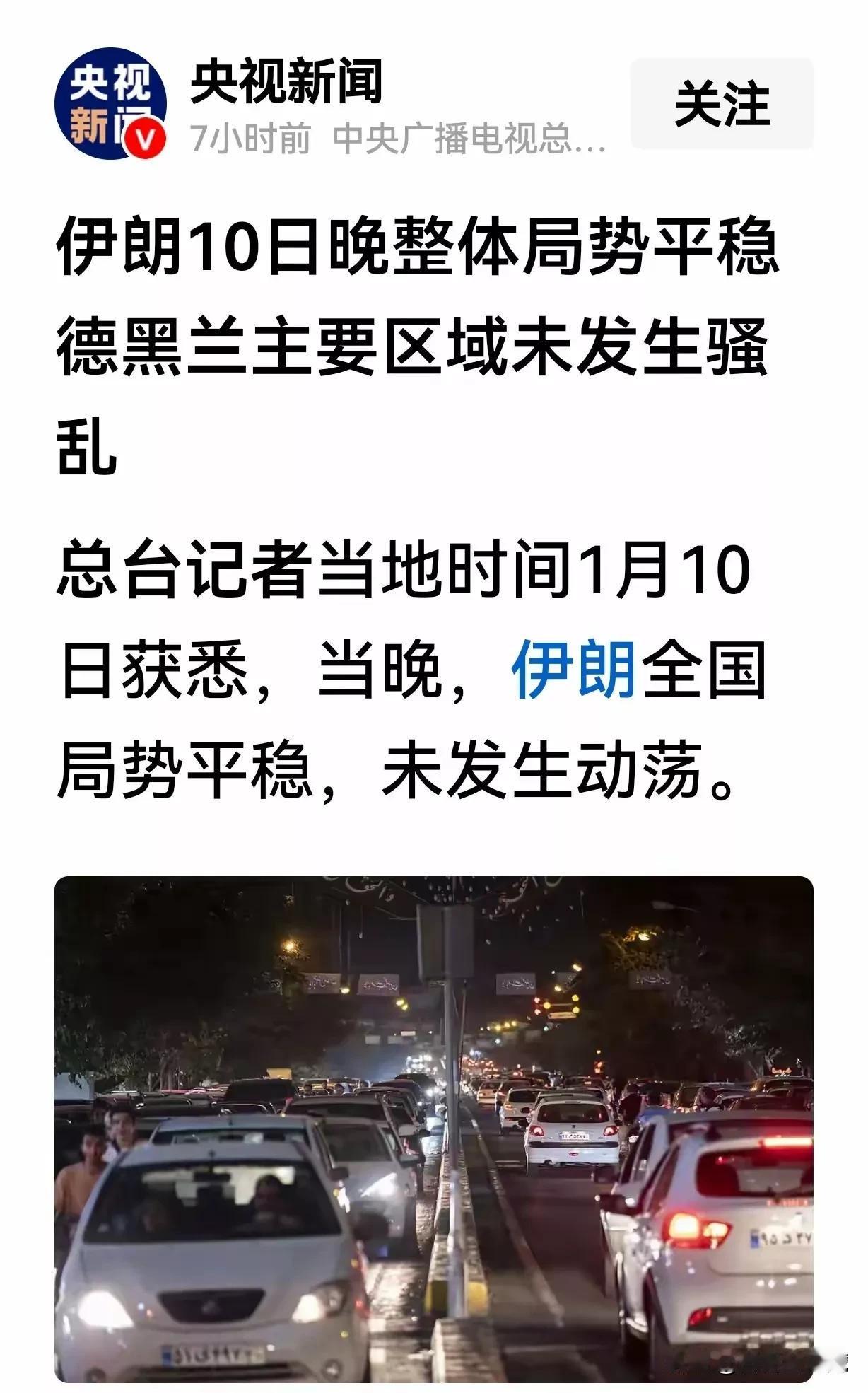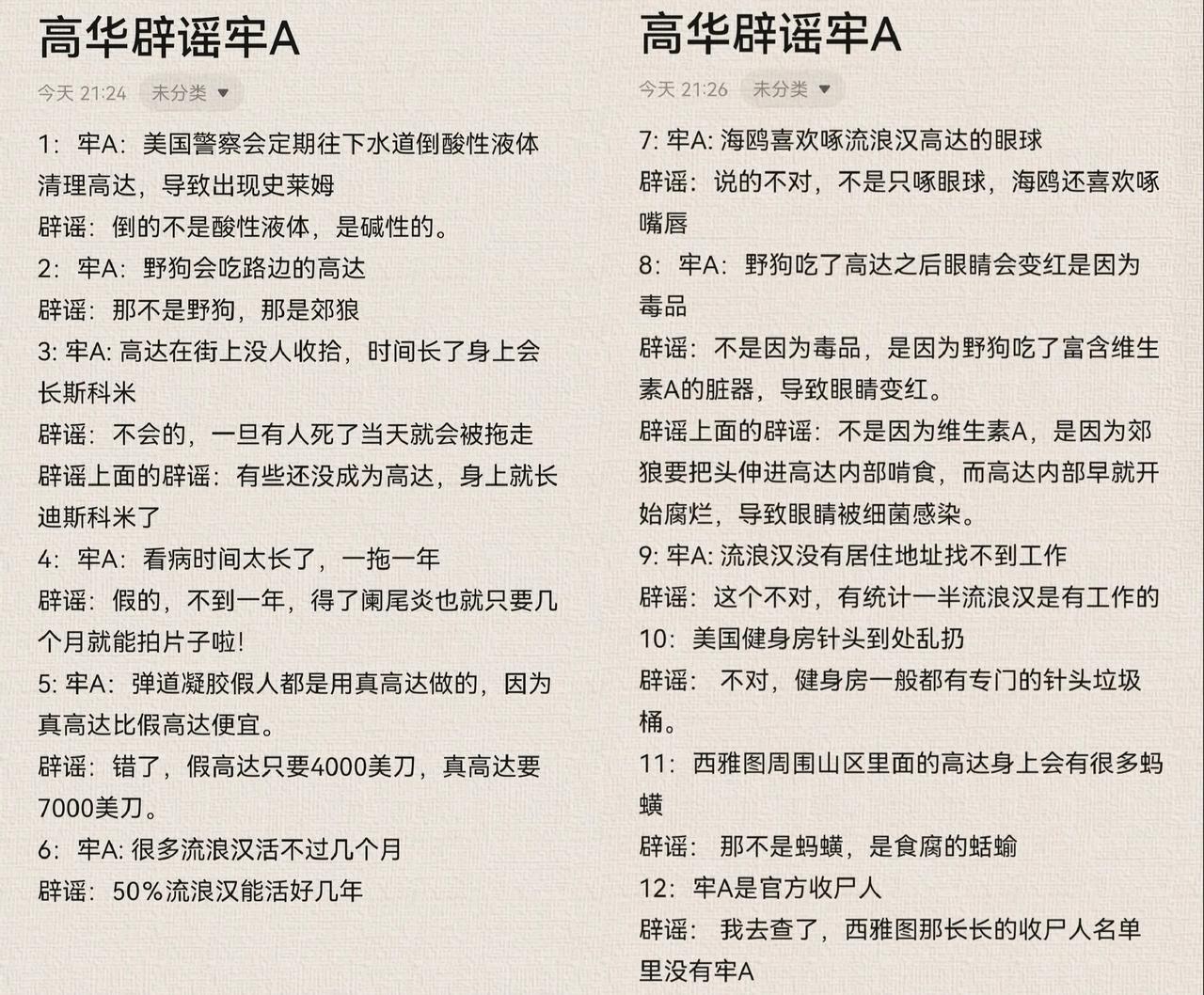我童年最喜欢的小狗,小狗总能凭着脚步声认出我,每次放学回家,我还没跨进大门,它就欢天喜地从院子里冲出来,围着我的腿蹭来蹭去、打转撒欢。
日子一天天过,小狗越长越大,和我的感情也越来越深,我知道狗的寿命也就十几年,肯定等不到我成家立业、为人父母的那天,但总觉得它至少能陪我熬过青春期、走到成年。
可就在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下午,我放学回到家,却没看到它像往常一样蹦出来接我,房前屋后找了个遍都没见踪影,我急得跑去问母亲,她才低着头说,今早把它卖掉了。
那一刻我像被雷劈中一样,怎么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反复问了母亲好几遍,才不得不接受我的小伙伴再也回不来的事实。
我躲在房间里大哭了一场,晚饭也赌气不吃来抗议,可看着母亲满脸愧疚、手足无措的样子,到嘴边的埋怨话终究还是咽了回去。
后来这些年,我经历了太多聚散离合,有家人的天人永隔,也有朋友的渐行渐远,这才慢慢琢磨明白,童年那次突如其来的失去,其实早就藏着所有关系结束的模样。
只是成年人的世界里,没人会替你做结束的决定,得自己拿主意,还得学着坦然接受所有结果。 五个月前我向公司提了离职,做这个决定前,我纠结内耗了好久,总忍不住把离职后的日子往最坏了想,迟迟不敢下定决心。
一方面怕失业后没着没落,没了稳定收入该怎么生活,要是一时半会儿找不到下一份工作又该怎么办?
另一方面更让我犯难的是不知道怎么开口,怕同事私下议论猜测,怕领导极力挽留阻拦,更怕一个月的漫长交接期会过得尴尬又煎熬。
那时候后者给我的压力其实比前者还大,我本就不擅长跟人打交道,尤其是面对领导,每次谈话都觉得浑身不自在,像被人盯着审视一样局促不安。人一旦露出怯懦的样子,心里的退堂鼓就会敲个不停,那段时间我总想着再等等,等个更合适的时机再说。
可每次这样放过自己,心里的失望和懊悔就多一分,直到提离职的前一晚,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突然想通了——等所谓的“好时机”的时候,日子不也在一天天白白溜走吗?原来结束一段关系根本没有什么最佳时机,当下就是最好的时候。
第二天上班,我没再犹豫,鼓起勇气跟领导提了离职。 离职的消息在办公室传开后,果然引来不少挽留、猜测和打听。我一直默默提醒自己,别被这些杂音带偏,记住自己离职的初衷就好。办完所有离职手续,走出公司大门那天,我深吸了一口气,没有预想中的狂喜,也没有莫名的失落,反倒有种前所未有的平静。
我退了所有工作相关的群,却忘了两个私下的生活群——一个是和前同事们一起约饭的饭搭群,还有一个是周末一起打球的球友群。离职一星期后我回了老家,某天早上醒来翻看手机,才发现自己被这两个群悄悄踢了出来,那一刻的感觉挺奇妙的,没有愤怒也没有委屈,反倒有种意料之中的释然。
成年人的世界本就如此,很多关系都是建立在共同的场景之上,一旦场景消失,关系慢慢松动甚至走向终结都是难免的。不管是主动退出还是被动出局,本质上都是这段关系走到了终点。不用觉得自己先提出结束就占了上风,也不必因为被“踢出局”就觉得没面子、丢了尊严。一段关系里,退场的方式固然重要,但更难得的是离场时能保持一份从容和体面。
其实仔细想想,任何一段关系都有它存在的使命。我们和亲人、伴侣、朋友、同事,甚至和一只猫、一条狗、一盆花的相遇,不管关系深浅,都是为了在彼此的生命里扮演一个特别的角色,戏演完了,角色自然也就该退场了。
而且人都是会变的,要么是自己变了,要么是对方变了,要么就是大家一起变了,变得不再契合、不再同频。
小孩子可以拉勾发誓“一百年不许变”,但一个成熟的大人心里都清楚,所有关系都有期限,哪怕是密不可分的血缘关系,终有一天也会因生死而终结。
对永恒的幻想,其实就是给人生埋下痛苦的种子,世间好物本就不坚牢,就像彩云易散、琉璃易碎,我们赤条条来到这个世界,最后也注定什么都带不走。
一段关系的价值,从来不是看它持续了多久,而是看它是否在相处的日子里,给彼此带来了成长和滋养。
当这段关系不再有滋养,反而开始消耗彼此的精力和情绪时,我们该做的就是坦然接受现实,心怀感激地回望过去,然后悄悄转身离开。要是明知不合适还紧抓不放,只会让自己和对方都活得疲惫不堪,最后只剩下互相消耗的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