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交契无老少,论交何必先同调。”从前总信这句诗里的坦荡,觉得真正的朋友该是山高水长,经得起风雨,也容得下窘迫。直到钱包里的票子成了衡量情谊的标尺,才在一次次拉扯里看清,有些关系,脆得像秋后的玻璃,碰一下就碎成满地寒光。

老周来电话时,我正在给孩子换奶粉。他的声音带着罕见的局促,说开厂资金周转出了问题,想借十万块应急,还特意强调“三个月准还,利息按银行来”。我们是穿一条裤子长大的发小,他当年揣着两百块闯深圳,是我在火车站帮他拎着破旧的行李箱;我结婚时凑不齐首付,他把准备买房的钱先打给了我。这份情分,我一直记在心里。挂了电话,我翻出银行卡,看着余额里刚发的工程款,咬咬牙转了过去。妻子在旁边叹气,说“亲兄弟明算账”,我却拍着胸脯保证,老周不是那样的人。
头一个月,他每天都给我发消息,说工厂的进度,讲回款的希望,字里行间都是感激。第二个月,消息渐渐稀疏,我问起情况,他只说“再等等,快了”。第三个月,约定的还款日到了,我犹豫了三天才拨通电话,那边却支支吾吾,说“资金还没回笼,再缓两个月”。我没好意思多问,挂了电话才发现,他的朋友圈已经对我设了权限。妻子没再多说什么,只是默默把孩子的奶粉换成了平价的牌子,那一刻,我心里像塞了团浸了水的棉絮,沉得发慌。

后来我才从共同的朋友那儿得知,老周的工厂早垮了,他拿着借我的钱还了高利贷,还偷偷买了张去海南的机票。我再打电话,提示已是空号;发微信,红色的感叹号刺得眼睛疼。有次在菜市场撞见他的堂弟,对方含糊地说“他也不容易”,我张了张嘴,想问句“我们的情分就值十万块吗”,最终却只挤出一个僵硬的笑。那些年一起在大排档喝啤酒、说心事的夜晚,那些互相扶持的日子,忽然就成了褪色的旧照片,风一吹就散了。
同事小李也曾遇到过类似的事。他的大学同学结婚,说彩礼还差三万,哭着求他帮忙。小李刚工作没几年,省吃俭用攒了点钱,架不住对方的软磨硬泡,还是借了出去。婚后那同学像变了个人,朋友圈里晒着蜜月旅行的照片,却对借钱的事绝口不提。小李急着交房租,上门去要,对方的妻子却翻了脸,说“当初是你自愿借的,现在催什么催”。那天小李回来,坐在工位上闷头抽烟,说“我不是心疼钱,是觉得十几年的同学情,怎么就这么廉价”。

楼下开水果店的张姐,更有过切肤之痛。她的闺蜜要开美容院,找她借二十万,还写了借条。可美容院开张不到半年就倒闭了,闺蜜直接搬了家,断了所有联系。张姐拿着借条去法院,赢了官司却拿不到钱,每次说起这事,她都红着眼圈说“早知道这样,当初就算撕破脸,也不该借”。可谁又能预知未来呢?那些借钱时的信誓旦旦,那些推心置腹的信任,在利益面前,往往不堪一击。
前几天整理旧物,翻出老周当年送我的钢笔,笔帽上的划痕还清晰可见。我试着给他的旧手机号发了条消息,没指望回复,只是想说“钱不用急着还,要是难,说一声”。消息石沉大海,就像我们再也回不去的从前。我忽然明白,借钱这件事,从来都不是简单的数字往来,而是情谊与现实的博弈。不借,怕伤了情分;借了,怕丢了朋友也没了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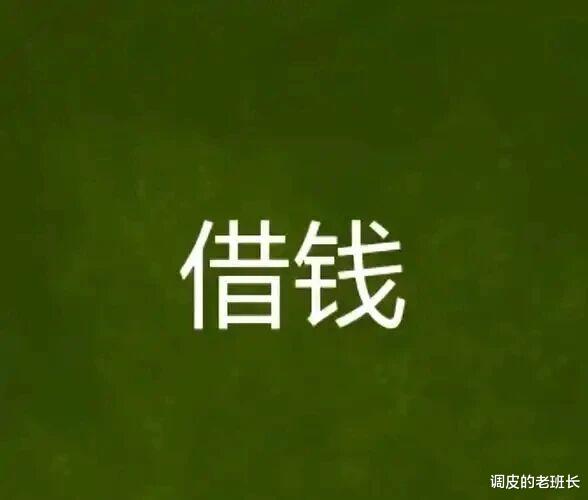
夜渐渐深了,窗外的路灯投下昏黄的光。那些因钱而生的隔阂,那些因借而起的遗憾,像细密的雨,打湿了人生的路。我们总以为朋友是避风港,却忘了有些风浪,恰恰是朋友带来的。后来再有人借钱,我学会了委婉拒绝,也承受着对方转身离去的落寞。这世间的情谊,或许本就脆弱,而钱,不过是撕开真相的那把刀。“论交何必先同调”的洒脱,终究抵不过“谈钱伤感情”的现实,这大概就是成年人世界里,最无奈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