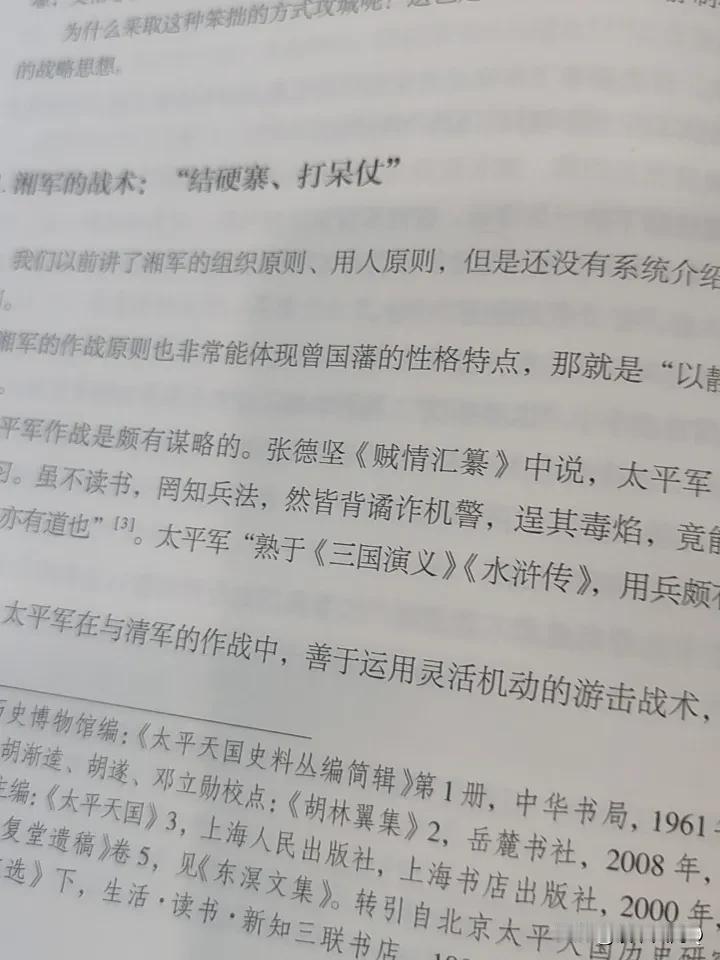这故事的主角,叫陈威远。搁 康熙 四十二年那会儿,绝对是个人物。你想想,镇边大将军,在西北跟敌人拼了二十年命,那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这天,老将军六十大寿一过, 康熙 爷准了他告老还乡。
二十年没回家了,老将军心里那叫一个念想。可等他骑着那匹跟他一样老的老马,晃悠悠回到老家祖宅门口,整个人都懵了。 这哪是家?这简直是“鸠占鹊巢”现场。 祖宅斑驳的木门上,挂着别人的灯笼。东院墙干脆被人凿了个大豁口,贴着墙根,硬生生“长”出来一排土坯房,把半个院子都给吞了。院里那口老井,旁边堆满了不认识的柴火和杂物。
跟着他回来的老管家,当场就哭了,抹着眼泪说:“将军,咱们家被恶霸钱豹给占了!这家伙在县里一手遮天,连县太爷都护着他!” 换成你我,估计当场就得炸了。我这提着脑袋给朝廷卖命,回来连家都没了?不抽刀子砍了他? 可陈威远是啥人?在战场上,越是箭在弦上,他心里越是静如止水。他听完,没吭声,只是背着手在门口站了一会儿,看了看那排刺眼的土坯房。 他没去县衙敲鼓,也没去找钱豹拼命。 他转身进了马厩,从包袱里摸出两包从京城带来的好茶叶,提着,溜达出门了。 他干嘛去了?他去找他的老部下,一个在驿站当 驿丞 的小官。

啥叫“驿丞”?放今天,大概就是个管收发公文、接待过往官员的招待所所所长。官不大,但消息灵通。 俩老哥们儿见面,分外亲切。驿丞赶紧沏上好茶。陈威远呢,就坐在院子里,跟他拉家常。可这家常拉的,水平就太高了。 他一句没提房子被占的事,净是聊西北战场的风沙,聊康熙爷召见他的时候,龙颜大悦,赏了他一件 黄马褂 ,说那料子是真好。又聊起当年手下的几个兵,这个现在在 知府 衙门当师爷,那个在 巡抚 大人帐下当 校尉 …… 驿丞是多机灵的人,一听这味儿,心里就有数了。这哪是聊天,这是在“点名”呢。 俩人喝茶的院子,就在驿站边上,人来人往,总有几个衙门的差役溜达。这耳朵一听,得了,了不得了。
“听说了吗?陈老将军回来了!” “哪个陈将军?” “还能哪个?皇上赐过黄马褂的那个!听说他跟知府、巡抚大人都是过命的交情!” 话这东西,一传开,就跟长了腿一样。 很快,全城都知道了。 这话传到钱豹耳朵里,他“切”了一声,冷笑。他一个地头蛇,在本地盘踞了十几年,县令都是他“喂”熟的。他怕这个? “一个退了毛的老兵,能有多大能耐?吓唬谁呢?” 钱豹觉得这老头是在虚张声势。为了立威,也为了彻底断了陈威远的心思,他干了个更绝的事——派了十几个流氓,拉了几车土,当着街坊四邻的面,把陈家院里那口老井给填了! 这是赤裸裸的挑衅。意思是:这宅子是我的,你陈威远连口水都别想喝。 陈威远在二楼窗户看着,还是没动静。他就等,等这条蛇自己把毒牙全亮出来,等蛇背后的洞也露出来。

钱豹得意了没两天。 第一记重锤,砸下来了。 他开在城里最大的那个赌场,突然被知府衙门的人给端了。知府亲自带队,账本、银子、人,一锅端。 钱豹彻底傻眼了。他赶紧去找县令,结果县令大门紧闭,托人带话:“偶感风寒,不见客。” 钱豹哪知道,这事儿的根子,就在那个小小的驿丞身上。老将军一走,驿丞立马给知府大人写了封请安信。信里啥也没说,就是问候起居,末了提了一句:“属下的老上司陈威远将军回乡了,提起您,还说您是国之栋梁。”
知府一看信,冷汗都下来了。陈威远是谁?那是皇帝跟前的红人!他的老上司,那不就是我的老祖宗?这事儿县令敢护着,我敢吗?知府立马装病,不,是立马亲自出马,把钱豹最肥的产业给办了。 这叫“撇清关系”,也叫“主动示好”。
第二记重锤,来得更快,也更狠。 赌场被封,钱豹只是断了一只手。他还有更赚钱的买卖——贩私盐。这可是掉脑袋的生意,他上下打点得水泄不通,连巡抚衙门都有他的“兄弟”。 可就在赌场出事的第三天,他刚从海上运来的一船私盐,还没上岸,就被巡抚衙门的水师给扣了。带队的,是巡抚大人的亲信 校尉 。
这下,钱豹是彻底慌了神。他想不通,自己的关系网怎么突然就破了? 他还是太嫩了。他忘了陈威远喝茶时聊天的内容。那位巡抚大人,当年就是陈威远帐前的 校尉 ! 老上司受了这么大的气,当小弟的能坐得住?这都不用老将军开口,一个眼神,下面的人就得把事儿办得明明白白。 这就是陈威远的路数。他从来不跟你玩“一楼”的“打打杀杀”,他直接在“顶楼”跟你玩“政治”。 钱豹这种只懂欺软怕硬的,连对手在哪儿都摸不清。

五天时间,钱豹的赌场没了,私盐生意黄了,县令这个“保护伞”也装病“死”了。他这才明白,自己惹上的是个什么神仙。 他彻底崩溃了,半夜三更,疯了似的跑到陈家祖宅——不,现在是他的宅子——在柴房里拼命地翻。他想起来了,当初占这宅子时,好像有个带锁的旧箱子。 他撬开箱子,里面赫然躺着一块乌木牌匾,上面用 朱砂 龙飞凤舞地刻着几个大字,旁边还有一个鲜红的刺眼大印! 钱豹不识字,但他认识那印!那是 康熙 爷的玉玺大印! 他手抖得跟筛糠一样,捧着那块木牌,连滚带爬地冲到县衙。
县令一见这牌子,吓得从床上直接滚了下来,脸都绿了。 牌子上写着:“祖宅世业,钦此。” 这哪是宅子?这是圣旨!这是皇家的体面! 占这宅子,跟谋反有啥区别? 第二天一早,钱豹带着全家老小几十口,在陈家祖宅门口跪成一排,头磕在青石板上,砰砰响,哭着求老将军饶命。 陈威远这才慢悠悠地走出来,把钱豹扶起来,话说得云淡风轻:“哎,都是乡里乡亲,抬头不见低头见。和睦最重要嘛。” 宅子还回来了,填平的井也挖开了,多占的院子也退了。一场泼天大祸,就这么消弭于无形。

陈威远赢了吗?赢了。他靠的是什么?《大清律例》吗?不是。他靠的是他当过大将军的“身份”,靠的是他认识知府、巡抚的“人脉”,靠的是康熙爷赏的“特权”。 说白了,这是一场“特权”对“恶霸”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