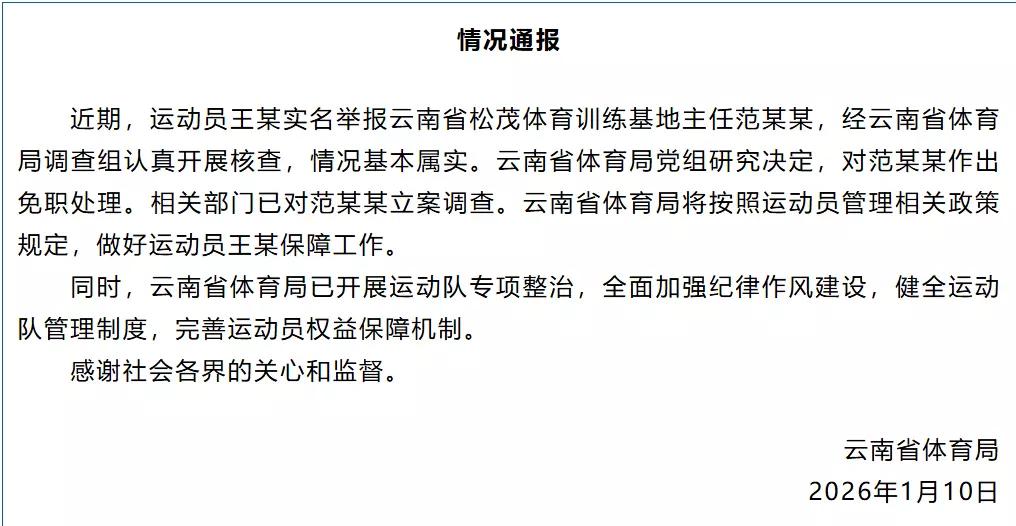表姐苏静宜打来电话,想借我的路虎揽胜回山东老家。
她只说要开几天,还车时会加满油。
还车那天,她不仅加满了油,还硬塞给我1个厚厚的信封,里面是2500块钱。
这远远超出了油费和过路费,我心里掠过一丝异样。
几天后,1张卡在后备箱里的云南高速收费票据,彻底搅乱了我的思绪。
她明明说是回山东,票据却指向千里之外的边境。
我满心疑惑地查看了行车记录仪。
当10天6000公里的数据在屏幕上展开时,我屏住了呼吸。
01
周六的早晨,窗外飘着细雨。
我正窝在沙发里翻看汽车保养手册。
手机突然震动起来,屏幕上跳动着“苏静宜”三个字。
她是我大姨家的女儿,比我年长六岁。
接起电话,那头传来她略显沙哑的声音:“景轩,你现在在家吗?”
“静宜姐,我在家,有什么事吗?”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背景里似乎有隐约的车站广播声。
“姐想跟你借个东西。”
“什么东西?你说。”
“你那辆路虎……能借我开几天吗?”
我愣了一下。
我那辆路虎揽胜是去年才提的,落地将近百万,平时自己都舍不得多开。
“姐,你要用车?”
“嗯,想回老家看看你大姨和姨父。”
她停顿了一下,补充道:“我那辆旧车开长途不太放心,你姐夫的车又刚好在修理厂。”
这个理由听起来很合理,但我总觉得她的语气有些飘忽。
“行吧,你什么时候要?”
“我明天坐高铁过去,直接从你那里开走就好。”
挂断电话后,我摩挲着车钥匙,心里泛起一丝疑虑。
静宜姐嫁得不错,姐夫周振宇做建材生意,家里应该不缺车才对。
但转念一想,或许她只是想开辆好车回老家,在亲戚面前有些面子。
第二天中午,苏静宜准时到了。
她穿着一件米色的风衣,素面朝天,整个人看起来瘦削了不少,眼角的细纹比记忆中深了许多。
“姐,你最近是不是太累了?”我递给她一杯热茶,“脸色看着不太好。”
她接过茶杯,勉强笑了笑:“人到了这个年纪,哪有不累的。”
她低头抿了一口茶,没有继续这个话题。
“车钥匙给我吧,我想下午就出发。”
“这么着急?吃了饭再走吧。”
“不了,你大姨说炖了汤等我。”
我把钥匙交给她,帮她把那个不大的行李箱放进后备箱。
“姐,大概用几天?”
“一周左右,最多十天。”
她坐进驾驶座,系好安全带,从车窗探出头来:“放心,姐一定完好无损地还给你。”
我点点头:“路上注意安全。”
车子缓缓驶离,消失在小区转角。
我站在原地,总觉得她最后的笑容里,藏着说不出的疲惫。
十天后的傍晚,我接到了苏静宜的电话。
“景轩,我今晚把车还给你,你在家吗?”
“在的,姐你直接开过来就行。”
到家时,她已经等在楼下了。
让我意外的是,姐夫周振宇也来了,就站在她身后半步的位置。
“景轩,这次麻烦你了。”周振宇笑着递过来一支烟。
“姐夫客气了。”我摆摆手,心里却有些纳闷——他的奔驰不是送修了吗?
苏静宜把车钥匙放在我手心:“车洗过了,油也加满了。”
“姐,你太见外了……”
话没说完,她又塞过来一个厚厚的信封。
“这是油钱和过路费,你收着。”
我捏了捏信封,厚度明显不对:“这太多了,来回一趟老家哪用得了这么多。”
“该给的。”
她的语气很轻,却带着一种不容拒绝的意味。
说完这句话,她便转身拉开了周振宇那辆奔驰的车门。
“我们先走了。”
车子很快驶入夜色,我站在原地,看着尾灯的光晕渐渐模糊。
手里的信封沉甸甸的。
回到家,我打开信封数了数,整整两千五百块。
从我们这里开车回她老家,往返最多八百公里,油费过路费加起来,一千块都绰绰有余。
她多给这么多,是什么意思?
我走到阳台,看着楼下已经停好的路虎。
车确实洗得干干净净,在路灯下泛着柔和的光泽。
后座上放着一箱老家的苹果,应该是大姨让她带给我的。
我打开后备箱,里面收拾得一尘不染。
就在我准备关上箱盖时,角落里一张皱巴巴的纸片引起了我的注意。
那是一张高速公路的收费票据,卡在了后备箱垫子的缝隙里。
我抽出纸片,借着灯光仔细看。
票据上的字迹有些模糊,但依然能辨认出“云南省”、“昆曲高速”以及一个陌生的地名。
云南?
静宜姐的老家,分明在山东。
02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辗转难眠。
那张来自云南的票据,像一根细小的刺,扎在我的思绪里。
第二天一早,我决定查看行车记录仪。
我的车安装的是前后双录的记录仪,除了视频,还能记录完整的GPS行驶轨迹。
平时我几乎从不查看这些数据,但今天,我必须弄清楚苏静宜这十天究竟去了哪里。
取出存储卡,插入电脑。
文件夹里按照日期排列着密密麻麻的视频文件。
我直接点开了轨迹记录文档。
当那条清晰的线路图在屏幕上展开时,我感到一阵眩晕。
记录显示,车子第一天就从我这里出发,一路向西,经过郑州,当晚抵达西安。
第二天,从西安开往成都。
第三天,进入云南,最终停在一个名为“勐洛”的边境小镇。
车子在那里停留了整整三天。
之后,又沿着几乎相同的路线,用三天时间返回。
十天,总里程超过六千两百公里。
这根本不是回山东老家的路线。
我盯着地图上那个陌生的云南小镇,勐洛,距离缅甸只有几十公里。
她为什么要去那里?
为什么要对我撒谎?
犹豫片刻后,我拨通了大姨的电话。
“景轩啊,怎么想起给大姨打电话了?”
“大姨,我就是问问您和姨父身体怎么样。”
“好着呢,你姨父最近还天天去公园下棋。”
寒暄了几句,我试探着问:“大姨,静宜姐前几天是不是回老家看你们了?”
电话那头安静了一两秒。
“是啊,回来了,待了两天就走了。”
“她……一切都好吗?有没有说要去别的地方?”
这一次,沉默的时间更长了些。
“景轩啊,”大姨的声音压低了些,“静宜她……她有些自己的事。你就别多问了,好吗?”
“大姨……”
“大姨这边还有点事,先挂了啊。”
电话里传来忙音。
我握着手机,心里的疑惑非但没有减轻,反而更加沉重了。
大姨显然知道些什么,却在刻意隐瞒。
接下来的几天,我一有空就查看行车记录仪里的视频片段。
一段在西安境内的录像显示,苏静宜把车停在一所大学的老校区门口,静静坐了半个多小时,期间多次抬手擦拭眼角。
另一段在四川的盘山公路上,车内录到她很轻的自语:“就快到了……再等等……”
进入云南后,有一段白天的视频。
她把车停在路边,额头抵在方向盘上,肩膀微微耸动。
她在哭。
这些无声的影像,拼凑出一个充满悲伤的旅程。
我找到了车子在勐洛镇停留期间的一段视频。
那是抵达后的第二天傍晚,她坐在车里,手里拿着一张泛黄的照片。
眼泪无声地滑落,滴在照片上。
她对着照片,声音哽咽地低语:“十八年了……我终于来了……”
“海阳,对不起……真的对不起……”
海阳?
我从未听说过这个名字。
“那个孩子……也是你的孩子……我对不起你们……”
孩子?
静宜姐不是只有一个女儿周薇吗?今年正好十八岁。
她说的“那个孩子”,是谁?
03
一个尘封已久的记忆碎片,突然划过我的脑海。
十八年前,我十四岁,静宜姐二十岁,正在省城读大学。
那年暑假,她没有像往常一样回老家。
母亲曾去大姨家,回来时脸色凝重,夜里我听见父母低声交谈。
“静宜那孩子,怎么这么糊涂……”
“小点声,别让景轩听见。”
“大姐他们坚持要她去处理掉,真是造孽……”
当时年少的我懵懵懂懂,如今串联起来,一个令人心颤的猜测逐渐成形。
那个叫“海阳”的男人,那个从未被提及的“孩子”……
周末,我开车回了趟老家。
大姨见到我时,脸上的惊讶掩饰不住。
“景轩?你怎么突然回来了?”
“想您了,回来看看。”
姨父出门了,家里只有大姨一人。
她给我倒了茶,坐在我对面,手指无意识地搓着围裙的边缘。
“大姨,”我放下茶杯,决定开门见山,“我看了行车记录仪,静宜姐根本没回山东,她去了云南。”
大姨的身体明显僵住了。
“她还提到了一个叫‘海阳’的人,和一个……孩子。”
大姨的脸色瞬间苍白,眼眶迅速泛红。
她低下头,沉默了很久很久,久到我以为她不会开口了。
“海阳……全名叫沈海阳。”她的声音沙哑,“是静宜大学时的恋人。”
我的心沉了下去。
“他们……曾经有过一个孩子。”
虽然早有猜测,但亲耳听到证实,仍感到一阵窒息。
“那时候,静宜还在读书,沈海阳家里条件很差,我们做父母的,不能眼看她毁了自己。”大姨的眼泪掉下来,“是我们逼她……去了医院。”
“那沈海阳呢?”
“他知道,但他无能为力。”大姨抹着眼泪,“后来,你姐夫……周振宇找过他,之后他就消失了,再也没出现过。”
“姐夫对他做了什么?”
“我们不知道具体说了什么,只知道他走后,静宜就像丢了魂。”大姨哽咽道,“半年后,她嫁给了周振宇。”
“那这次去云南……”
“两个月前,静宜收到一封信,是沈海阳寄来的。”大姨深吸一口气,“信里说他病了,很重的病,想在……之前,见静宜一面。他在云南那个小镇开了个小诊所。”
“所以静宜姐是去见他最后一面?”
大姨点点头,泪水涟涟:“她瞒着所有人,包括周振宇。她说这是她欠的债,必须去还。”
从老家回来,我的心情异常沉重。
我继续查看记录仪里勐洛镇的视频。
画面显示,车子长时间停在一个挂着“安民诊所”招牌的小屋对面。
有一段视频里,苏静宜从诊所走出来,回到车上,然后压抑地痛哭。
最后一段在勐洛的视频,是临行前的清晨。
天色微亮,她站在车边,面朝行车记录仪的方向,仿佛知道我会看到。
“景轩,如果你看到这段视频……”
她的声音很轻,带着晨间的微哑。
“姐这辈子,最后悔的就是十八年前,没有勇气留下自己的孩子。”
她停顿了一下,眼神望向远处雾气缭绕的山峦。
“现在,姐要去做一个决定。这个决定,或许很多人不理解。”
画面外传来一个当地女人的声音:“沈家嫂子,东西收拾好了吗?”
苏静宜转过头应了一声,又看向镜头。
“景轩,别为姐担心。”
她努力笑了笑,但那笑容浸满了苦涩。
“那两千五百块钱,不是车钱。是姐……在还心里的债。”
视频到此结束。
04
几天后的一个深夜,苏静宜主动打来了电话。
“景轩,还没睡吧?”
“姐,我没睡。”
“你去过老家了,是吧?大姨都跟我说了。”
“姐,对不起,我只是……”
“我知道你是关心我。”她的声音听起来异常平静,“沈海阳,他走了。我离开后的第三天。”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去见了他最后一面,也去看了……那个孩子。”她的声音有些颤抖,“海阳给他起了名字,叫‘沈念’,还给他立了块小碑。碑朝着诊所,他说这样每天都能看到。”
我的喉咙有些发紧。
“我在新碑上,刻了我的名字。”她轻轻地说,“这辈子,我总算给了他们一个名分。”
“姐……”
“景轩,周振宇当年,是用前途和家人威胁海阳离开的。”她的语气忽然变得很冷,“这些事,我都知道了。”
“那你以后……”
“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吧。”她叹了口气,“谢谢你,景轩。这段路,姐总算走完了。”
挂断电话后,我很久没有动弹。
后来,我在网上看到一则很小的新闻。
云南边境小镇一位叫沈海阳的医生病逝,他在当地行医十八年,去世后,许多受过他帮助的村民自发为他送行。
新闻照片里的男人清瘦,戴着旧眼镜,笑容温和。
我想,静宜姐青春里爱过的,就是这样一个人吧。
春节家庭聚会,气氛热闹。
周振宇喝了些酒,搂着苏静宜的肩膀,大声说着当年追求她多么不易。
苏静宜面带微笑,安静地听着,不时给他夹菜。
但在桌下,我看到她的手,紧紧攥着自己的衣角,指节发白。
聚会散场时,我帮她拿外套。
一张折叠的纸片从她口袋里滑落。
我捡起来,瞥见是一张“勐洛镇卫生院短期支援医护报名回执”,日期就在下周。
她接过纸片,轻轻塞回口袋,对我摇了摇头,眼神里有请求,也有决然。
我什么都没问,只是点了点头。
回去的路上,我收到大姨发来的微信。
只有没头没尾的一句:“静宜她打算……”
消息停在这里,没有再继续。
我望向车窗外流动的夜色,想起苏静宜还车那晚,站在路灯下孤单又释然的身影。
有些路,注定只能一个人走。
而有些告别,不是为了离开,而是为了真正开始。
05
收到大姨那条戛然而止的信息后,我握着手机在客厅里踱步了许久。
窗外的夜色已经完全沉淀下来,远处楼宇的灯光像是洒在黑色绒布上的碎钻。
我最终没有回复,也没有追问,仿佛那条未完成的信息是一个需要被小心翼翼对待的缺口。
任何贸然的触碰都可能惊扰到某种正在艰难凝聚的平衡。
接下来的几天里,我尝试着像往常一样投入工作。
处理那些似乎永远也看不完的报表和开不完的会。
但思绪总会不受控制地飘向那个云南边陲的小镇。
以及静宜姐最后看向镜头时,那双盛满疲惫与决绝的眼睛。
一周后的傍晚,我下班回到小区,习惯性地看向车位。
那辆路虎安静地停在那里,金属漆面在夕阳余晖下反射着温润的光。
就在我准备走进单元门时,一个有些熟悉的身影从旁边的花坛边站了起来。
是周振宇。
他穿着一件略显褶皱的衬衫,下巴上冒着青黑的胡茬,眼神里透着一股难以掩饰的烦躁。
“景轩,下班了?”他扯出一个笑容,但看起来十分勉强。
“姐夫?你怎么在这儿,没提前打个电话。”
“路过,顺便想找你聊聊。”他搓了搓手,目光有些游移,“关于你静宜姐的事。”
我心里微微一紧,面上却维持着平静:“上楼坐坐吧,喝杯茶。”
进了屋,我给周振宇泡了杯茶。
他坐在沙发上,身体前倾,双手紧紧握着茶杯,指节有些发白。
沉默在客厅里弥漫了好一会儿,他才像是下了很大决心似的开口。
“景轩,你静宜姐……最近有没有跟你联系过?或者,有没有跟你说过什么特别的话?”
我斟酌着用词:“春节后倒是通过一次电话,聊了些家常。姐夫,是出什么事了吗?”
周振宇重重地叹了口气,把茶杯搁在茶几上,发出“磕”的一声轻响。
“她从老家回来之后,整个人就不太对劲。”
他抬起头,眼睛里布满了红血丝。
“以前虽然也话不多,但家里的事她都打理得井井有条,现在经常坐在那儿发呆,问她也只是摇头。”
“是不是最近太累了?或者,薇薇高考压力大,她也跟着操心?”
“不是这些。”周振宇烦躁地抓了把头发,“我能感觉到,她心里有事,很大的事,而且她在瞒着我。”
他忽然看向我,眼神里带着探究和一丝不易察觉的恳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