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AI写作来临,
我默默地拿出曾经的手写稿,
那有真实写作的印记!
我是千丘生,说点手稿之外的故事给你听…

▲乡村供销社意象老照片
我正儿八经动笔写日记,是在小学三年级的第二学期。
在这之前,我以极大的兴趣写了不少似日记非日记的东东,几经辗转,保留下来的并不多。
现在能见到的文字片段,毫不讲究地写在捡来的处方笺的背面、写在信纸上、写在哥哥姐姐们用剩的笔记本上、写在假期作业本的空白处,甚至写在老师给的用剩的备课纸上。
是谁送的备课纸呢?前边文章提到过,是我小学二年级时,教我们语文(兼班主任)的肖玉生老师和教我们数学的付姗姗老师。
今天拎出来的这篇《骄傲的一个营业员》,也是写在了备课纸上,大约写于刚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

▲我写在备课纸上的小作文《骄傲的一个营业员》
这个小作文,题目似乎改为《一个骄傲的营业员》更恰当些。
那时哪有什么语法概念,主谓宾定状补,一顿糊了去。
文本内容大体如下:
那是去年十一月的一天,我和哥哥去供销社买《唐诗三百首新编》的书。
哥哥向那个卖图书的营业员说:“同志,给我取一本《唐诗三百首》的书看看。”
谁知她那瓜子形的脸一转,用大眼睛瞪了哥哥几眼说:“有多少钱?”
“二元。”哥哥沉重的(地)回答。
那个营业员高大而胖的身子一下子拱下去,取出那本书翻转来一看,说:“还少钱呢,你看,一共要二元二角呢。”
哥哥说:“等一会儿,我回去拿!”
那个怪生(声)怪气的营业员,整了整呢子大衣的衣领,说:“到底要不要?”
“要,要。”哥哥说。哥哥就跟旁边的熟人说:“太红,借我两角钱,我以后还你。”
那个人就掏出两角钱给哥哥,哥哥接下钱只好买了。

▲乡村供销社意象老照片
自从买这本书以后,我一连几个月没有到她那里去买东西。开学的前几天,才到那里买了一瓶墨水和几本练习本。
平时她看到那(哪)个小孩(穿得)破破旧旧,就冷笑别人。她每天下班就去和别的女人打羽毛球。
这个人值的(得)批评,大家都不要向她学习,要向好的一方面学习。

▲当年我哥买的《唐诗三百首新编》,他在书上题字是在十二月。
这篇小作文,纯粹是二年级刚升三年级的小孩子的口水话。
童言无忌,但说的都是当时的真话和实话。
1980年代的歌曲《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有一句唱词:光荣属于八十年代的新一辈。
我在八十年代还是个小屁孩,只觉得:光荣属于供销社的营业员。
那时的营业员不得了啊,是吃居民粮的上班一族。他们养尊处优,牛气哄哄,把“顾客就是上帝”这句话基本抛在脑后,对来购物的人大多时候是爱搭不理的。
那时,农村穿破衣烂衫的人还多,营业员们见到不管大人还是小孩,都先问一句:“你带了多少钱?钱不够就不要来问!”
所以,小时的我学得机灵,当时特别喜欢购买小人书,见到营业员我首先发问:“最近有没有一毛钱一本或两毛钱一本的小人书啊?”
有,就买,没有拉倒。


▲我小时候购买过的一些小人书
供销社里的标语还是要美好一点、抚慰人心才行,就像下边这张意象图里的标语一样:高兴而来,满意而归,百问不烦,百拿不厌。
当然,也不能一概而论,毕竟有些营业员出生贫苦、不忘初心,对老百姓的态度还是可以的。
如同古时人们痛恨科举,却又为科举挤破脑袋一般,1990年代初及之前很长一段时期,相当流行报考包分配的中专学校,很多成绩不错的农村中考生,报考的正是商业系统尤其是供销类专业的学校。

▲乡村供销社意象老照片
然而,时代它变化快啊,改革开放走过十几个年头后,供销社已经式微,风光不再,甚至逐渐解散没落了。
读了几年中专的人,难有分配工作的喜悦之感。打工潮就在此时汹涌而来……
也不知卖书的那位穿呢子大衣、胖胖的瓜子脸女营业员,后来怎样了,也已无处问候。
此后不久,“自选超市”的概念席卷而来。
不管城乡,初次接触超市的人,都会惊问:
“真的可以到货柜里边去自行选购吗?”
“那营业员不会骂死个人?”
“你说的是真的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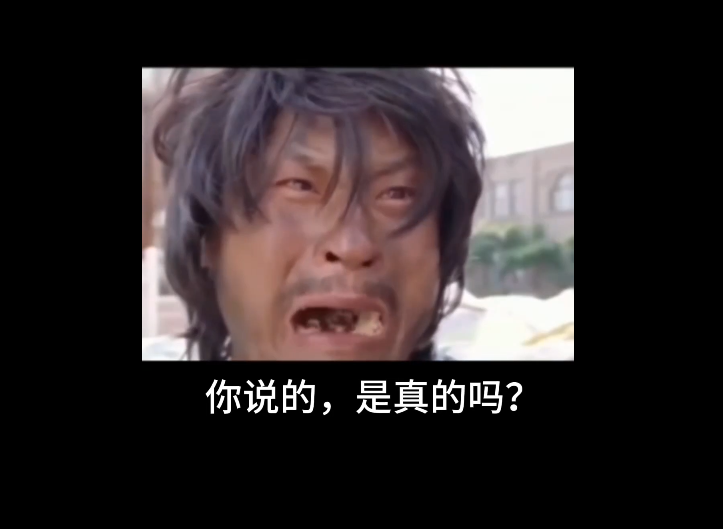
当年,我哥向营业员说:“同志……”
你看,现在主流意识形态正在为“同志”这个词正名。
“供销社”这个词也在正名啊,“你在柜台里卖,我在柜台外买”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时光流转,目前,供销社已然有翻身变样的大好趋势。
人们拭目以待供销社服务三农、助力乡村振兴的新的作用与表现。
文中提到的我哥的同学“太红”,大名叫“王太红”,算是我母亲那边的远房亲戚。
王太红的姐姐叫王太玉,跟我大姐是同学,后来当了老师。
王太红的弟弟叫王太亮,比我大些,虽然我们不是同学,但关系相当好。他曾邀请我去他家做客,在一个叫“江挟垅”的偏远山村,那边离沈从文的老家黄罗寨好像不太远了。
那本《唐诗三百首新编》,由大名鼎鼎的岳麓书社出版。
何曾料到,现今我跟岳麓书社算得上很熟了——
我爱人的表妹夫刘文是岳麓书社的资深编辑,他的“刘博士读书管见”越来越有影响力。
岳麓书社现任总编辑马美著先生,很有出版经营能力,他在读研时我们就熟识了,他一直就叫我“小田”。
马美著当时的同舍刘奇军老师跟我先认得几年,刘老师后来一直在省教育厅工作,曾任湖南省语委办主任。
岳麓书社首席编辑唐浩明先生,是著名作家、学者,曾任湖南省作协主席(现为名誉主席),我跟他在一个国学基金会有诸多交集,我还曾几次前往岳麓书社拍摄采访过他。
唐浩明老先生有时挺随意谦和的,下面这张我跟他的合影,拍于2015年春的一次采访之后。当时他说:“你看,我没戴眼镜来,现在又正是眼袋最大的时候,真对不住了!”

▲我与唐浩明先生的合影,20150316
话说,我哥为什么要买这么一本书呢?
极有可能,是受到他当时的初中语文老师周兴俊的影响。
周兴俊老师传奇一时,是当之无愧的文学青年一枚,他给学生们刻印了不计其数的诗歌散文,还组织了各种乡里少见的文艺活动。
(“刻印”是指用特制的铁笔在钢板上刻写蜡纸,再通过孔版油印进行批量印刷的技术。)
周老师的爱人(当时可能还是女朋友)是外地人,在我们小学教高年级语文,说着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在全是讲土话的村小,听着肯定是个大稀奇啊!
有一次,周老师的爱人拖堂,迟迟不下课,原来是有几个字音很多同学都读不好。我正从她那教室门口过,她就把我拉了进去,让我读,我竟然全都读对了。周老师的爱人一口普通话叨吧着:“你们看看,你们看看,连低年级的同学都读得准……”
也是因缘际会吧,后来的我,岂止是语文课代表,上大学就直接念的是“语文专业”。当然,这是我们的玩笑话,“语文专业”就是中文(汉语言文学)专业。
再说,热血的周老师据说是文武双全,还饶有兴致地教学生武术。
周老师也曾醉后晚归,愤青般踢坏了久叫不开的木质校门。
这就让人联想到了“鲁智深醉打山门”的热血故事。
有故事的青年才俊啊!

▲我哥的初中毕业照,周老师已调离
我哥当时也是深度热爱语文与写作,他在买的那本书上的题字是:文章本无天成,妙手偶得之。
估计也是受到了周老师的影响。不过,宋代陆游的原话是: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
那时,我和我哥晚上同睡一张床,记忆犹新的是,他经常绘声绘色地给我讲睡前故事。后来了解到,那些都是语文或历史课本上的故事,如《桃花源记》《大铁锤传》《负荆请罪》等等。
至今我还珍藏着我哥买的《唐诗三百首新编》,时不时拿出来翻阅一下。
这本书曾经在老家放置多年,被一只有文化的老鼠啃过。
清代孙洙在他编辑的《唐诗三百首》序言中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
我就想,我家那只有文化的老鼠,是否也秉持着“诗书传家”的良好风尚,一代一代地吟诗传诗呢?

▲被一只有文化的老鼠啃过的《唐诗三百首新编》
【关于作者】
千丘生,本名田宏辉(曾用名田红辉),湘西籍土家族。身耕都市,心念乡野,主营一个文化策划工作室和一颗真实写作的心。
越过山丘,看见千丘,看见您的关注、分享和赞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