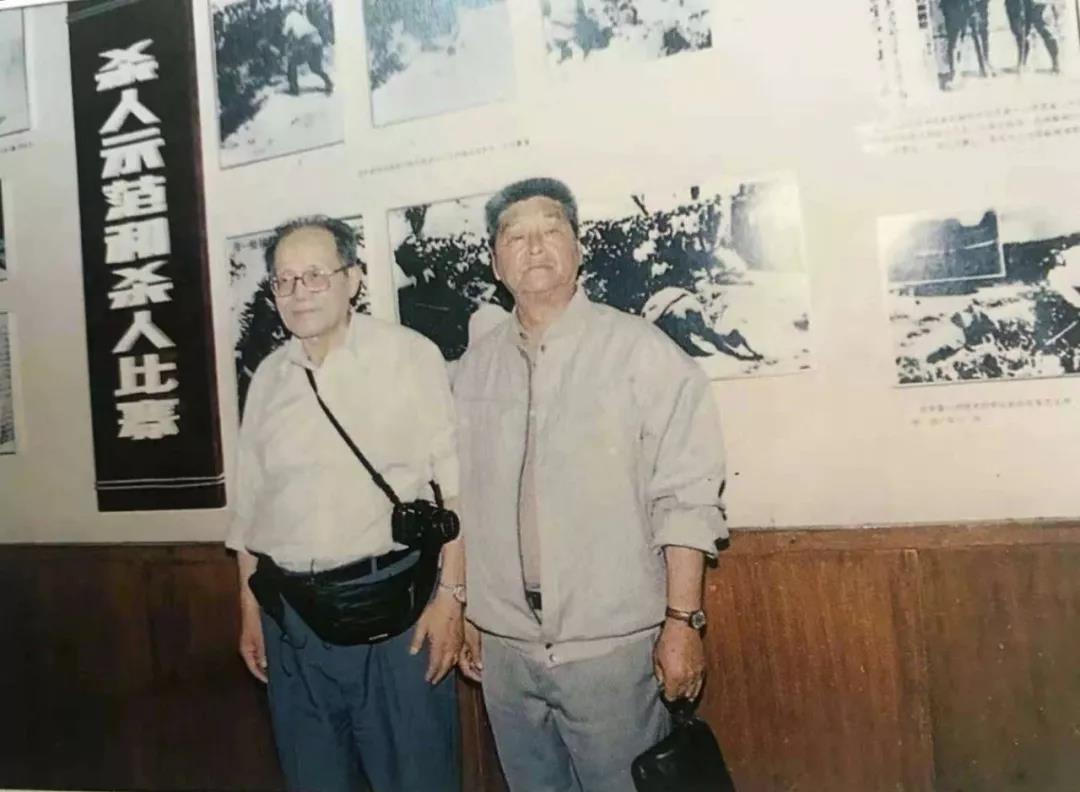[太阳]1941年,一名15岁的男孩在上厕所时,发现墙缝里似乎藏着什么东西,他用手把泥巴刮开,竟然发现了一个油布包,当他打开包裹时,里面的东西让他既害怕又愤怒。 (参考资料:2020-05-20 抗日战争纪念网——一本滴血的相册) 1947年的南京军事法庭上,气氛冰冷,前侵华日军第六师团师团长谷寿夫,正对南京大屠杀的指控百般抵赖,审判一度陷入僵局。 就在这时,一份被法庭标记为“京字第一号”的物证呈了上来,它不是枪炮,也不是文件,而是一本巴掌大的灰色相册。 当这本小册子被翻开,当那些照片映入谷寿夫眼帘时,他瞬间面如死灰,嚣张气焰荡然无存,惊慌得几乎站立不稳,究竟是怎样的照片,能让一个杀人如麻的战犯当庭崩溃? 故事要回到1938年初,日军屠城的腥风血雨尚未散尽,在南京国府路估衣廊10号的华东照相馆里,15岁的小学徒罗瑾,每天听着城中的哀嚎,看着日军的暴行,心里憋着一团火。 一天,一个日本少尉拿着两个胶卷来冲洗,罗瑾默默接下,当晚,他在暗房里冲洗胶卷,里面的内容让他浑身冰冷——全是日军屠杀同胞、奸污妇女的场景,每一张都触目惊心。 怒火压倒了恐惧,一个大胆的念头在他心中萌生,罗瑾冒着杀头的风险,偷偷多冲印了三十几张。 他仔细筛选,剔除了曝光差的,又忍痛拿掉了记录日军奸污妇女的照片——年少的他觉得,那是对中国妇女的巨大耻辱,多年后,他为此深感遗憾,最终,他留下了十六张最清晰的照片。 为了保存这些铁证,罗瑾找来灰色软卡纸,裁成小卡片,将照片一张张贴好,装订成册,更令人叫绝的是,他在封面上画了一幅画:左边一颗滴血的心脏,右下方一把带血的刺刀,刀尖下是一滩血泊。 而在右上角,他用美术字写下一个大大的“耻”字,下面再跟一个巨大的问号,这本承载着血泪的相册,就这样在一个无名少年手中诞生。 然而,在战乱中保存它,比制作它更难,1940年,罗瑾为求生计,考入汪伪政府的警卫旅通讯队,驻地在毗卢寺,他把相册偷偷带进军营,藏在床板下。 在这里,日伪教官们嘴上喊着“中日亲善”,背地里却常对学员拳打脚踢,谁知,1941年初,队里为迎接汪精卫视察,突然展开大清查,据说是因为发现了一颗来路不明的手榴弹。 情况紧急,罗瑾情急之下,将寺庙后院厕所的一块墙砖抠出,把相册塞进去,再用泥巴糊好,可几天后,当他想把相册取出时,却发现它竟然不翼而飞了! 罗瑾吓出一身冷汗,为免杀身之祸,他赶紧请了长假,匆匆逃离南京,后来举家迁往福建,这本相册的下落,也成了一个被他埋藏心底、渐渐淡忘的秘密。 罗瑾走了,可相册的故事没有结束,他逃离后不久,同在通讯队的吴连凯在清晨去后院厕所时,无意间发现墙角草丛里躺着一个灰色的东西,他捡起来一看,正是那本相册,封面上滴血的心脏和刺刀,在晨光下格外刺眼。 吴连凯翻开相册,那十六张日军暴行的照片让他心惊肉跳——他也曾亲历屠杀,那些场景刻骨铭心,他立刻意识到这本相册的分量,迅速将其揣入怀中。 当天,队长和政训员就召集全体队员训话,声色俱厉地警告队里有人私藏了相册,吴连凯的心猛地一沉,他明白了,这东西一定是被上一个发现者因为害怕而丢弃的。 现在,轮到他做选择了:是扔掉它保命,还是冒着掉脑袋的风险,为历史留下这份铁证? 夜里,吴连凯辗转反侧,思考着最安全的藏匿地点,他猛然想起,之前站岗时,曾发现万福楼大殿弥勒佛像的底座下有个洞,这不就是绝佳的藏身处吗? 后半夜,轮到他站岗,时机来了,吴连凯带上相册,蹑手蹑脚地绕到佛像背后,在黑暗中摸索到那个洞口,小心地将相册塞了进去。 也许是冥冥中的庇佑,相册在佛像底座安然度过了余下的战争岁月,吴连凯毕业时才将其取出,此后一直贴身珍藏。 时间一晃,抗战胜利了,当南京军事法庭发出公告,向市民征集日军罪证,准备审判谷寿夫时,已改名吴旋的吴连凯,毫不犹豫地将这本珍藏多年的相册上交给了南京市临时参议会。 1947年2月,这本相册作为“京字第一号”证据,在谷寿夫的公审法庭上被出示,据事后记载,谷寿夫见到照片后“神色突变,慌乱不能自持”,在如山铁证面前,一切狡辩都显得苍白无力。 就这样,两个再普通不过的中国青年,罗瑾与吴旋,在日伪高压统治的白色恐怖下,用勇气和智慧完成了一场关于历史真相的跨时空接力。 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守护的,不只是一本相册,更是民族的记忆与尊严,是对历史正义最执着的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