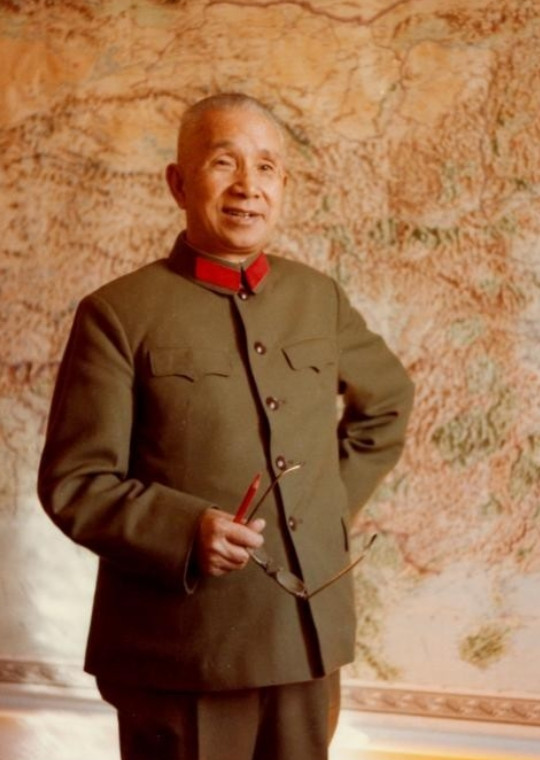1941年,黄克诚迎娶23岁的女学生唐棣华,结婚前,黄克诚对她说:“你不能因为男女平等就让我迁就你,我的岗位比你重要!” 1941年春,苏北阜宁,战火正紧,黄克诚作为新四军第三师师长,日夜奔波,统筹调度抗战事务,几乎没有喘息的时间,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他和一位山东籍的女大学生唐棣华结婚了,没有婚纱、没有亲友、没有任何仪式,只是在一间临时搭建的简陋屋子里,告诉几位战友:“我们结婚了,” 结婚这件事,在战时其实显得格外微小,更特别的是,这段婚姻从一开始就没有平常夫妻的甜蜜,他们之间立下了明确规矩:党和工作永远高于个人感情,家庭生活不能影响组织安排,不该问的事情绝不多问,对于唐棣华来说,这样的婚姻起点无疑是冷峻的,但她没有退缩,她清楚,自己嫁的不是一个普通人,而是一个把革命当成生命的人。 婚后没几天,唐棣华就被派去阜宁县参加修筑海堤的劳动,那是极为艰苦的工作,女人们和男人一样,挑土、搬石、打桩,衣服一干一湿,脚上磨出血泡,她没有借口,也没有抱怨,她是共产党员,她知道自己该怎么做。 战事紧张,黄克诚常年不在家,唐棣华独自承担起组织交给她的任务,同时还要照顾家庭,战争年代,她先后生下四个孩子,几乎每一次生产时,丈夫都在前线,孩子出生后,她一边做妇救会的工作,一边照顾婴儿,风里来,雨里去,没有人帮她看孩子,没有人替她做饭,她就把孩子背在身后,把文件揣在怀里,走村串户,组织妇女们缝军鞋、筹军粮。 她的丈夫黄克诚并不是一个温情脉脉的人,他对孩子们要求非常严厉,从来不许他们享受任何特殊待遇,孩子们上学必须走路,不能坐公车,哪怕是结婚,也不能讲排场,1980年,小儿子黄晴结婚,工作人员建议用单位的车去接新娘,他直接否了这个提议,孩子最后骑自行车把新娘接回家,婚礼也只是家里人简单吃了顿饭。 唐棣华的出身并不光鲜,她的父亲在旧社会曾经是汉口的鸦片商人,后来还做了汉奸,新中国成立后,她的父亲被判死刑,她没有去找丈夫求情,她明白,党的政策不能因为私人关系而改变,可黄克诚却主动找到负责此案的同志,请求允许唐棣华前往汉口与父亲见最后一面,他说,虽然他是汉奸,但毕竟是她的父亲,这个请求得到了批准,那次诀别虽然沉重,但唐棣华从未违背自己的立场。 新中国成立后,黄克诚任湖南省委书记,唐棣华也被调任工作,他们终于可以一家人团聚,那时,组织上为她分配了一套住房,她住了几十年,感情很深,但1979年,中央纪委出台规定,高级干部只能享受一套由国家提供的住房,黄克诚立即让她退掉那套房,她没有犹豫,立刻搬出,黄克诚对她说:“从严治党,要从我们家做起,” 在家中,他立了不少规矩,配车只能用于公务,家属不得乘坐,不准借单位名义谋私利,他说得严,做得更严,有一次,孙子黄健发烧了,下雪天起晚了,司机想开车送他去学校,黄克诚得知后立刻制止,他说,孩子不能从小依赖他人,更不能打破规矩,那天,小黄健在雪地里走了很远的路,病着身体坚持到了学校,这件事很快在机关传开,很多人深受触动。 黄克诚晚年身体越来越差,但他仍坚持工作,有一次,组织安排他南下休养,他拒绝了,他说,去了就得带人照顾,要花国家很多钱,还会给地方添麻烦,他最终被安排到北京玉泉山休养,但他提出条件:只带一个秘书,家属周日以外不得探视,生活费用全部自理,哪怕是住院期间,他也坚持不让国家花一分钱。 1986年,黄克诚病重,他知道自己时日无多,明确拒绝过度治疗,他说,自己已经不能为党工作,不希望再浪费国家的资源,他甚至举出马克思的女儿和女婿自愿结束生命的例子,希望医生尊重他的意愿,有时护士刚给他输液,他醒来就自己拔掉针头,唐棣华理解他的决定,劝医生随他的意思。 黄克诚去世那年,他84岁,唐棣华卧病在床,忍着悲痛为他写下一副挽联,她借这副联总结丈夫一生的不悔与担当,也倾诉了自己作为妻子、同志、战友的理解与支持。 整理遗物时,她在他的贴身口袋里发现一张已经发黄的纸,那是她1941年写的入党申请书,背面黄克诚用铅笔写道:“棣华的字比我工整,她的胆气比我更硬,”她的眼泪,一滴一滴落在那张纸上,把字迹晕开,也把他们共同走过的岁月照得更加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