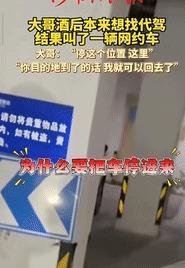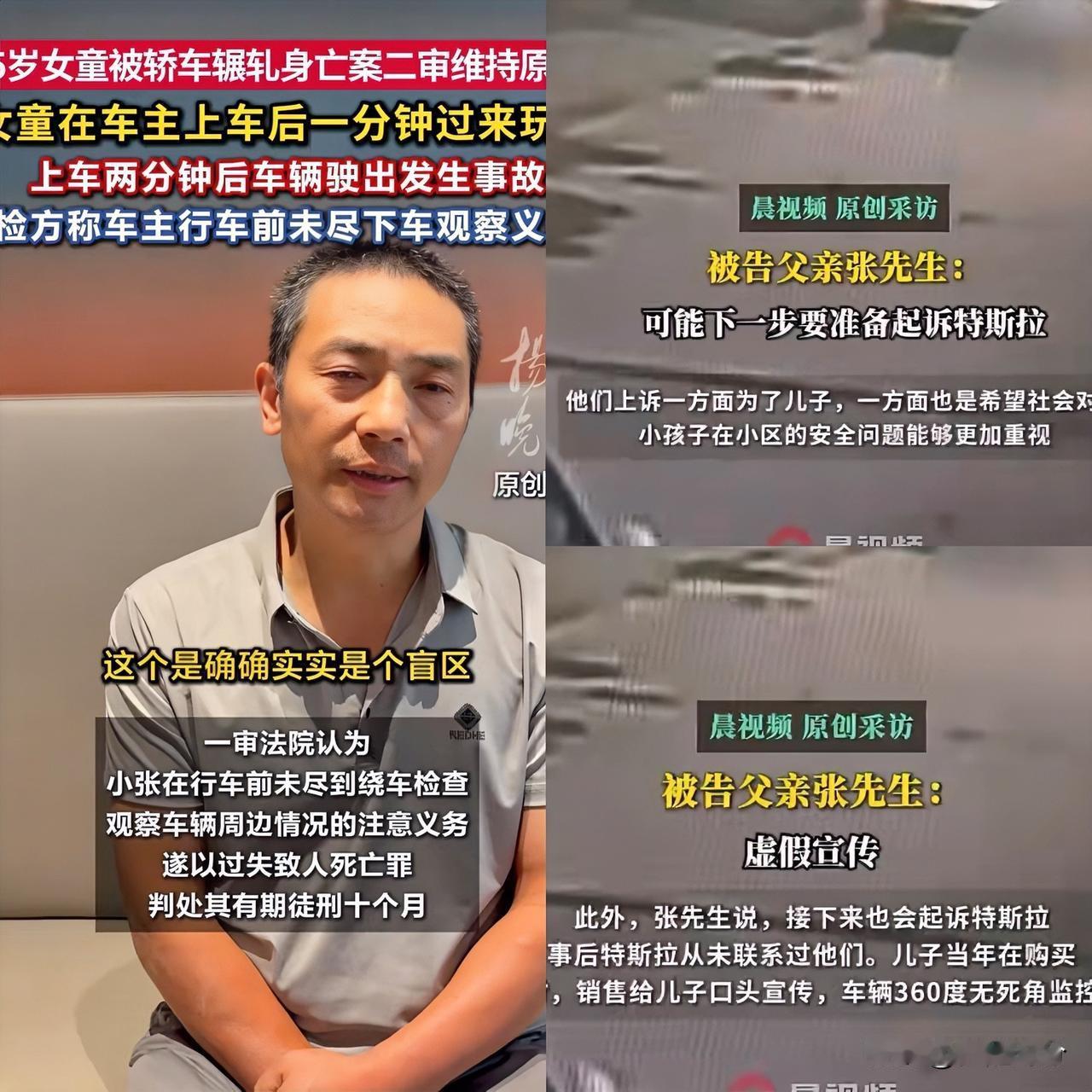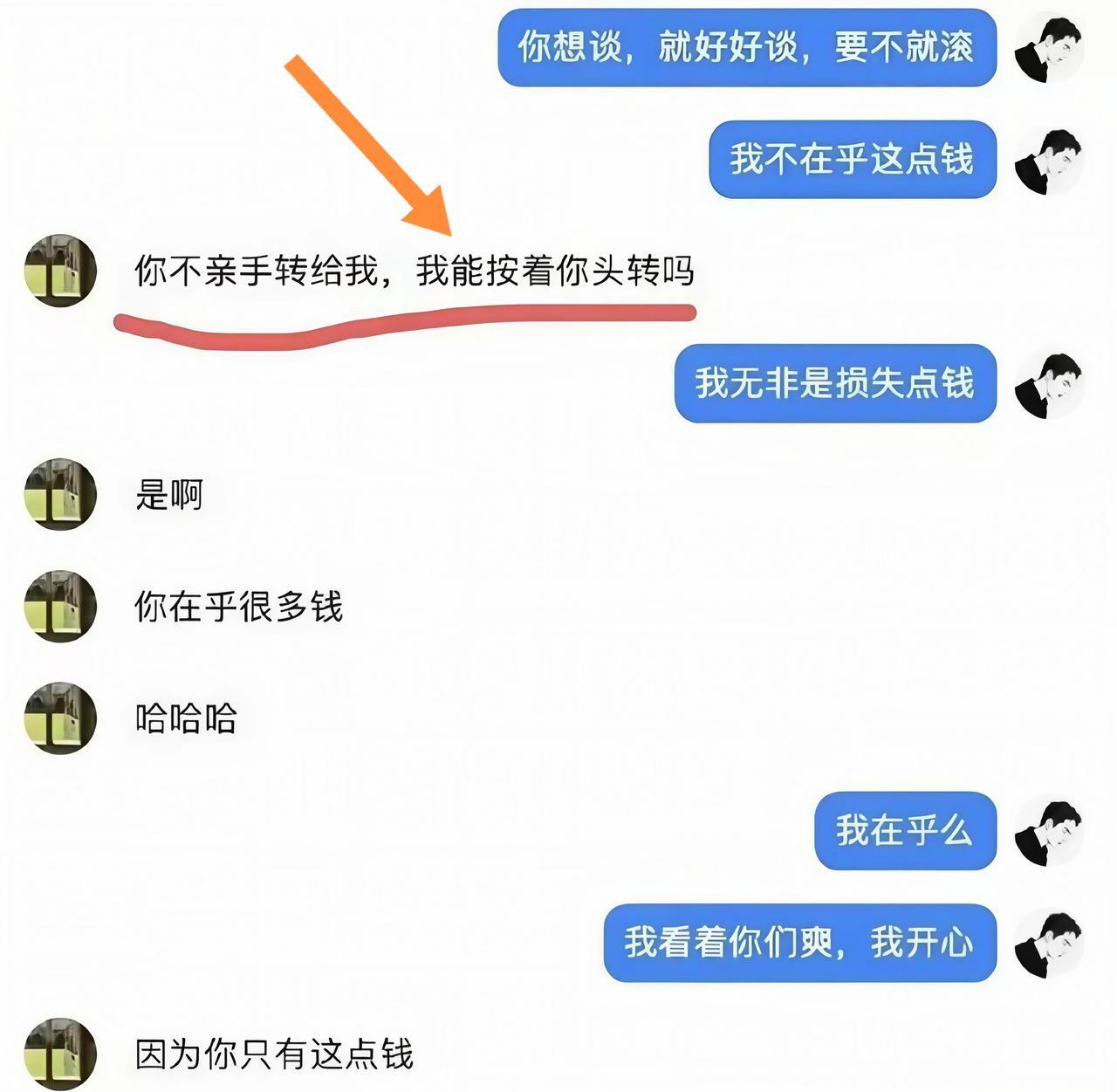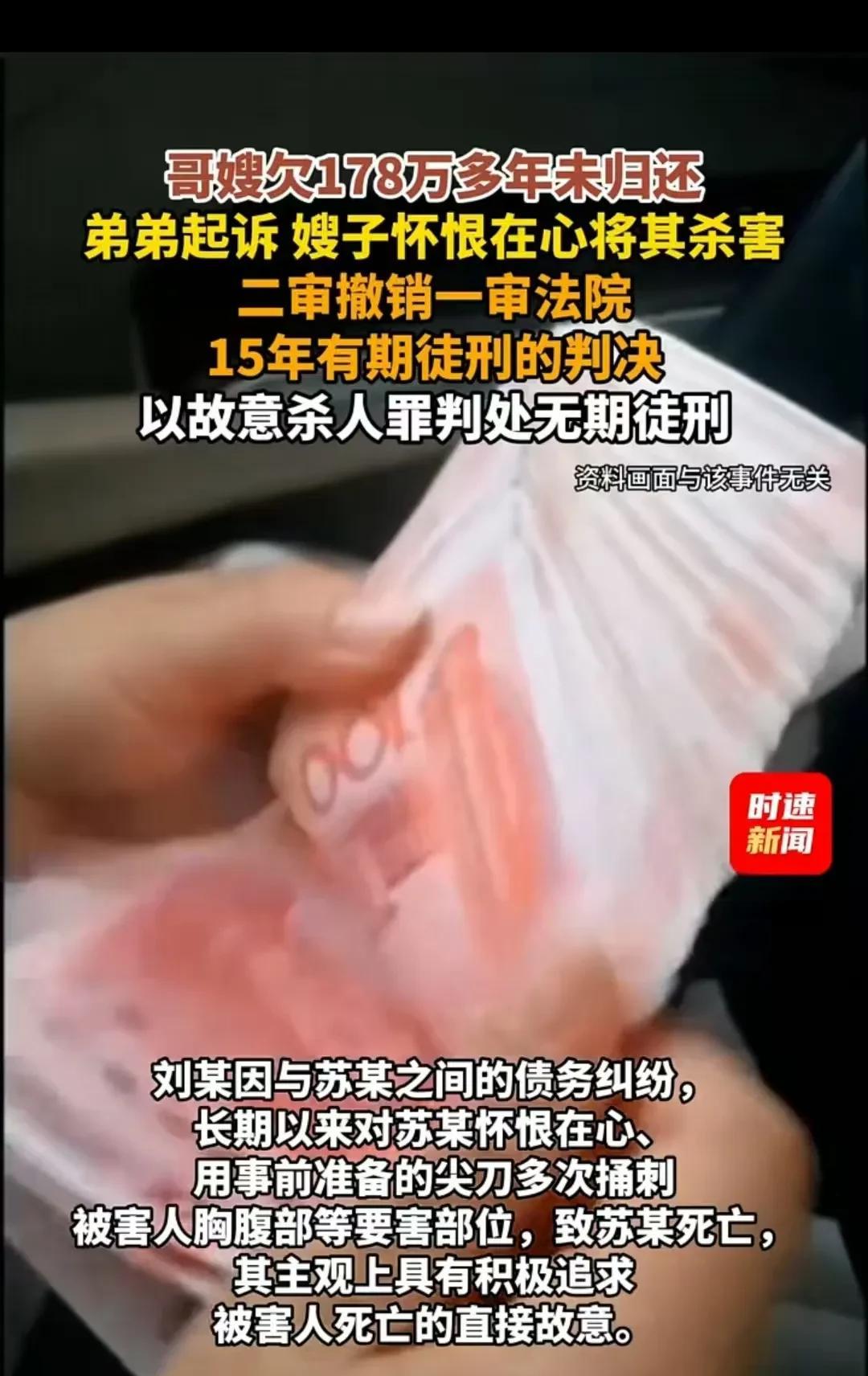“抓奸”变“坐牢”?四川西昌一桩家事,把六个人送上刑事审判席——女子发现丈夫出轨后,连夜“带人蹲守”、冲进出租屋殴打,还用鞋带反绑,将两人“押回婆家讨说法”长达“三小时”。结果丈夫头部挫伤、情人手臂骨折;可在公检法看来,这已越过法律底线:属于非法拘禁与故意伤害的交错,最终六人获刑(均适用缓刑)。 张女士起初是按下怒火的。2024年6月9日晚,她跟踪丈夫王某进入出租屋,门内传来男女窃语与笑声,她握紧手机却没破门而入。冷静没能持续太久,她拨通亲弟弟、堂弟等五人的电话,让人带上木棒、马鞭在门外守候。临近清晨6点,王某开门离开,众人一拥而上,棍影如雨;王某抱头倒地,毫无还手之力。很快,情人李某惊慌出门劝阻,也被殴打。其后,众人用鞋带将二人反绑,在街巷议论声中“押解”至王某父母家“要说法”。这段“捆绑殴打”与羞辱持续了“三小时”。 王某父母心疼儿子,更愤其失德。面对儿媳一行“押人示众”的尴尬与嘈杂,他们最终选择报警。警察赶到,解开鞋带带回调查。司法鉴定显示:二人全身多处皮下青紫、表皮脱落,李某手臂骨折。案件移送检方起诉前,张女士家属先行赔偿并达成谅解:王某家属出具谅解书,李某获赔8万元后也出具谅解书。 许多人第一反应是“活该”,可法律不会以愤怒为裁尺。人身自由是底线,限制人身自由、捆绑、押解,即使出于“教训”,也不能以私力救济替代公权力。何况还伴随群体殴打,造成骨折伤害。 把情绪交给法律,答案就清晰了。 首先,这并非“抓奸在床的正当防卫”。正当防卫须具有针对“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且防卫手段与强度应当必要、适度。婚内不忠系民事与伦理层面的严重过错,并非当场对人身、财产实施暴力的不法侵害。以棍棒群殴、反绑押人,既不具“制止急迫侵害”的前提,更明显超过必要限度。 其次,刑法规制明确。《刑法》第238条规定:非法拘禁他人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具有殴打、侮辱情节的,从重处罚。这里的非法拘禁既可表现为持续时间较长,也可表现为方法恶劣、后果严重。现实办案中,“24小时”只是对部分职务类情形的立案参照,而对普通主体,只要实施捆绑、看守、押解等明显剥夺自由的行为,并伴随殴打、侮辱,或造成轻伤以上后果,就可能入罪。 再次,故意伤害的边界也被触碰。殴打致李某骨折,已达到法律上“伤害后果”的入罪门槛(是否构成犯罪,取决于法医鉴定等级与证据链完整)。本案起诉与裁判以非法拘禁为主,但“殴打+骨折”这一事实,亦是法庭从重评价的重要依据。 有人会问:对方婚内出轨,难道没有法律责任?当然有。《民法典》第1091条明确了离婚过错损害赔偿制度:一方有与他人同居等严重过错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可请求赔偿。张女士若走司法途径——例如固定证据、提起离婚诉讼并主张精神损害赔偿与财产利益倾斜——法律会站在她一边。她真正需要做的是证据固定与策略诉讼,而不是把愤怒升级为违法的“押人示众”。“证据先行、法律后手”,才是正解。 法庭上,检辩双方围绕行为性质、手段与后果展开博弈。检方指控捆绑押解、时间持续、多人参与、伴随殴打侮辱;辩方强调婚内背德在先、情绪激愤、到案后悔罪、已赔偿且获谅解。 最终,法庭认可“以严重违法对抗民事过错”的性质,结合前述证据与伤情鉴定,依法作出有罪判决。考虑到张女士主动到案、如实供述、积极赔偿并取得谅解,适用认罪认罚并依法作出从宽处罚:张女士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6个月;其余5名亲属为帮助犯,各判有期徒刑10个月,缓刑1年2个月。 这并非“偏袒出轨者”,而是守住法治的最小公约数——任何人无权以殴打、羞辱、捆绑、押解等方式替法律“出手”。“以暴制暴”,会把弱者变成加害者、把正义变成风险。 此案给围观者一个提醒:别把法律当作“只惩坏人”的单行道。法庭上衡量的是行为与后果,不以出轨与否为转移。把“公序良俗”的愤怒转化为“法律秩序”的程序,才是理性与有效。 王某的不忠让妻子彻底失望,但张女士选择的维权方式,却让自己从“受害者”变成了“被告人”。这是一次典型的“以违法对抗违法”,最终所有人都付出了代价:婚姻破裂、名誉受损、自由受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