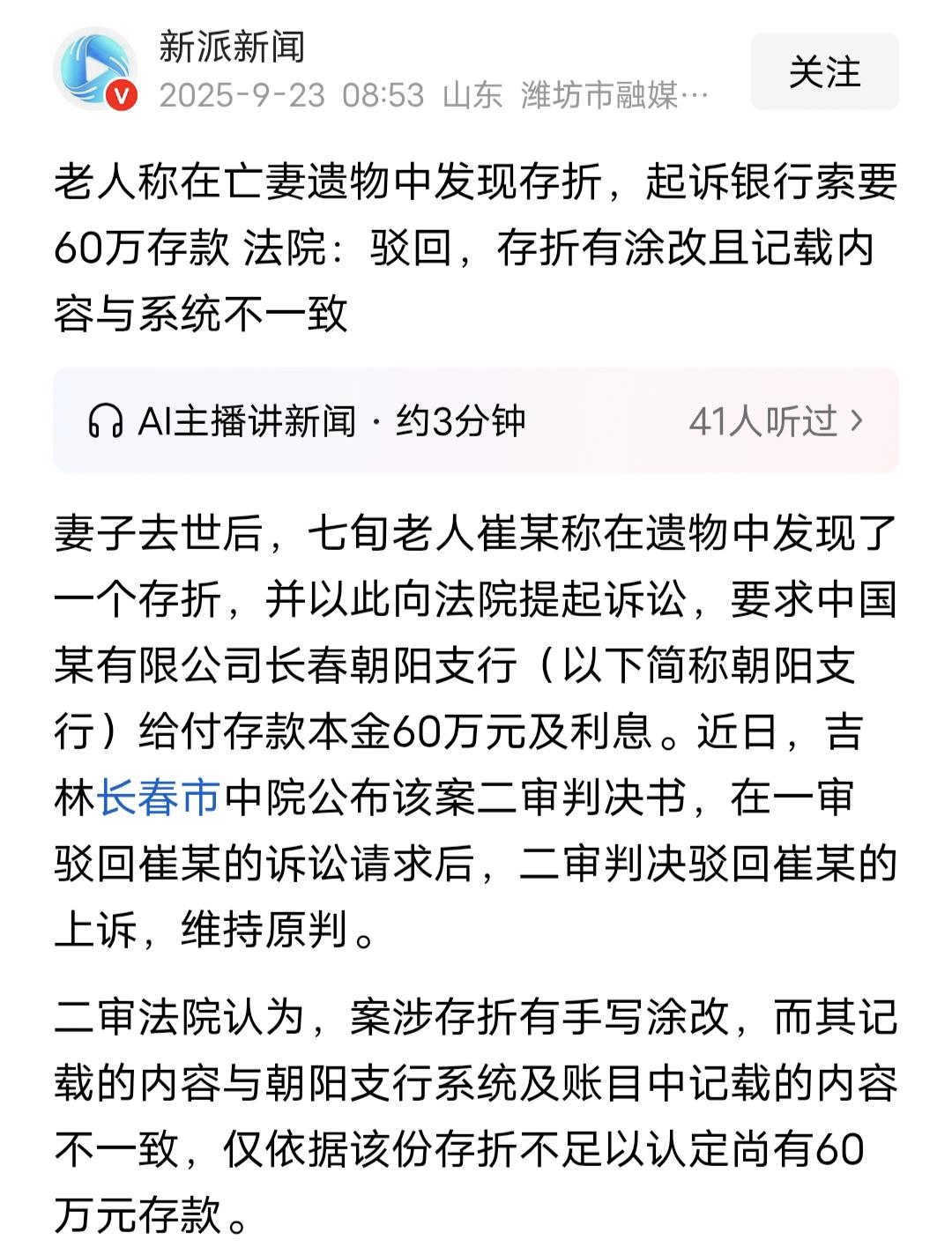吉林长春,一位七旬老人收拾亡妻遗物时,意外翻出一本写着“余额60万”的存折,本以为是老伴留给他的“养老钱”,却在银行取款时被告知账户记录与系统不符。老人气愤之下起诉银行,一审败诉,二审结果却让他意想不到。 2022年3月8日,崔大爷的老伴去世。直到半年后,他才鼓起勇气整理遗物。在一堆旧衣物和账本中,他发现了一本存折,上面清晰写着:2000年6月6日存入100万元,随后取出40万元,余额为60万元。 看到这行数字,老人眼眶湿润,他以为老伴悄悄为自己留了一笔“后路钱”。怀着激动的心情,他赶紧拿着存折来到某银行支行,提出要把60万本金和利息一并取出。 然而,银行工作人员翻看存折后,表示部分信息模糊,日期还存在手写涂改痕迹,需要进一步核实。双方争执不下,最终老人一怒之下将银行告上法庭。 一审法院经过调查后查明:第一,该存折账户实际是在2000年6月7日开立,开户金额仅为1元。第二,存折中所谓“2000年6月6日存入100万”的记录,是手写修改的,系统流水与原始凭证中都未出现这笔资金,也不存在之后取款40万的痕迹。第三,从开户至今20多年,该账户并无大额资金流入或流出,仅维持少量操作。 崔大爷在庭审中坚持称,存折是老伴用自己的身份证开户并一直保管,他并不知情,如今既然余额写着60万,就应当取出。但法院指出,《民事诉讼法》第64条明确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老人仅凭一本有问题的存折,而无资金来源证明、转账凭证或相关证人证言,不足以证明其存入过100万元。最终,一审法院以“举证不能”为由,驳回了崔大爷的全部诉求。 崔大爷不服,提起上诉。在二审中,银行方面再次强调:按照“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崔大爷必须证明存折记录的真实性;存折上的余额显示不能单独作为认定依据,必须与系统流水相互印证;一审已查明该账户开户金额仅1元,此后无百万元资金流入,所谓60万元余额显然不成立。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75条:“人民法院对当事人的陈述,应当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审查确定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 二审法院认为,崔大爷提交的存折存在明显涂改,与银行系统记载完全不符。老人既无法解释涂改缘由,也无法提供其他证据佐证“曾存100万并取出40万”的事实。 因此,二审判决认定:崔大爷的上诉理由不足,维持原判。2025年8月28日,法院正式判决——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这起案件,看似只是一起取款纠纷,实则包含多个法律要点: 关于举证责任。在民事诉讼中,谁主张,谁举证。老人要证明账户内确有60万元存款,就必须拿出与银行记录相匹配的证据。仅凭一本存在瑕疵的存折,无法形成完整证据链,自然要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关于存折的证明效力。在过去,存折是银行与客户之间确认存款的重要凭证。但在电子化背景下,存折上的记载须以银行系统记载为准。如果出现矛盾,需要结合流水、原始凭证综合判断。若存折存在手写涂改,更应要求出具合理解释,否则其证明力大打折扣。 关于长期未行使权利的合理性。崔大爷声称存折自2000年起便由老伴保管,从未查询余额。法院指出,超过20年未曾核对账户存款余额,本身不符合常理。若真存有巨额资金,作为家庭财产,不可能20余年间无任何使用或查验。 关于银行的举证义务。银行方面已提供了系统流水、开户凭证,能够证明未发生大额资金存入或取出行为。这些材料经法院审查,具备较高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因此足以反驳老人的主张。 案件的社会警示意义更为深远。 其一,对老人群体来说,妥善保管财产凭证尤为关键。存折、银行卡、密码等都需定期核对,以免因时间过长、凭证损毁而陷入不利境地。崔大爷20多年未曾查询存折,导致一旦出现问题,缺乏补强证据,最终败诉。 其二,对家庭而言,财产应当透明化、规范化管理。夫妻之间、子女之间不应完全依赖口头约定,应形成明确的书面记录或法律文件。这样既能避免纠纷,也能在意外发生后减少误会。 其三,对公众来说,这起案件再次提醒:“钱要落到实处,证据要留到手里。” 不论是大额存款还是财产转移,凭口说、凭记忆都不可靠,必须保留书面凭证、流水、合同。 其四,从法律角度看,法院在此案中的判决凸显了一个核心理念——程序公正与证据为王。即便老人身份特殊、境遇令人同情,但若无法提供合法有效证据,法院也不会轻易突破法律规则。 崔大爷翻出的那本存折,原本寄托着他对亡妻的思念与生活的希望。然而,数字上的“60万”最终沦为一场空欢喜。 案件的背后,不仅是法律对证据的严格要求,更是一次对人生教训的提醒:亲情可以寄托,但财产必须有凭有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