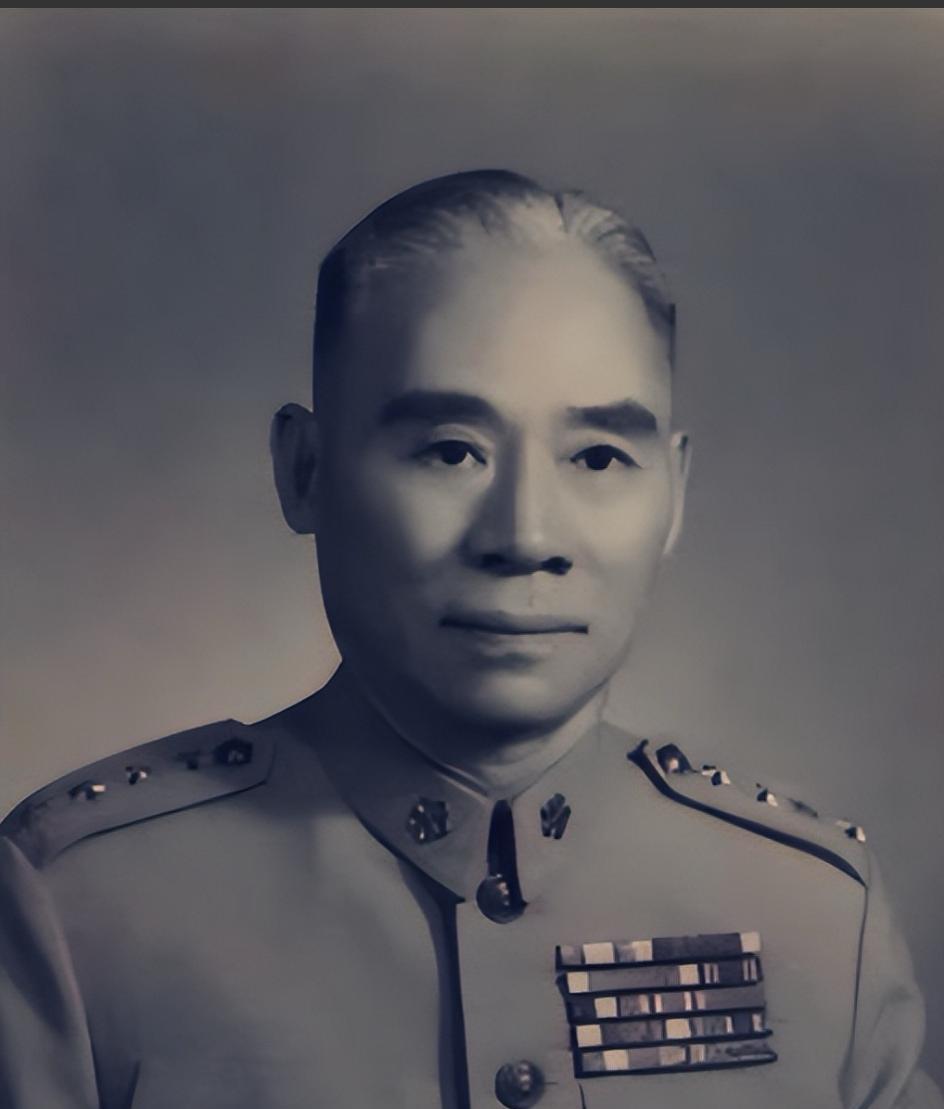1988年,在台湾42年的我党地下工作者,伪装身份回到大陆,没想到到家后,却看到一屋子的孩子,他疑惑地问道:“我42年没回来了,这些孩子是谁的?” 他站在门口的那一刻,真没想到,家里会有这么多孩子,他仔细数了数,至少四五个小家伙在院子里跑来跑去,个个叽叽喳喳,活蹦乱跳。 他的手紧紧抓着门框,眼神里全是困惑和不安,四十二年没回来,这个院子还是那个老院子,可屋里的人,怎么都变了模样? 正想着,门口出来一个驼着背的老太太,手里还牵着个小男孩,两人对视了几秒,老太太簸箕“咣当”掉在地上,嘴里发出低低的一声,“汉光?” 那孩子抬头望着他,圆圆的眼睛里全是新奇,他还是忍不住问了一句,这些孩子是谁的?老太太红了眼眶:是咱们的孙子孙女啊! 这时,一个年轻男人从屋后出来,脸有些熟,又有些陌生,那人开口,我叫建国,是你的儿子,他整个人几乎站不稳了。 这个男人,在他离家那年,还只是个刚出生的婴儿,这场团聚来得太迟,但也幸好,还赶上了。 谢汉光回到家不久,问题就来了,他说自己是地下党员,可地方上没人认识他,也查不到档案。 他拿出那个藏了几十年的老党员证,边角都磨得发卷,可依旧没人敢贸然确认,他住在老屋的一角,每月只领到一点“台胞困难补助”,他知道,真正的“身份”,还要等组织认定。 他没放弃,开始写信,四处打听老战友的下落,他找到了陈仲豪,当年一起在台湾工作的人,如今在汕头大学当图书馆馆长。 很快,中组部接到了材料,还有几封来自台湾老同志的证明信,他们很慎重,派了调查组到丰顺来实地了解,还翻查当年在台地下组织的记录。 过了半年多,县里来通知,说他1947年参加革命,属于老干部,离休待遇按科员级别发放,那一刻,他坐在炕上,手抖着打开那份文件,老泪纵横。 他不是为了待遇才回来,他回来,是想再确认一次,自己这些年的牺牲没有白费。 哪怕晚一点,也想让那个一直放在枕头底下的党员证,再次被认出来,不是为了荣耀,而是为了那句他年轻时听过无数遍的话:“共产党员,不能忘了初心。” 1950年冬天,他在报纸上看到了那个熟悉的名字,蔡孝乾,昔日的上级,成了叛徒,一口气供出了整个组织,他瞬间明白,留在台北等于自投罗网。 当天夜里,他带着仅有的干粮和一点现钱,坐上去往苗栗山区的车,头也没回。 之后几个月,他过得像野人一样,从苗栗转到台中,又从台中逃往嘉义,最后一路翻山越岭到了台东林场,山里一个老村长收留了他,帮他顶替一位失踪的高山族农民“叶依奎”的身份。 他交出两个金戒指,换来一张新的身份证,还有在林场做苦工的机会,从那一刻起,谢汉光这个人,彻底在台湾消失了。 在台东,他成了种树的“叶依奎”,白天上山锄草种树,晚上躲在阁楼里看老掉牙的《农作物分类手册》。 他从不和人深聊,也从不在村口闲站,他的腔调越来越像本地人,甚至闽南话说得比粤语还溜,但有一样东西,他从没丢,那本压在床底的党员证,还有对远方妻儿的思念。 村民们见他老实能干,经常给他介绍对象,他总笑着推说自己有病,怕耽误人家,只有他自己知道,那份“病”是心病,是他不能娶别人,更不能忘记自己来时的使命,他不是来避世的,他是来潜伏的。 时间一晃就是四十多年,那些年,他看着山里建了电站、修了公路,台湾的面貌越来越现代,但他始终没换过那身粗布衣。 有人劝他可以下山去台北“重新做人”,他笑笑没答,只有他知道,自己早就做好了等的准备,哪怕这一等就是一辈子。 1917年,他出生在广东丰顺县的一个贫寒农家,兄弟姐妹一共十一人,他排行靠前,从小就是家里第一个背上书包的孩子。 那时家境艰难,土屋漏雨,吃的是红薯叶,可父母始终咬着牙把孩子往学堂送,他小时候就说:“咱不能一辈子种地,得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他真的出去了,十九岁,他考进了广西大学农学院,专业是森林系。 那几年,学校里卧虎藏龙,李四光、竺可桢都来授课,他从这些老师那里,第一次听说“改造国家”的理念,也是那时候,他结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经常在夜里讨论抗日、革命、民族命运。 他逐渐被吸引,开始帮忙印传单、转情报,甚至亲眼见过日机炸掉村庄的惨烈场景,从那以后,他认定,这一生要跟着共产党干到底。 1942年毕业后,他被分配到黔桂铁路柳州农场任技术员,不久升任主任。表面上是研究植物,暗地里却成了地下联络点,他用自己掌握的专业知识掩护进出同志,还伪造过通行证。 抗战胜利那年,他终于如愿入党,不久后,组织派他去台湾,他没犹豫,拎着小包登上去基隆的轮船,他知道那不是旅游,也不是调职,而是从此藏身异乡。 可他万万没想到,秀萍真的等了整整四十二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