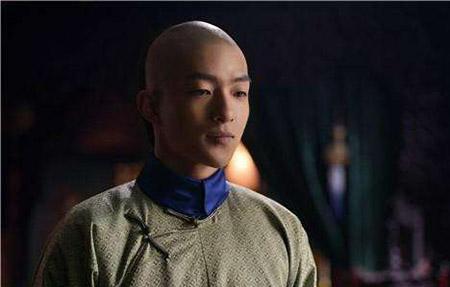1875年,皇后阿鲁特氏被慈软禁,四天内没有吃水米,快要死的时候,她收到了父亲崇琦偷偷送来的一个食盒,结果食盒里竟然一点东西都没有,阿鲁特氏苦笑着,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 阿鲁特氏人生最后一次求助,是写给她父亲的,纸条上不过寥寥几句,都是她对命运的挣扎。 父亲崇绮没有回长信,只写了一个字:“死”,这个字送进储秀宫,像最后一击,把她的念想彻底击碎,外人总觉得这是不近人情,可在当时的朝堂上,这其实是种“聪明人”的做法,一刀切断感情,避免全家覆灭。 后来她自杀身亡,宫人收拾她的遗物时,找到了那只空空的食盒,木盒底部,有两个小字——“女儿”,也许父亲是有苦衷的,也许他真不知道还能怎样帮她,不敢放吃的、不敢写信、不敢托人,他能做的,就只是这份沉默。 崇绮不是贪生怕死之徒,也不是彻底的冷血,他的仕途因为父亲赛尚阿早年得罪咸丰帝而屡屡中断,直到中了状元才算翻了身。 他知道朝廷权谋是怎么运转的,也知道自己一个汉林出身的状元,在慈禧面前没有分量,他明白得太清楚了,所以才会选择不救,不是不想救,而是不能救。 阿鲁特氏能成为皇后,表面看是同治帝的选择,其实背后藏着一场两宫太后之间的明争暗斗。 那年选秀,两位太后各推一人,慈安看中的是她的表外甥女阿鲁特氏,而慈禧属意的则是侍郎凤秀家的富察氏,两人背后牵着的是家族、朝局、旧怨和对皇权的控制欲。 慈禧对阿鲁特氏从来没什么好感,这不仅和性格有关,还跟郑亲王端华有直接关系,这个端华是慈禧政变路上的障碍,偏偏又是阿鲁特氏的外祖父,过去的仇怨全被她一人承担。 更要命的是,阿鲁特氏一向性子倔,有次当面说“我是从大清门抬进来的”,这句话狠狠戳中了慈禧的心口。 谁都知道,慈禧当年是以贵人身份入宫,根本没有资格走大清门,这事她一直记着,一直介意。 而阿鲁特氏的这句无心之言,无异于一记耳光,就算她是皇帝的正妻,慈禧也绝不会让她好过。 尽管如此,慈安还是坚持推她上位,这背后有亲情成分,也有制衡慈禧的政治意图,而同治帝本身就对她心生好感,两人性格互补,一个孤僻沉默,一个端庄温和,婚后感情越来越好,这更让慈禧看不惯。 她本想让慧妃慢慢取代皇后的位置,却没想到两人越走越近,把自己排除在外。 这场对峙,从阿鲁特氏成为皇后的那天起就注定不会有好结局,表面是皇室选妻,背后却是清宫争权的大戏,阿鲁特氏不过是台上最显眼、但最无力反抗的那个棋子。 阿鲁特氏的死不是突然的,而是慢慢地被逼到一条不归路,她被送进储秀宫的那一刻起,命运就已经悄悄定下了基调。 这座冷宫并不是普通的住处,阴暗潮湿、人迹罕至,是清宫里专门“消失”人的地方,宫人们明白分寸,送饭送水突然停了,也没人敢问一句。 她试图抗争,头磕得血流满面,还是没人理会,她刻字在墙上,“天可怜我”四个字刚写完,就听到门口响动,送来了那个空食盒。 那一刻,她明白了,这不是宫里的疏忽,而是上面下的命令,哪怕她再端庄贤淑,也不过是慈禧眼中的一根刺。 身边没了同治帝,宫中所有的规则都开始改变,她原本可以守灵,但被强行隔离,按理说该受朝廷祭拜,却连身份都被贬回“皇贵妃”,她从天子的正妻,变成孤魂野鬼般被困在那一座阴暗宫殿中。 但她没有崩溃,也没有大喊大叫,那天深夜,北京的风吹进窗缝,她披上所有衣物,烧水、煮药,坐在灯下整了整衣襟。 她不是在等人来救她,而是在准备体面地告别,第二天,宫人推门看见她靠在墙角,唇边还有血,但妆容没有花,发丝没乱,她选择了安静地死去,就像当年她安静地入宫一样。 慈禧听说她死了,语气平静地说了一句:“她聪明”这个评价让人不寒而栗,聪明的,在清宫不会留下来,活下来的,要么会装傻,要么早已学会低头,她没学会,所以她走了。 她死了,但历史没打算记住她,那份讣告上只写了“皇贵妃薨”,没有“皇后”二字,她的谥号被赋予得体面——孝哲嘉顺淑慎贤明宪天彰圣毅皇后,但讣告与谥号之间,有太多的沉默地带。 她曾是中宫之主,却没能入祖庙,没立墓碑,甚至在《清史稿》里只落了六个字:“悲伤致疾而薨”。 当时有御史上书,请求为她加谥节烈,以表彰她殉夫之举,慈禧看完之后大发雷霆,不仅否了奏折,还罢了御史的官,说他“信谣传妄”。 她不想让这个名字再出现,不想这桩死事再在朝野引发议论,越是压制,就越说明这事刺痛了她。 死后的她,被安葬在惠陵,躺在同治帝的左侧,但陵墓里也发生过盗掘,墓被打开后,陪葬品被洗劫一空,连尸体也不完整。 有说她的肚子被剖开取金,有说头骨被敲碎取珠,昔日皇后的尊严,最终也没能逃过尘埃与暴力。 清宫擅长选择性记忆,慈禧不希望她被记住,于是她真的就被人遗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