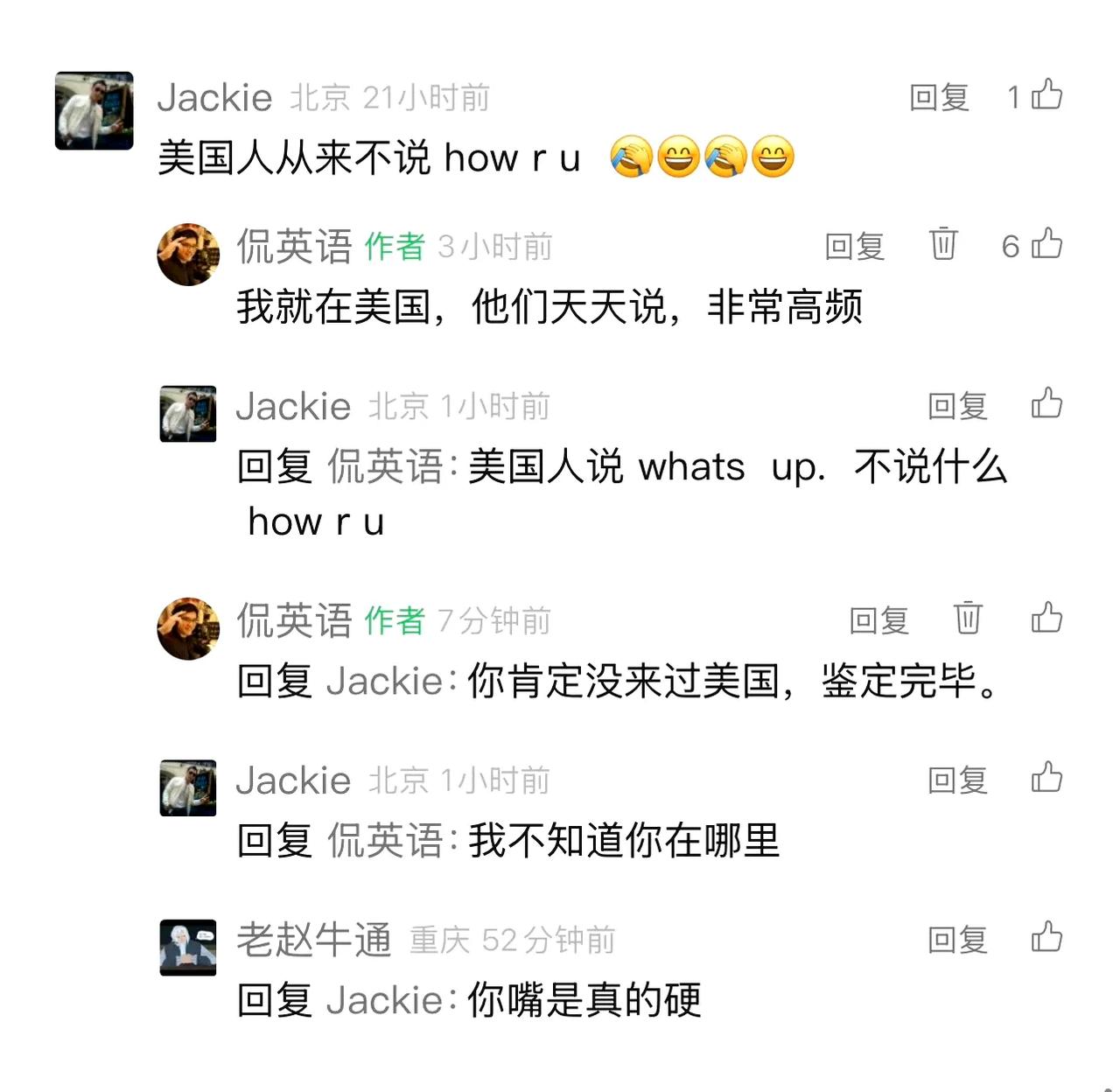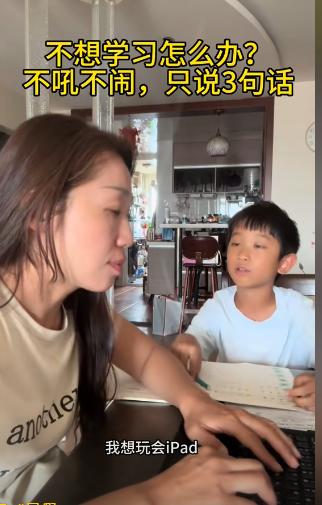1952年冬天,北京海关收到个神秘包裹,里面装着20克苏联送来的“一号除虫菊”种子,这半两不到的种子被分成四份,由警察叔叔护送,分别送到呼和浩特、大同、西安、潍坊四个农场,这可不是普通的种子,而是能救全国孩子命的“宝贝疙瘩”。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孩子最怕的不是作业,而是肚子里的蛔虫,农村孩子喝生水、光脚跑,十个有九个肚子里有虫,这些白花花的虫子能长到二十多厘米,抢营养不说,还让人肚子疼得直打滚。 有老人回忆“那时候孩子瘦得跟竹竿似的,拉出来的蛔虫能绕毛笔杆好几圈。” 当时唯一能治蛔虫的药叫“山道年”,全靠进口,价格贵得离谱,普通家庭根本买不起,很多孩子只能硬扛,苏联这时候送来的蛔蒿种子,简直就是“救命稻草”。 潍坊农场的工人像伺候祖宗似的照顾这些种子:土壤酸碱度调了又调,浇水时间算得比闹钟还准,连防虫网都织了三层,1954年秋天,当金黄色的蛔蒿花在潍坊农场绽放时,整个中国都松了口气——咱们终于能自己种驱虫药了! 科研人员发现,直接吃蛔蒿提取物苦得能让人怀疑人生,1954年,淄博制药厂的师傅们想出个绝招:把药做成宝塔形状,裹上糖衣,这糖不光造型可爱,味道还甜丝丝的,孩子们抢着吃。 到1958年,潍坊农场种了8640亩蛔蒿,一年能产150吨花叶、3吨种子,不光够全国用,还能出口赚钱,制药厂专门建了40间烤房烘干蛔蒿,公安局派人在田边24小时站岗,这待遇比种人参还金贵。 1960年闹自然灾害,粮食都不够吃,蛔蒿田被改成麦田,1964年潍坊连下40天雨,蛔蒿全被泡烂,更惨的是1965年中苏翻脸,苏联专家带着设备拍拍屁股走了,中国制药厂瞬间瘫痪。 改革开放后,卫生条件好了,蛔虫病越来越少,1982年,更高效的驱虫药出现,卫生部宣布淘汰宝塔糖。 尽管有人偷偷把种子藏在井里,但最终还是没能保住这株植物,1985年,当国外药企高价求购蛔蒿种子时,中国已经连一株活的蛔蒿都找不到了。 20克种子背后,是新中国刚成立时“把卫生工作搞上去”的死磕劲头:四个农场同时试种,是科学家的严谨,把药做成糖果,是医生的智慧,农民宁可少种粮食也要种蛔蒿,是普通人的奉献。 宝塔糖的消失看着可惜,但其实是国家进步的证明,现在孩子打虫药是草莓味的,再也不用担心肚子里爬出虫子,这不就是当年那些科学家、农民、工人用汗水换来的幸福吗? 不过这段历史也给我们提了个醒:当年因为信息不通、规划不足,导致蛔蒿绝种,这样的教训不能忘,现在潍坊的农田里再也找不到蛔蒿,但那些深埋地下的种子,永远记得那个年代中国人为了健康有多拼。 从20克种子到全民健康,从宝塔糖到现代医药,这场持续半个世纪的“驱虫大战”,最终写就的不只是医药史,更是一个民族从穷到富、从弱到强的奋斗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