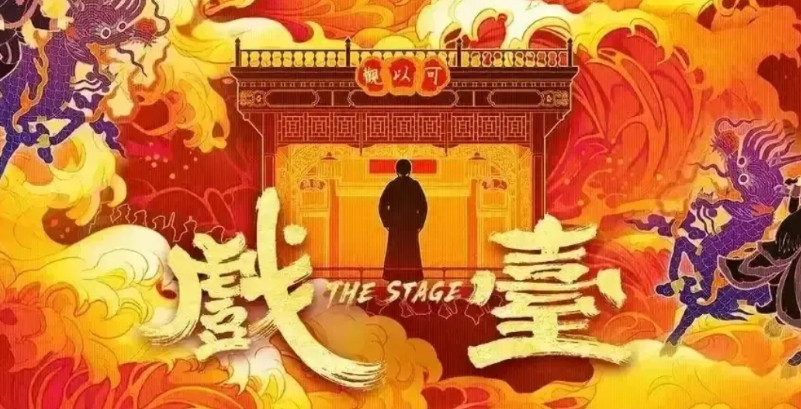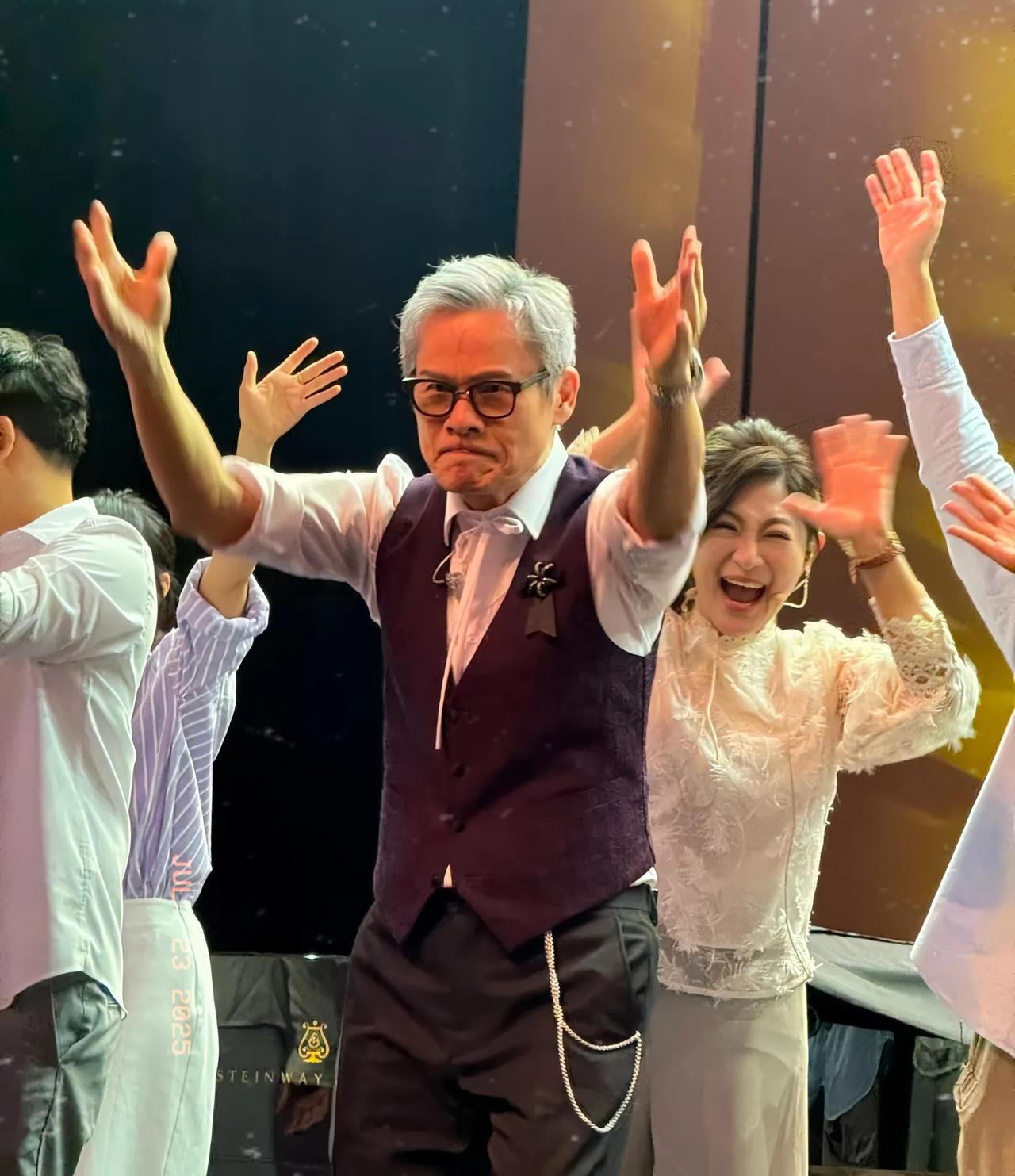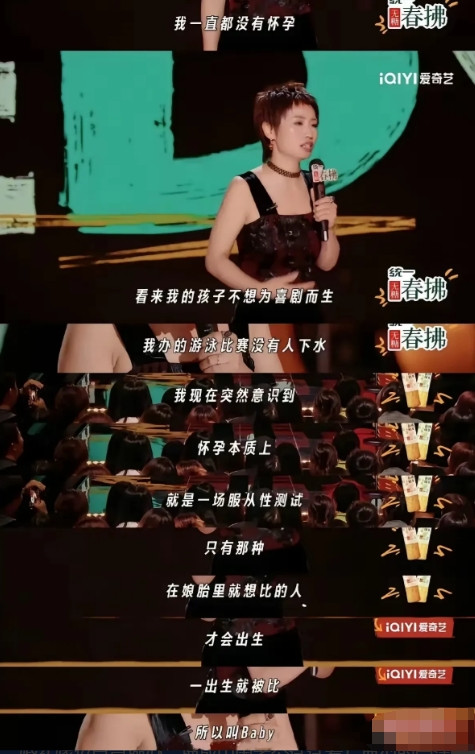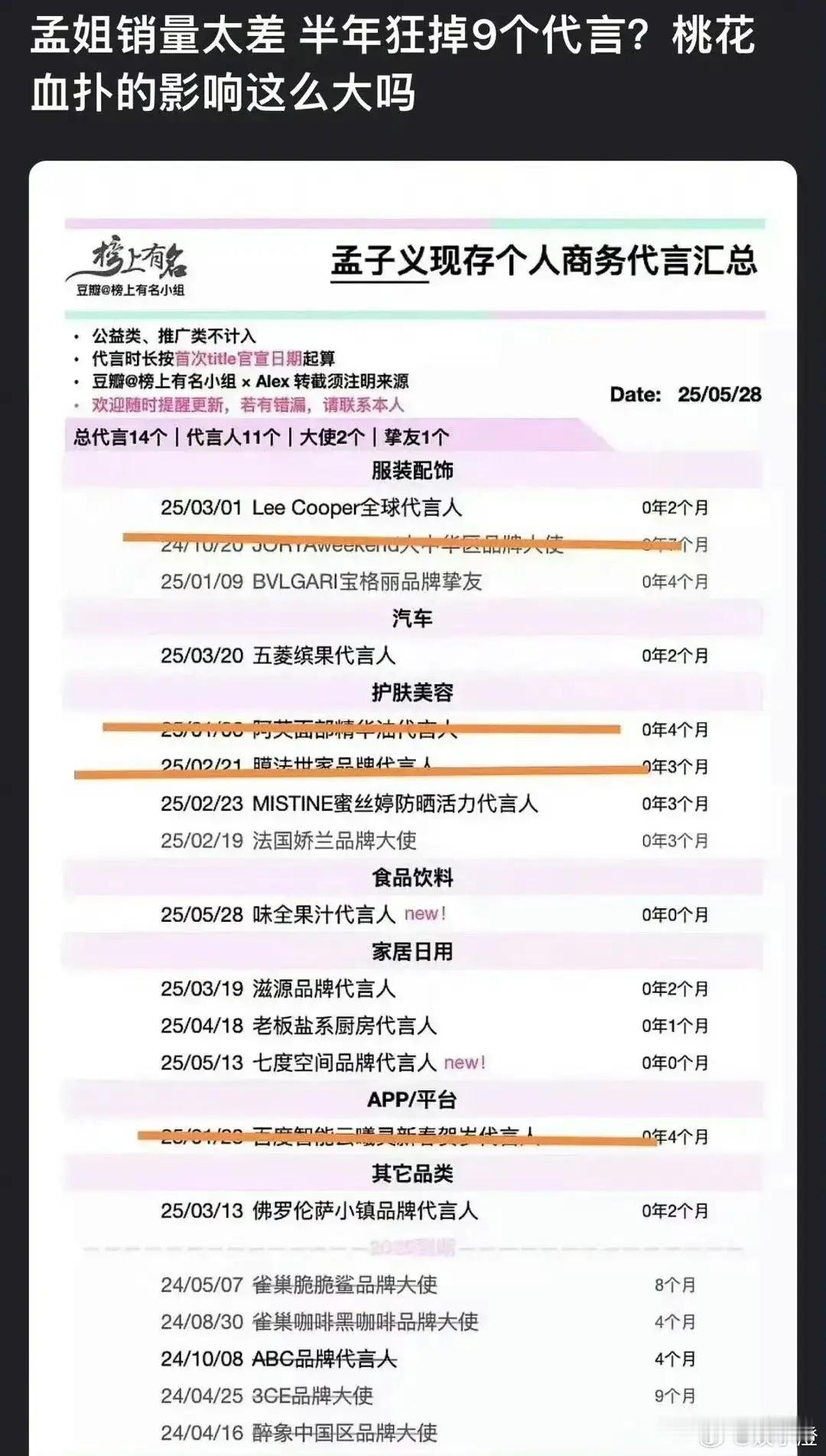巴金直言:样板戏从本质上说就是一批宣传片,完全忽略了艺术性!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也提到,“样板戏”已经成为其所在时代精神生活的象征。当一个时代的精神生活仅被一门艺术所涵盖时,该艺术无疑是阻滞文艺发展的,其具有典型的“工具化”特点。在当时,样板戏绝不仅仅具有艺术的作用,更是宣传主流意识形态的工具,包含阶级斗争、对革命英雄的歌颂、反封建反帝国主义、对领袖的歌颂等主流意识形态的内容。 其中有阶级斗争,如《白毛女》中杨喜儿代表的农民阶级和黄世仁象征的地主阶级之间的斗争;也有对革命英雄的歌颂,如《红灯记》中赞扬了为了给共产党游击队传递情报而英勇牺牲的李玉和、李奶奶。其中有反封建和反帝国主义的政治成分,如《红色娘子军》中对女性做出的历史性贡献的宣扬、《沙家浜》中革命英雄与“日寇”的斗智斗勇;也有对领袖毛主席的歌颂,如样板戏中多次出现的高呼“万岁”的场面,感染力极强,常常能带动台下的观众们。 样板戏是被政治“借用”的艺术,主流意识形态对其进行了全方位的雕琢和构造,虽然也产生了许多不朽的艺术成就,但由于其不可避免地和主流意识形态挂钩,无疑对当时的文艺发展留下了障碍。样板戏作为工具,发挥了极大的宣传作用。但与此同时,它的政治色彩也盖过了艺术色彩,为我国文艺的多方位发展带来了一定的阻滞。 在戏曲艺术的漫长发展历程中,不同时代的作品宛如一面面镜子,映照出当时社会的风貌与价值取向。传统戏曲长期以来热衷于塑造“帝王将相”与“才子佳人”,这些形象承载着特定的历史文化内涵,在大众文化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然而,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到了特定的历史时期,戏曲舞台上的形象塑造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回顾历史,自五四以来,文艺作品在典型人物塑造方面有着自己独特的发展脉络。那时,典型人物的塑造模式多关注小人物的命运,文艺创作者们热衷于聚焦普通劳动者的生活状态。他们通过细腻的笔触,描绘小人物在社会变迁中的挣扎、奋斗与无奈,展现出社会底层人民的真实生活画面,从而引发大众对社会现实的思考。例如鲁迅笔下的闰土、阿Q等人物形象,生动地展现了当时底层人民的精神状态与悲惨命运。 然而,到了后来,革命样板戏所塑造的工农兵英雄人物形象,以一种截然不同的姿态登上文艺舞台。这些英雄人物奋勇当先、挺身而出、战无不胜,他们的出现迅速且彻底地改变了文艺舞台的格局,成为文化大革命时期文艺创作的主流形象。这种转变并非偶然,而是当时政治、文化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革命样板戏,从本质上讲,首先是一种政治文学思潮中的戏剧文学现象。它的诞生与当时的政治环境紧密相连,是政治理念在戏剧文学领域的具体体现。 在政治社会化的推动下,革命样板戏引发了全民学唱的传播热潮,其传播盛况空前,远远超过当今任何一种传播现象。当《红灯记》在全国上演时,其影响力迅速蔓延至社会的各个角落。全中国的姑娘仿佛受到一种无形力量的指引,几乎都梳起了“铁梅”式的粗黑大辫子,这种发型成为那个时代的时尚标志,同时也象征着对革命精神的认同与追随。而剧中人物怒目而视的表情,也成为当年最具代表性的符号之一,它传递出对敌人的愤怒与抗争精神。 《沙家浜》演出之际,街头巷尾随处可闻人们模仿阿庆嫂与刁德一对唱的声音。这段经典的对唱不仅展现了人物之间的智慧较量,也成为大众娱乐与表达情感的一种方式。《红色娘子军》中的经典唱段“向前进,向前进!战士的责任重,妇女的怨恨深。打碎铁锁链,翻身闹革命!我们娘子军,扛枪为人民!”更是深入人心,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几乎张口就能唱出。这些唱段宛如时代的强音,激励着人们投身于革命事业,为实现理想而奋斗。 在这八大样板戏中,交响乐《沙家浜》却略显“特殊”。由于其艺术表现形式相对较为新颖,与当时人们长期以来形成的审美习惯存在一定差异,所以在传播范围上,它没有其他七部样板戏那般广泛。这种差异使得人们在提及“八大样板戏”时,往往会下意识地将其排除在外。与此同时,另一部京剧《龙江颂》却逐渐崭露头角,被列入到八部样板戏的行列之中。 除了传播范围这一因素外,《龙江颂》自身的特点也使其具备了成为样板戏的条件。《龙江颂》的公映时间与《海港》相近,在叙事结构方面,它与《海港》《奇袭白虎团》有着诸多相似之处。其故事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模仿了第一期样板戏的套路,从情节架构到人物塑造,都能看到第一期样板戏的影子。 这种对成功模式的借鉴,使得《龙江颂》在艺术创作上有了一定的基础,也更容易被当时的观众所接受。基于以上原因,《龙江颂》顺理成章地被纳入到本研究的范畴之中。 “八亿人民八部戏”,这一特殊的传播形式与盛况,生动地反映了当时文艺创作的单一性与集中性。在那个时代,这八部样板戏成为人们文化生活的主要内容,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与审美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