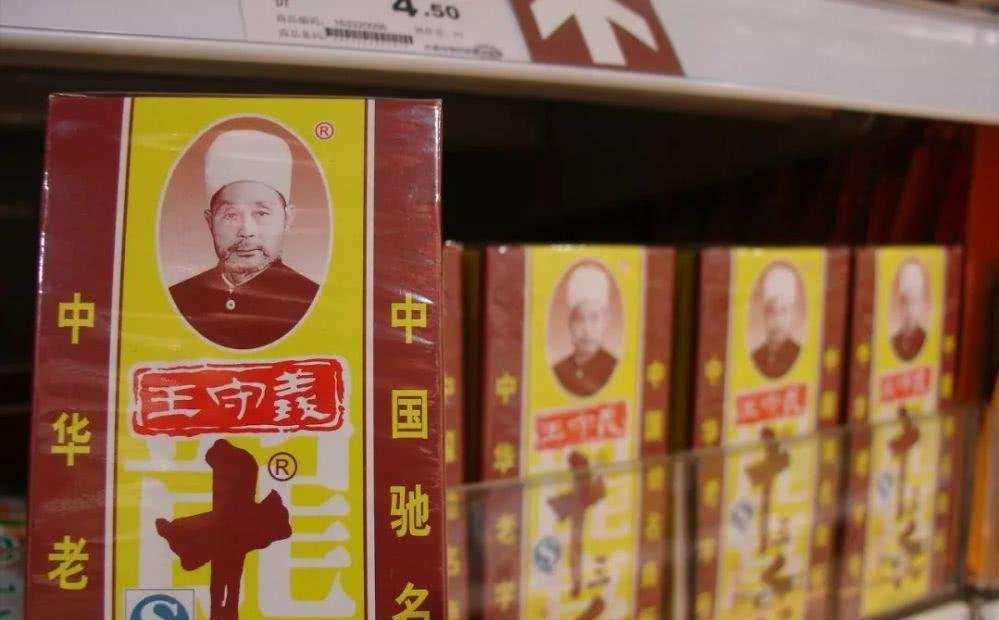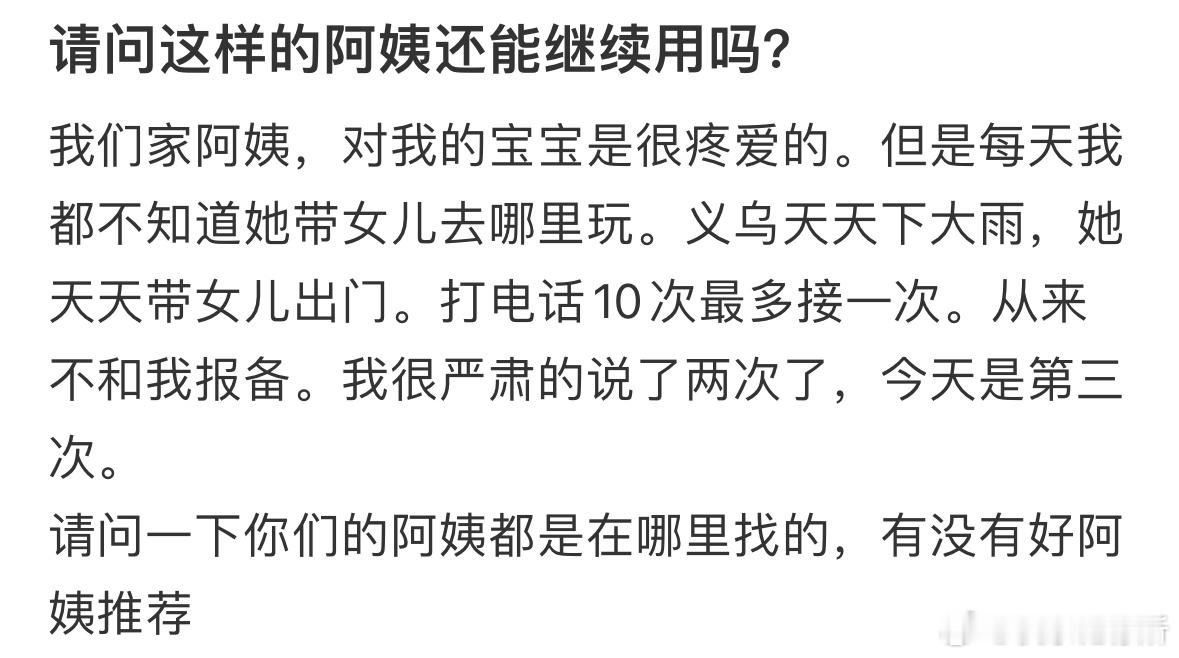1997年,陈景润的妻子坐在丈夫的雕塑旁,紧紧搂住“丈夫”的肩膀,留下了这张感人至深的合影........
1997年春,厦门大学海韵园里,阳光洒在青翠的草坪上,一座铜像安静地伫立。那是陈景润,目光深邃,仿佛仍在凝视数学的星空。他的妻子由昆缓缓走来,坐在铜像旁,手臂轻轻环住冰冷的“肩膀”。她低头,眼角湿润,嘴角却挂着浅浅的笑。
摄影师按下快门,定格了这瞬间:一个女人对丈夫的思念,一段跨越生死的爱,与一个未尽的数学梦。照片传开,感动了无数人。可这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故事?
1941年的福建福州,战火弥漫,8岁的陈景润跟着家人逃进闽侯山区。破旧的茅屋里,风从缝隙钻进来,他裹着单薄的衣裳,缩在角落,手里却攥着一本破旧的算术书。家里12个兄弟姐妹,饭都吃不饱,可他总能从数字里找到安宁。战争结束后,1945年回到福州,他考进福州英华中学。数学老师沈元在课堂上讲起哥德巴赫猜想——“每个大于2的偶数都能写成两个素数之和”——这个200多年的数学谜题像一颗种子,深深埋进少年陈景润的心里。
他不善言辞,瘦弱的身体常被同学嘲笑,但他从不在意。课间别人嬉戏,他趴在课桌上演算,草稿纸上满是密密麻麻的公式。1949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入厦门大学数理系。那时的厦大,校园里弥漫着海风的咸味,陈景润却像个苦行僧,泡在图书馆,啃着数学家华罗庚的《堆垒素数论》。他常在宿舍的木桌上熬夜,煤油灯昏黄的光映着他专注的侧脸。
1953年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北京第四中学教书,可口齿不清的他被学生嫌弃,甚至被学校“劝退”。那段日子,他站在空荡的教室,望着黑板上的公式,第一次感到梦想的沉重。
1954年,厦门大学校长王亚南听闻陈景润的遭遇,拍板让他回校当图书管理员。整理书架的间隙,他偷空钻研数论,桌上堆满了借来的数学书。1956年,他写出《塔内问题》论文,改进了华罗庚的研究成果。消息传到北京,华罗庚眼睛一亮,亲自把他调到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1957年,陈景润踏进中科院的大门,推开一间六平米的小屋,里面只有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和一盏灯。他却觉得,这是他离哥德巴赫猜想最近的地方。
1966年,北京的夏天闷热,小屋里没有风扇,陈景润却埋头在一堆草稿纸中。他的肺结核早已拖垮了身体,手指微微颤抖,可他仍一笔一画推演公式。经过无数个日夜,他终于证明:“每个足够大的偶数都能写成一个素数加一个不超过两个素因子的数的和。”这便是震惊世界的“陈氏定理”,又称“1+2”。
1973年,他在《中国科学》发表详细证明,国际数学界为之沸腾。英国数学家哈伯斯坦在《筛法》中写道:“陈氏定理是筛法理论的光辉顶点。”那一年,陈景润的名字响彻全球,他却依旧穿着旧布鞋,住在逼仄的小屋,桌上还是那盏昏黄的灯。
可命运从不温柔。1977年,陈景润住进北京309医院,肺病加重,帕金森病的症状也开始显现。他握笔的手抖得像秋天的落叶,连公式都写不完整。就在这低谷中,一个身影悄然走进他的世界——军医由昆。她27岁,来自武汉军区医院,温柔又细腻。查房时,陈景润捧着数学书,试探着跟她聊了几句。医院的后平台上,两人一起晾衣服,聊英语,聊生活,彼此的心慢慢靠近。1978年春天,他鼓起勇气表白,由昆红着脸点头。1980年,他们结婚,次年有了儿子陈由伟,名字里藏着两人相濡以沫的深情。
1984年,陈景润骑自行车时被撞,头部重伤,帕金森病加速恶化。他的手抖得连筷子都拿不稳,写字更成了奢望。可他仍不甘心,躺在病床上,嘴里念叨着公式,让由昆帮他记录。医院的病房里,白墙斑驳,窗外梧桐树影摇晃,由昆坐在床边,握着他的手,细心抄下他断续的思路。那些公式,像他生命的延续,承载着他对哥德巴赫猜想的执念。
由昆不仅是他生活的支柱,也成了他研究的后盾。她学会整理复杂的数学手稿,帮他回复学术信件,甚至推着他去参加学术会议。陈景润常说:“有她在,我才能多想几道题。”可病魔无情,1996年3月19日,肺炎夺走了他的生命,年仅62岁。弥留之际,他还在低语:“1+1……还没证明……”由昆握着他的手,泪水滑落,却强忍着不让他看见。
1997年,陈景润去世一周年,由昆带着15岁的陈由伟回到厦门大学。海韵园里,铜像上的陈景润目光坚毅,仿佛从未离开。她轻轻抚摸雕像的肩膀,坐下,紧紧搂住,眼泪终于决堤。那一刻,她不是在拥抱冰冷的铜像,而是在拥抱那个为数学耗尽一生的男人。摄影师捕捉到这一幕,照片传遍全国,成了无数人心中的经典。
而这张合影,不只是由昆的思念,更是陈景润精神的象征。他用一生告诉我们:再苦的日子,只要心怀梦想,就能翻篇。他的故事,由昆守护,儿子传承,仍在数学的天空闪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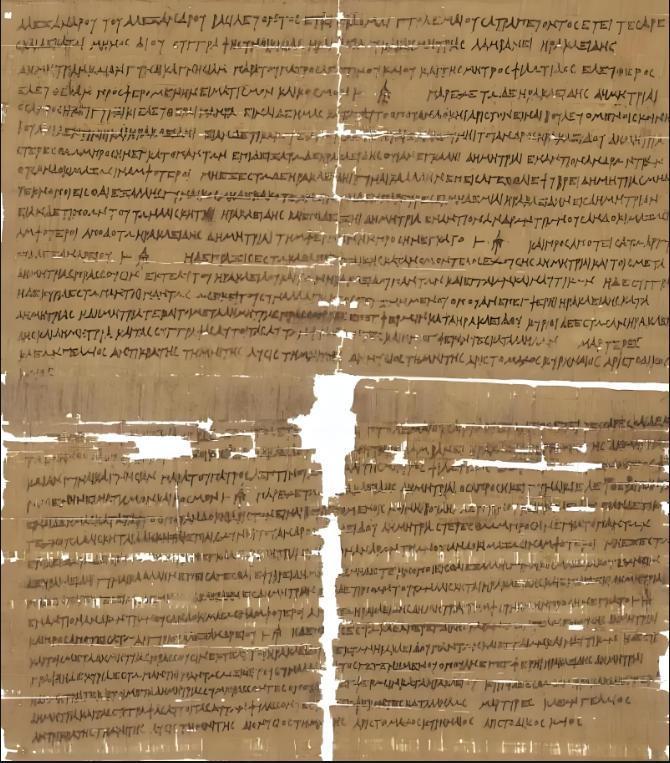
![女儿过生日邀请同学,我心里有点不舒服[裂开]](http://image.uczzd.cn/46795969549256464.jpg?id=0)
![一面之缘的师兄[哭哭]](http://image.uczzd.cn/1371727644479210818.jpg?id=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