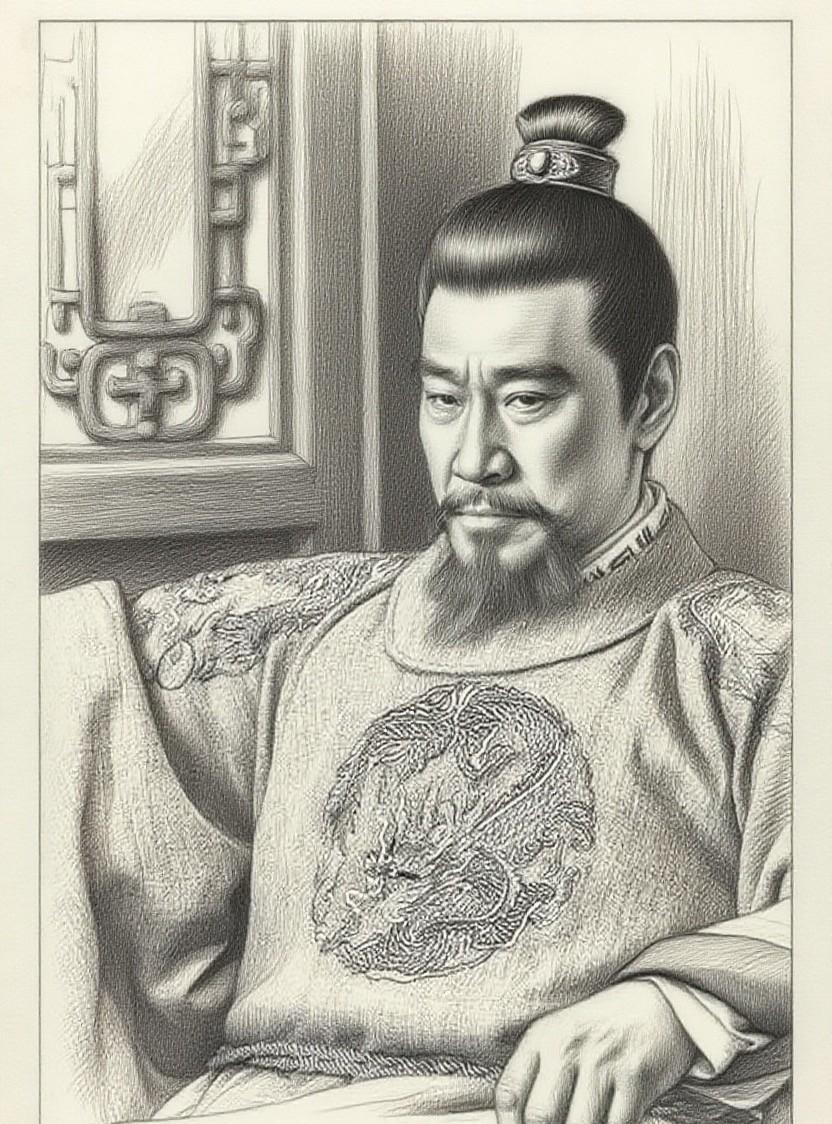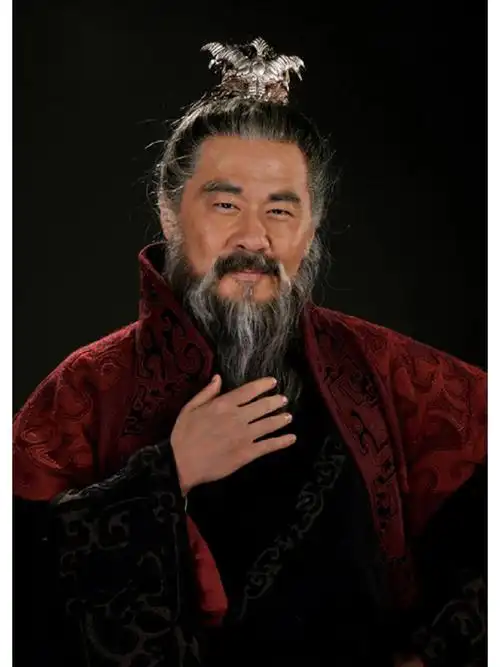1648年,清宫内外风起云涌。一个摄政王,一位太后,一个前皇太子的死,掀起了帝国权力场最险恶的一幕。多尔衮,手握天下,竟敢处死自己侄子豪格,还夺了其妻妾。孝庄太后冷眼旁观,却心里早已起算。
清太宗皇太极去世后,继承人选举像一场赌局。皇长子豪格,嫡出,自负理应登基;多尔衮,幼子,兵权在手,不愿屈人之下。二人虽是叔侄,但骨子里的竞争,比敌人还冷。
1643年,太宗猝死。豪格准备继位,多尔衮却抢先拥立年仅六岁的顺治,自己做了摄政王。这一手漂亮,却也埋下仇恨。豪格没哭,没闹,只是暗下决心——他会靠战功再夺回一切。
接下来的几年,他在西南平川蜀、剿张献忠、立战功,越打越猛。但功劳越大,多尔衮越忌惮。一个已经失权的太子,一旦赢得民心,迟早威胁摄政的位置。
1646年,豪格回京,一身战袍,气势逼人;1648年初,顺治设宴为他庆功,百官山呼。就在这喜庆背后,一场杀局悄悄布好。
1648年正月,豪格刚刚结束巡抚之职,便被下令逮捕。罪名不多,只有三条:私通旧部、越权独断、图谋不轨。
这几条,看似空泛,却无从辩驳。摄政王说你有罪,你就有罪。皇帝年幼,朝中重臣几乎都是多尔衮亲信。很快,豪格被幽禁,削爵除名,紧接着死讯传出。官方口径是自尽,没人信。真正的原因,没人敢问。
豪格死了,年仅39岁。死后不久,多尔衮开始清点“遗产”。侄子的正妻、妾室,连带女眷,一一登记分赏。他本人甚至将豪格福晋纳入私府。
朝野震动,人人自危。清宫上下都知道,这不是一桩亲情事故,而是一次政治示威。多尔衮宣告:别妄想挑战我的权威,哪怕你姓爱新觉罗,也一样死。
豪格的死,让宫中一人彻夜难眠——孝庄太后。
她是顺治的母亲,也是前朝的王妃,亲历皇位之争、子嗣纷争。她知道,摄政王再不收权,顺治将形同傀儡。而多尔衮,已从“辅政叔父”升至“皇父摄政王”,几乎取代皇帝本尊。
孝庄没有喊口号,也没当场翻脸。她知道硬碰硬没用。她开始悄悄扶持顺治亲信,调动旗主济尔哈朗、索尼,重新部署内务府与侍卫体制。她还命人整理豪格生平事迹,为日后翻案做准备。
1648年年末,多尔衮以“皇父”身份主持国政,权力至巅。可就在这一年,他突然感到朝堂气氛变了——他的话,有人敢驳;他的旨,有人敢延迟执行。他知道,孝庄开始动手了。
一场狩猎成为转折。
1650年,多尔衮在北郊骑射时坠马,膝骨断裂,卧床不起。这一伤,像是命运给他的最后警告。朝中风声骤变,亲信变得冷淡,密折越来越少。
孝庄抓住机会,联手顺治与索尼,迅速下诏:废除“皇父”封号,取消摄政特权,查抄其府。没过几月,多尔衮病死,年仅39岁。死后不久,棺材还没合盖,他的名号、牌位、祭祀待遇全部被取消。
而豪格呢?死后三年,被追封为“和硕肃亲王”。他的冤屈在朝堂上堂而皇之昭雪,一纸诏书,将多尔衮的恶行一一列出。
曾经的摄政王,如今成为历史罪人。孝庄没有亲自动手,却主导了整场清算。
多尔衮不是没有本事。他征战四方、稳住政权,实属开国重臣。但他一旦染上权欲,就不再知止。他杀侄取妃,不顾宗法,甚至挑战皇权。最终,他成了宫廷政治自我吞噬的牺牲者。
孝庄也不是温婉太后。她懂得等待,擅长谋局,面对摄政压制能隐忍十年,再一朝翻盘。顺治登基之稳,她功不可没。
而豪格,这个英勇却悲剧的太子,最终没能抵过权谋的洪流。他的死,为满清皇权的确立付出代价,也让清宫明白一个道理:哪怕你是皇子,也得看谁在背后撑你。
1648年,那一串死亡的名字、那一条布满权谋的白绫,至今仍在清史上隐隐作痛。权力太重,亲情太轻,历史留下的,是一地碎骨,一页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