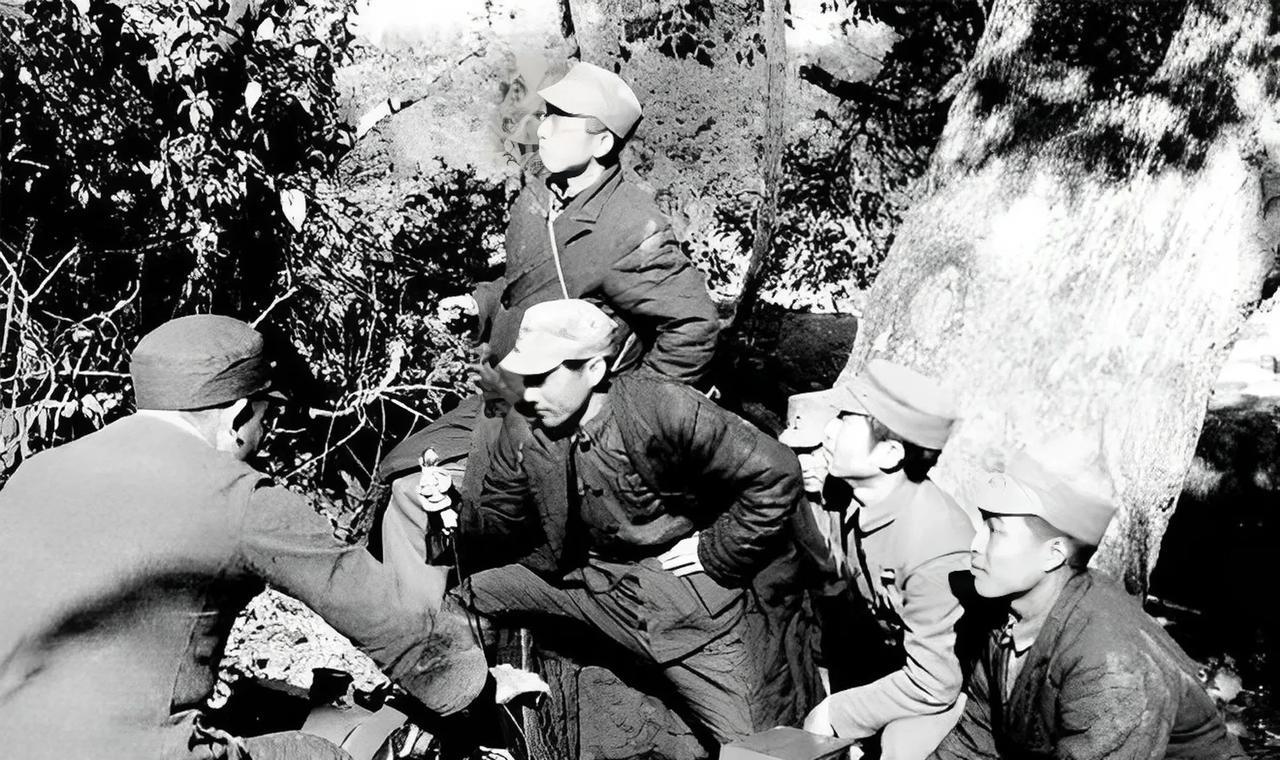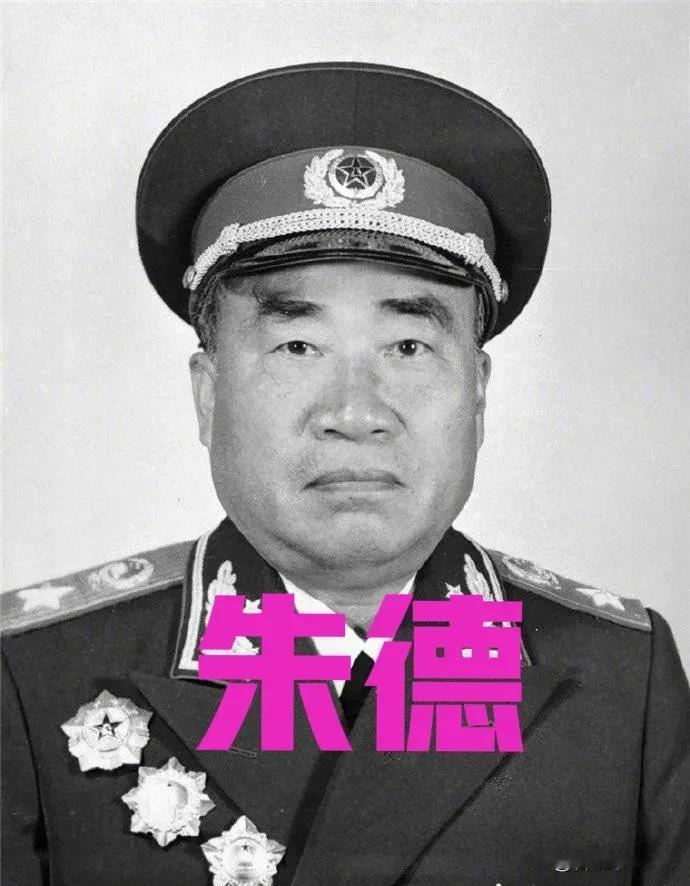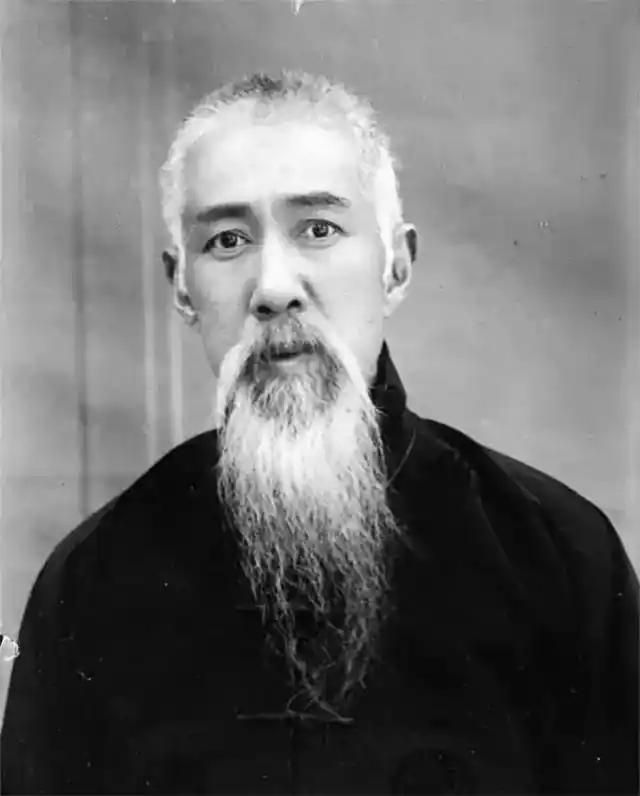1978年,女知青李亚茹返城前夜,她颤抖地解开衣扣,对丈夫说:“今晚,我们做最后一次夫妻吧!”次日,她抛下3岁女儿,头也不回的离开,42年后,女儿一句话让她泪流满面。 2020 年春天,头发全白的李亚茹站在东北小村的村口老槐树下。 树干上还留着当年孩子们刻下的印子,她一眼就认出来,这就是自己曾经生活了十年的地方。 如今村里多了不少砖瓦房,可那棵老槐树依旧矗立,让她悬了一路的心渐渐踏实下来。 晓燕把她让进里屋,倒了杯热气腾腾的茶。没有预想中的哭闹与质问,晓燕只是轻声说:“我爸说过,您回上海是有苦衷的,他不怪您。还说您肯定也想我。 ” 这句话像一把钥匙,瞬间打开了李亚茹积压四十二年的情绪,眼泪毫无征兆地涌了出来。 那晚,母女俩聊到半夜,晓燕细细讲着父亲刘宝华如何拉扯自己长大,村里这些年的变化; 李亚茹也终于说出了上海的生活,以及藏在心里四十多年的愧疚与想念。 时间倒回 1968 年,不到二十岁的李亚茹背着铺盖卷,从上海里弄的石库门来到了东北黑土地。 刚来时,她吃不惯玉米面饼子,睡不惯冰窖似的土炕,每到冬天,寒风刮得窗户纸哗啦作响,让她格外想念南方的温暖。 后来村里小学缺老师,村干部见她识文断字,便请她去教书,也就是在那里,她认识了本地老师刘宝华。 刘宝华话不多,却格外实在。知道李亚茹一个南方姑娘扛不动水缸,他就每天早起帮她挑两担水; 冬天担心她炕凉,天还没亮就去捡柴火,把炕烧得暖烘烘的。一来二去,两人渐渐生出感情,在村民们的撮合下成了家。 婚后第二年,女儿晓燕出生,一家三口挤在学校的小屋里,日子虽然清苦,却满是踏实的烟火气,李亚茹甚至一度觉得,自己这辈子就要在东北扎下根了。 可 1978 年的知青返城潮,打破了这份平静。不少已婚知青都陷入两难 ,想回城,带着配偶和孩子根本没有落脚的地方,也找不到工作; 不回,又实在惦记老家的亲人。李亚茹也收到了上海父母的信,说托人帮她找了小学老师的工作,但名额只给未婚的人,要是已婚,机会就会让给别人。 那三天,李亚茹几乎没合过眼,一边是从小长大的上海和生养自己的爹娘,一边是睡在身旁的丈夫、会喊 “妈妈” 的女儿,还有这个装满回忆的小屋。 她躲在被窝里哭,眼泪把枕头浸湿了一大片,最后还是咬咬牙,决定回上海。 离开的那天,刘宝华天没亮就起来,装了满满一袋玉米饼,煮了鸡蛋塞进她包里,又给她披上厚外套。 里屋传来晓燕的哭声,婆婆抱着孩子出来,晓燕伸着小手喊 “妈妈”,可李亚茹不敢回头,她攥紧包带快步往外走,生怕自己一回头,就再也迈不开离开的脚步。 回到上海后,李亚茹顺利进了父母托人找的小学当老师,后来经人介绍再婚,生了个儿子,日子过得也算顺顺当当。 可每当夜里静下来,东北的土炕、刘宝华劈柴的背影、晓燕扑进怀里时的温度,总会不自觉地浮现在脑海里。 这些念头被她深深藏在心里,四十二年里,从没跟现在的家人提起过。 另一边,刘宝华带着晓燕在村里苦苦支撑。他白天既要教书,又要下地干活,晓燕就一直跟在他身边打转。 没妈的孩子不仅没有自卑,反而像爸爸一样,性子稳当又实在。初中毕业后,晓燕留在村里帮着看店、干农活,后来还开了间卖油盐酱醋的小卖部,日子过得平淡却安稳。 十年前,刘宝华病重,他拉着晓燕的手说:“别恨你妈,她当年有难处。有机会,去上海找找她。” 晓燕把这话记在了心里,可始终不知道该怎么开口,她怕自己的出现,会打扰到母亲现在的生活。 像李亚茹这样的情况,当年在知青里并不少见。那时候的人跟着时代浪潮前行,很多选择都身不由己,背后藏着太多说不出口的无奈。 四十二年的时光,隔开了地域,却隔不断血脉与牵挂,最终在老槐树下,让这份迟到的亲情得以重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