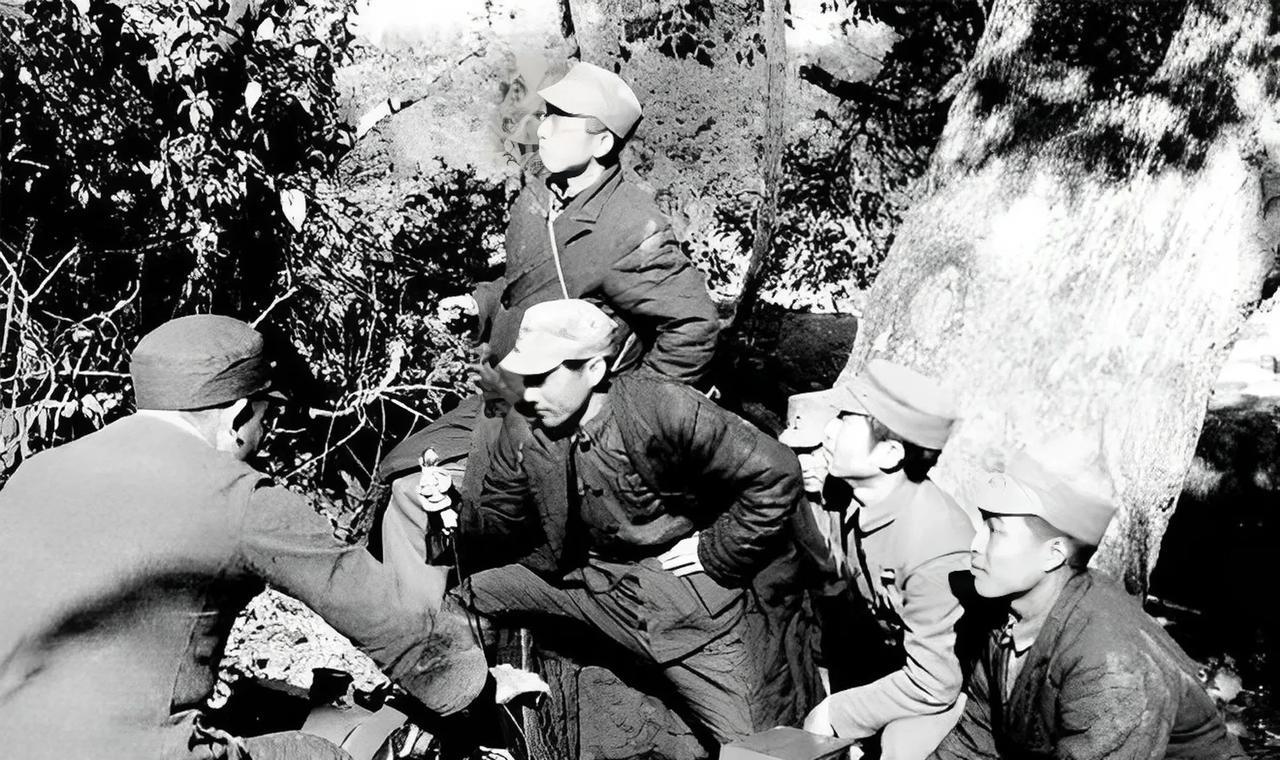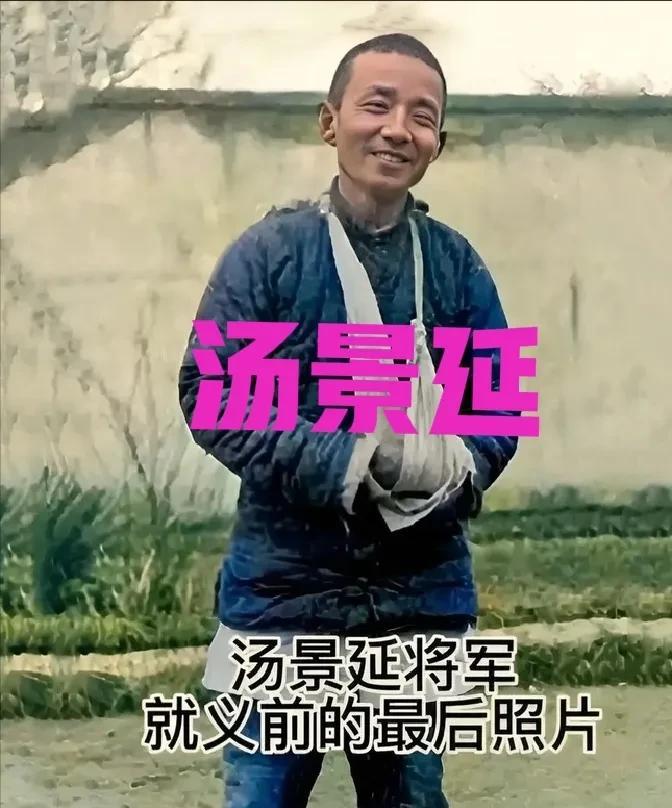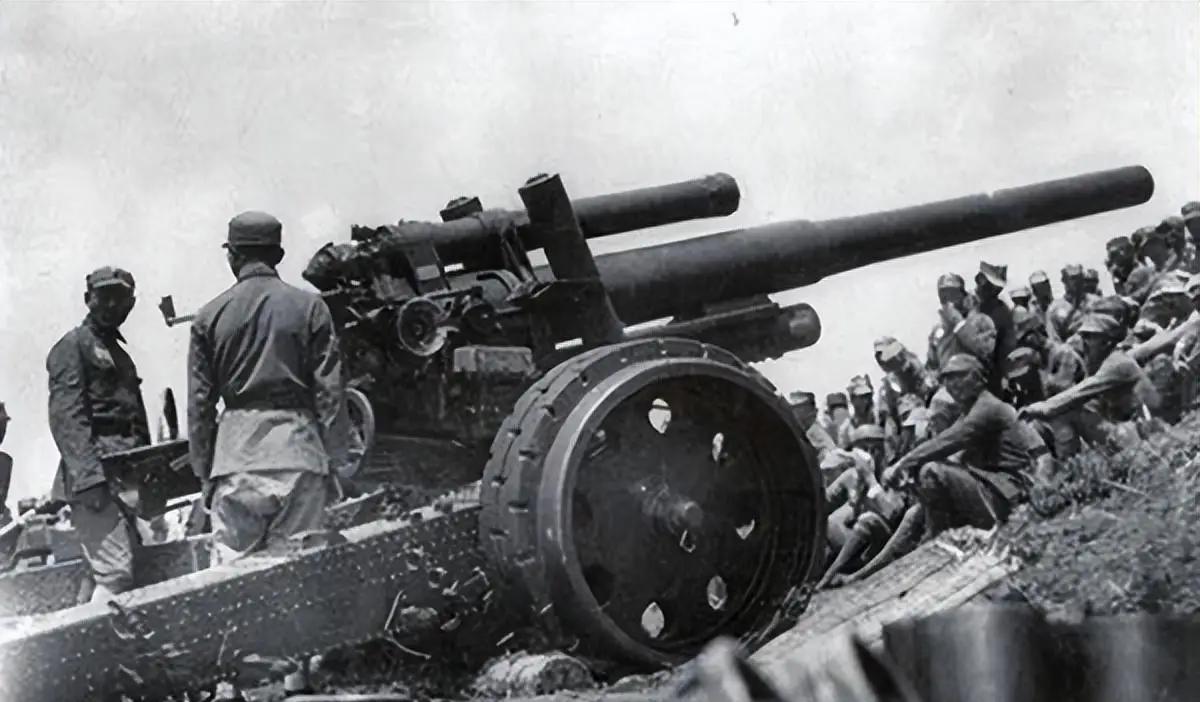1934年,新婚后不久,才女作家苏青就撞见丈夫与表嫂约会,她隐忍不发,接连生下5个孩子,一次,她向丈夫要钱买米,丈夫甩了她一耳光:“你也是知识分子,干嘛找我要钱,想要钱自己去赚啊!” (信息来源:中国作家网《苏青:事无不可对人言》) 您听说过苏青吗?就是四十年代上海滩跟张爱玲齐名的女作家,笔杆子比谁都硬,可谁能想到,她前半辈子竟在婚姻里熬成了泥里的小草,直到一记耳光,才把她抽醒了。 苏青本名冯和仪,1914年生在宁波的书香门第,爷爷是清末举人,爸爸是留美回来的银行职员,打小她就爱捧着书读,字写得秀,文章也有灵气。 可天不遂人愿,爸爸年纪轻轻没了,家里欠了一堆债,日子一下紧巴起来。 1933年,她考进中央大学外文系,刚摸到大学的门槛,家里就来人了,中学同学李钦后家愿意出钱帮她还债,条件是嫁给他。 那时候她才19岁,想着只要能继续念书,能帮家里扛债,咬咬牙就答应了。 婚礼办得风光,坐头等轿车,住上海国际饭店,报纸上都登了照片,可谁知道,这热闹背后全是刺。 新婚没几天,她就撞见丈夫和守寡的表嫂拉拉扯扯,更寒心的是,丈夫当着她的面跟表嫂唱《风流寡妇》,那软乎乎的调子像针一样扎耳朵。 往后更难熬,李钦后猜忌她,不让她回学校,好好的大学读了一半就断了,她被关在李家的宅子里,成了只会生孩子的机器。 接下来十年,她连生五个孩子,前四个都是女儿。每生一个,婆婆就在产房外摔暖盆,骂她“李家的罪人”。 第五胎终于生了儿子,家里人才对她稍微松了点,可那点好全落在孩子身上,没她的份。她每天围着孩子转,做饭、洗衣、缝补,像个陀螺,连抬头喘口气的机会都没有。 1942年,上海在打仗,物价飞得比风筝还高,李钦后失业在家,一分钱都不往家拿,米缸见了底。 苏青抱着饿哭的小女儿,硬着头皮找他要生活费。没想到他瞪着眼甩了她一耳光,骂道:“你是知识分子,干嘛找我要钱?想要钱自己赚啊!” 那记耳光打得她耳朵嗡嗡响,脸烫得能煎蛋,可更疼的是心里——这么多年,她忍了又忍,换来的就是这句话? 那天晚上,她坐在床头,看着熟睡的四个孩子,眼泪掉了下来,可哭完了,她突然想通了:不能再这么熬下去,得为自己活一把。 她锁上房门,铺开稿纸,把十年的委屈、痛苦、不甘,全写进文章里。她写自己怎么撞见丈夫的背叛,怎么被强迫退学,怎么连生五个孩子,怎么求一口饭吃,那些没说出口的苦,全变成了文字。 后来这些文章登在《风雨谈》杂志上,一下子火了。读者都说,这才是女人真实的日子啊,不是戏文里的风花雪月,是锅碗瓢盆里的委屈,是求生存的难。 苏青的《结婚十年》连出36版,稿费多得能买好几袋米,她一下子成了上海文坛最红的女作家,连张爱玲都夸她写得实在。 1944年,她带着四个女儿搬出租界里的亭子间,彻底跟李钦后断了关系。 她办了《天地》杂志,从约稿到编辑,从校对到发行,全自己来。 那时候她白天带孩子,晚上写稿,有时候累得握不住笔,可一想到孩子能吃饱,能上学,她就又有劲了。 邻居们都说,冯小姐变了,以前的她总是低着头,现在的她,走路都挺直了腰。 其实苏青的故事,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传奇,就是一个女人在苦难里熬,在绝望里醒,最后活成自己的光。 她从李太太变成了苏青,从依附丈夫的女人,变成了靠笔吃饭的作家。 她用自己的笔,写出了女人的苦,也写出了女人的硬,女人不是谁的附属品,能自己站着,也能自己活。 后来有人问她,后悔过吗?她笑着说,不后悔,那记耳光不是打她的脸,是打醒了她。 人活一世,总得拼一把,不为别人,为自己。 苏青的日子,其实离我们不远。就像老辈人常说的,日子再难,也得熬出个头; 女人再弱,也得有自己的底气。她的故事,不是悲剧,是一个女人从泥里爬起来,开出花的励志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