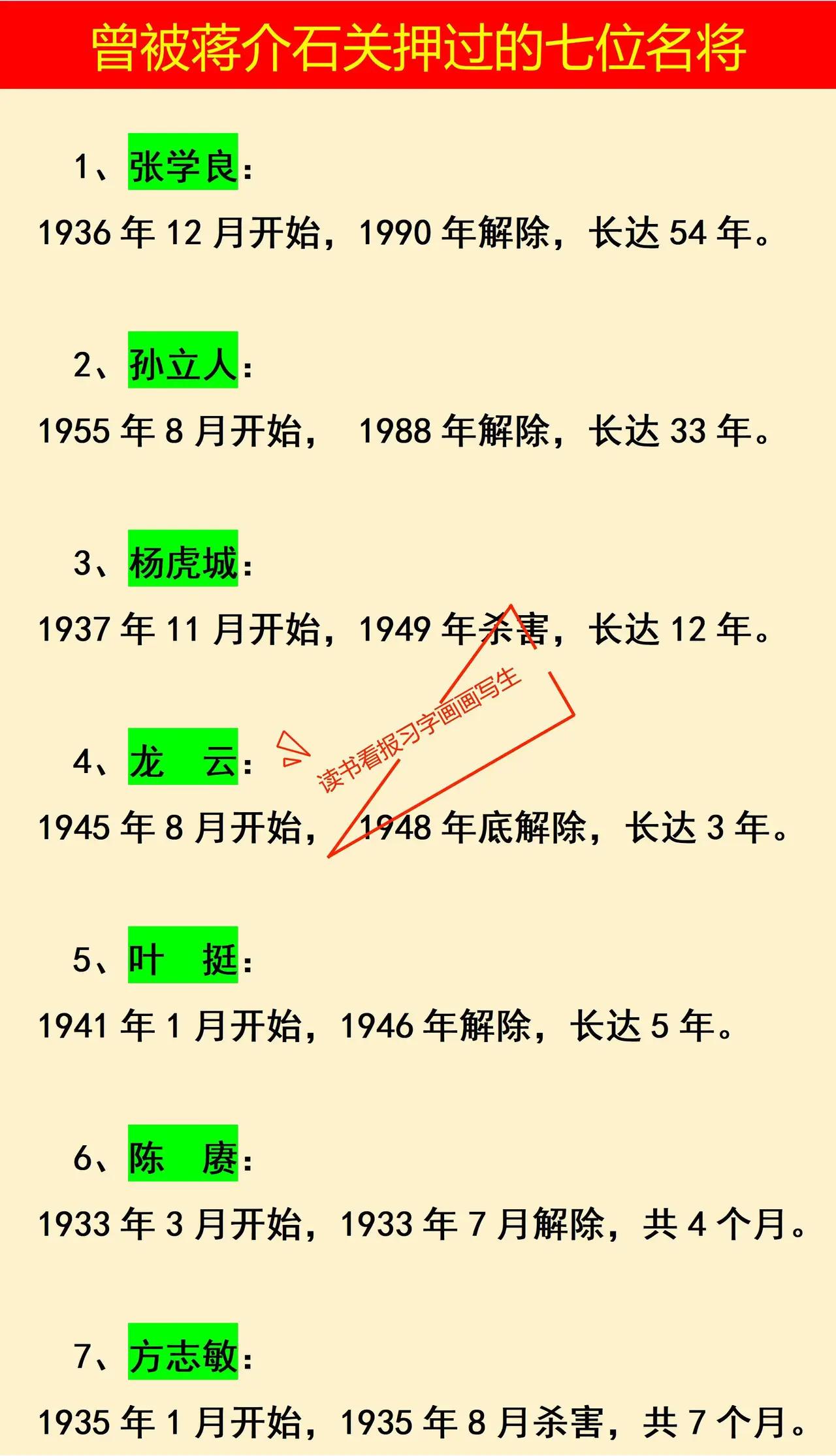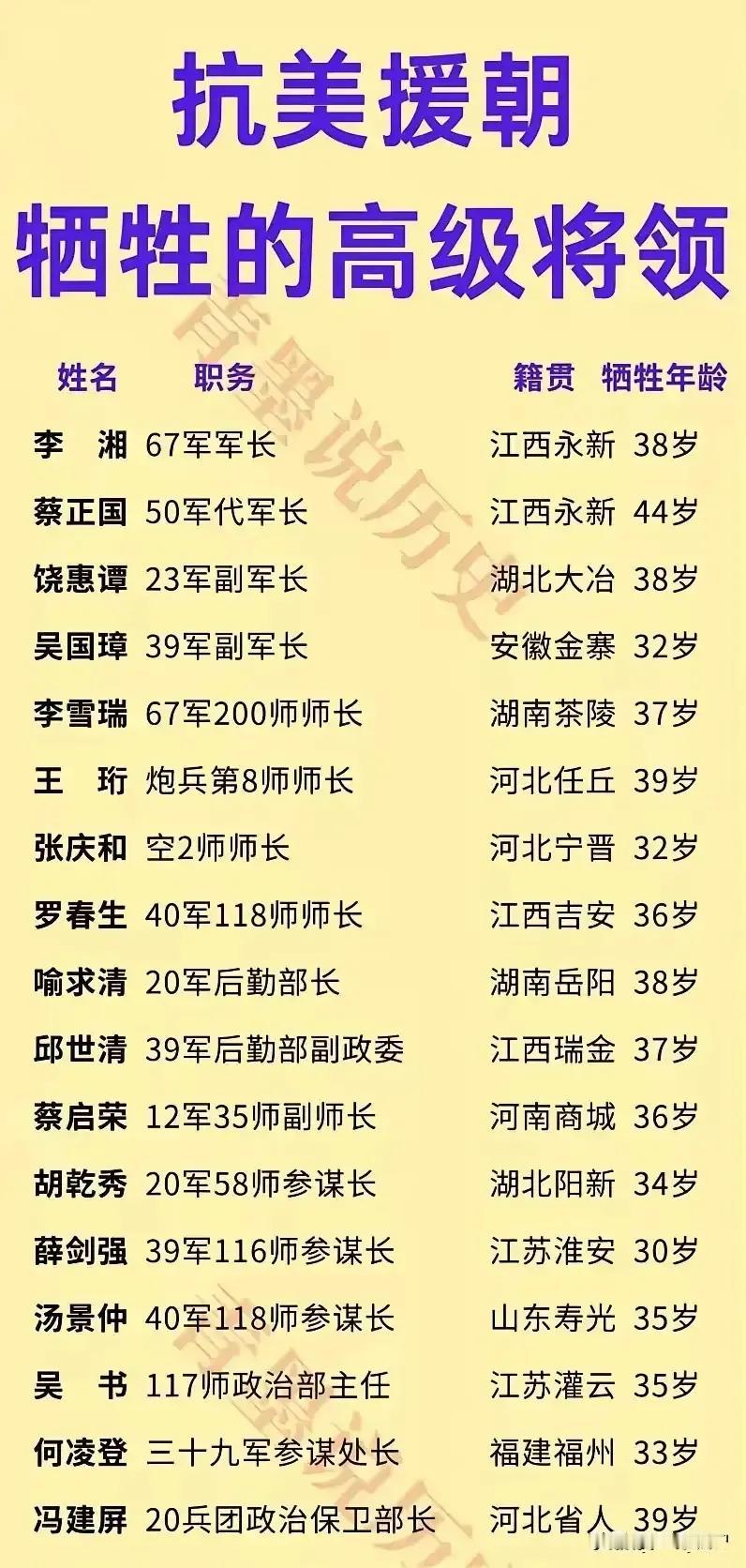1971年1月19日,林语堂参加一个饭局,将长女独自留在房间,也正是这一次疏忽,长女林如斯将自己吊在了屏风梁上。 林如斯,是林语堂的长女。人如其名,美丽如斯,聪慧如斯。她的离去,一直是父亲林语堂心中挥之不去的疼痛。 林如斯,1923年出生于厦门。父母对她非常宠爱,给她取名如斯。 如斯遗传了父亲的长相和气质,身材颀长,容貌清丽;她也遗传了父亲的文学才华。 受父亲的影响,林如斯从小喜欢写作,七八岁的时候,林如斯就给《西风》杂志投稿了。 1936年,林语堂带着全家去了美国。虽然身在国外,但是林语堂一直教导女儿们不要忘了自己的祖国,不要忘了祖国的传统文化。 —— 纽约的冬天冷得透骨,林家公寓里却烧着旺旺的壁炉。十三岁的如斯窝在父亲怀里,听他念《红楼梦》里的黛玉葬花,英文夹着中文,软糯的闽南腔在炭火旁打着旋。她眨巴着眼问:“爸爸,花儿掉在地上,为什么不捡起来还给枝头?”林语堂揉了揉她的发旋:“因为有些告别,是捡不回来的。”这句话,像钉子,早早钉进了如斯的心。 后来她考上哥伦比亚大学,穿呢子大衣,踩高跟鞋,走在曼哈顿街头,回头率不比电影明星低。可谁也看不出,牛仔裤包裹的腿,一天到晚发软。她失眠、掉秤、把面包撕成碎屑,却跟家里报平安:“我很好,别担心。”这时候的林语堂,正忙着写《苏东坡传》,隔着大洋,没嗅到女儿字里行间的药味。等察觉到,已来不及——如斯的手腕上,早已横七竖八,像被猫抓过的稿纸。 让她坠入深渊的,是一段被长辈夸赞的“好姻缘”。男方是父亲朋友的儿子,留洋博士,门当户对,婚礼请柬甚至提前印好。可男人有另一面:控制、贬低、拳打脚踢。如斯第一次挨耳光,是在图书馆门口,她刚拿出研究中国古代女性的论文稿。男人抢过去,随手扔进垃圾桶:“写这些破烂,能当饭吃?”她没哭,蹲身去捡稿纸,像捡自己碎了一地的自尊。回宿舍,她在日记里写:“花儿掉在地上,为什么没人帮我捡?”——父亲那句童年预言,鬼使神差地回来了。 离婚过程像剥一层皮。父亲拍电报:“回来吧,家是你的港口。”可港口也有雾。60年代的美国,对华人的偏见尚未散去,对离过婚的女人更是指指点点。如斯怕,怕自己的阴影落在父母身上,怕别人戳林语堂的脊梁骨:“瞧,大作家的女儿也离婚。”她强撑笑脸,陪父亲出席酒会,拍照时嘴角弯弯,照片外的手却把酒杯攥得发白。失眠更严重,一瓶安眠药,眨眼见底。 1971年1月19日,台北中央酒店走廊, carpet 厚得能把脚步声吞没。林语堂去参加文坛饭局,想着“让女儿静静”,没带她。房间里只剩如斯和一盏昏黄台灯。她写下最后一张字条:“爸爸,对不起,我撑不到春天了。”然后踩上板凳,把围巾抛向屏风横梁。等服务员发现,为时已晚——花儿真的捡不回来了。 林语堂抱着女儿的棺木,哭到直不起腰,嘴里反复一句话:“是爸爸太粗心,没听见你心里下雨。”此后十年,他再没出版一本书,只把如斯少年时的作文、日记、信札,一页页贴在书房墙上,像拼一幅永远缺块的拼图。访客进门,常见老人站在梯子上,用颤抖的手抚平纸角,嘴里念念有词:“你看,这丫头写‘希望’,点总是画成心形。” 有人叹:这么优秀,为何想不开?其实,优秀与脆弱并不冲突。光芒越盛,阴影越长;才华越横溢,自我攻击的刀越锋利。如斯的问题,不是“想不开”,而是“没人真正听见她”。连林语堂这样的大师,也会在父爱里失聪——他教会女儿吟诗作赋,却没教会她如何向暴力说“不”,如何允许自己不完美。她从小被夸“才女”“乖女”,于是把“失败”当原罪,把“离婚”当耻辱,把“抑郁”当矫情,直到黑狗彻底咬住喉咙。 今天,我们重提林如斯,不是为了消费悲剧,是给所有父母、所有“别人家的小孩”提个醒:优秀不等于刀枪不入,光鲜不等于幸福满仓。别只问孩子飞得高不高,先问她翅膀疼不疼。若她真想落地,请给她一个软垫,而不是一句“你要坚强”。毕竟,有些花儿掉在地上,捡回来,还能再开;错过了,就只能留在回忆里飘香。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