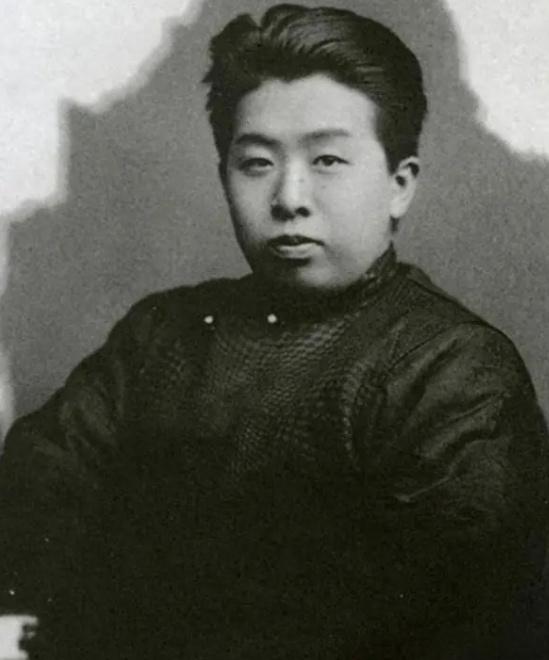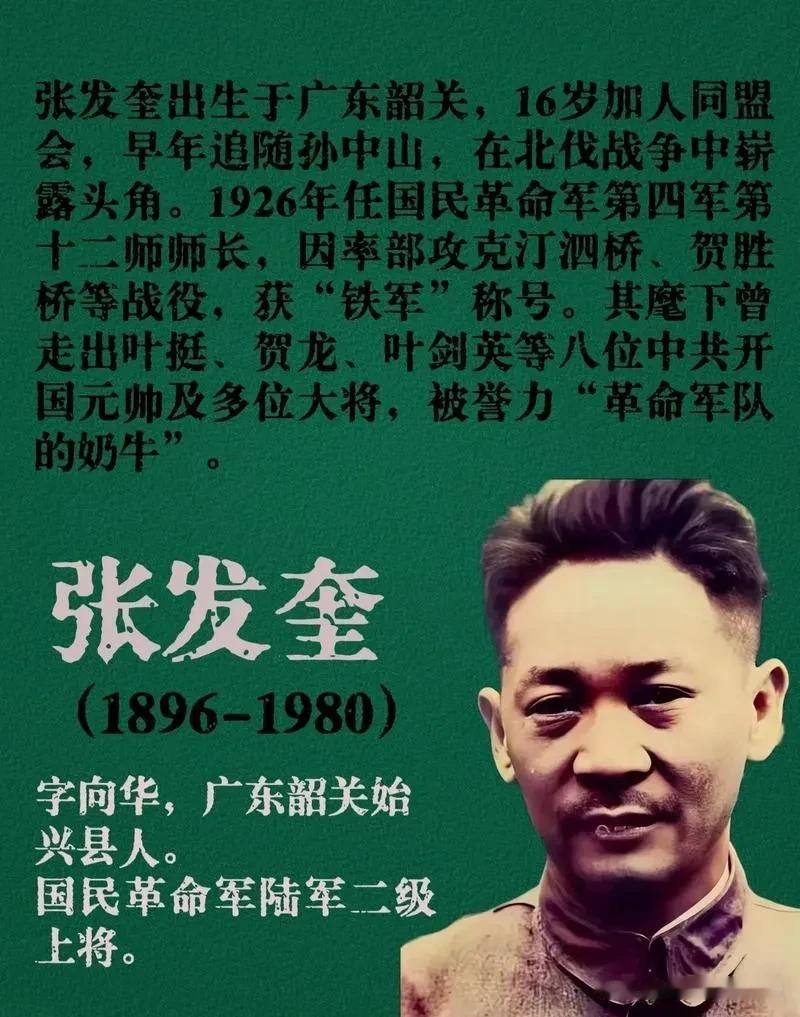1917年,40岁军阀王德庆临终前,攥17岁小妾的手腕,摸出檀木匣子,说:“藏好,别让人知道。”谁知,小妾转头就把木匣子给了军阀的儿子,并说:“有件事想求你。” 王德庆曾在湘西打仗,做事果断。现在他眼里满是担心,还泛着泪。王仪贞眼圈红了,含泪点头。那时她还不知道,这事会彻底改变她的人生。 王德庆突然去世,衡阳城炸了锅。王德庆家穷,16 岁当湘军,从马弁做到军阀,占了常德、衡阳一带。 他家三个姨太为争遗产,吵得厉害。王仪贞却捧着装银票的匣子,走到继子王志远门口。 她进屋跪下,举着匣子说:“大少爷,这钱您拿着。” 王志远很惊讶,看着比自己小两岁的庶母。两年前父亲娶她,他是反对的。 看着王仪贞清亮的眼睛,王志远满是疑问。王仪贞声音微抖却坚定:“我就一个请求,送我去明德女校读书。” 1917 年的湖南,这请求很出格。长沙明德女校开了三十年,上学的多是官宦小姐。 王仪贞家在衡阳城西,是织布的。15 岁陪母卖布时被王德庆看中,父亲按了聘礼单。没人想到,这被迫做妾的姑娘,两年后会做这决定。 王志远想了很久,答应了。他连夜给明德女校任教的表姐写信,又托人改王仪贞户籍为 “王氏贞”,瞒下她军阀妾室的身份。 1918 年春天,王仪贞坐乌篷船去长沙。船行渐远,衡阳城的影子越来越小。 在衡阳,有她被迫嫁人的老房,有王德庆给她银票的病房。更重要的是,她在那下定了改变命运的决心。 到了明德女校,王仪贞才知课程难。她从《诗经》学起,每天天不亮就去走廊背书。 上数学课,她拨算盘用力,手指磨疼了。她最爱英文课,外籍教师念 “knowledge is power” 时,她第一次觉得知识有用。 学校里有人背后说她出身不好,王仪贞没在意,一心学习。 期中考试,她国文第一,算术满分。连严傲的英国教师,都夸她有林徽因之才。 可命运难改。1920 年夏天,王仪贞在岳麓书院诗会,遇到北伐军将领何键。 何键是湖南醴陵人,懂文化,当时任湘军旅长。因反对军阀打仗,被排挤到长沙。 那天两人聊得投机,从《楚辞》聊到女子教育,直到天黑星星出来,还没停。 后来何键回忆:“那晚她说话,有湘女直爽,又有读书人谦和,像《诗经》里‘有美一人,清扬婉兮’。” 两人要结婚,长沙城议论多。有人骂何键丢脸面,有人笑王仪贞攀高枝。 何键不管闲话,在岳麓书院办婚礼,请徐特立当证婚人。 婚后,王仪贞没享清闲。她想为女子读书做事,办了湖南第一个女子识字班。 白天陪何键查军营,晚上油灯下改作业。怀孕后,她仍挺着肚子去难童学校上课。 1927 年长沙马日事变后,何键调任湖北省主席,王仪贞随他去武汉。 到武汉,她又办女子职业学校,教纺织女工学算术、认秤杆,让她们有手艺能养活自己。 一次遇工人罢工,场面乱还有流弹,王仪贞不怕,冒险调解。她说:“工人是为活下去才反抗。” 她有传统美德,又有新思想。当时《大公报》夸她是 “新女性的特别例子”。 抗战爆发,何键调去重庆,王仪贞带五个孩子辗转多地。 到重庆,她见孤儿无依,心里难受,就办了 “战时儿童保育会”,把孤儿接到歌乐山别墅。给他们饭吃,教他们读书。 孤儿小菊后来回忆:“何夫人教我读《幼学琼林》,说女孩子也要知天下事。她院中的湘妃竹,是从湖南移来的,说见竹要想家乡骨气。” 1949 年,何键要去台湾,劝王仪贞同去。她有自己的想法,决定留在大陆。 之后她带小儿子在上海定居,在虹口办了女子职业补习学校。 学生回忆,王仪贞上课总穿月白旗袍,发间插着何键送的翡翠簪子。 她讲课投入,激动时会拍桌子:“女孩子读书不是为嫁人,是要知自己能成什么样的人!”50 年代初,这想法很超前。 改革开放后,王仪贞快九十了,多次回国。1982 年春天,她站在衡阳湘江大桥上,看江里的货船。 她对侄孙女说:“当年我在这卖布,总盼着能识字。现在见街上姑娘都上学,才知那三十万大洋花得值。” 后来她捐出毕生积蓄,给湖南女子学院设 “明德奖学金”,要求受助学生 “读史以明智,知耻而后勇”。 1998 年,王仪贞在洛杉矶去世。整理遗物时,发现一本发黄的笔记本。 笔记本最后一页写:“人生像下棋,落子不悔。我最庆幸的不是有三十万大洋,是用它换了读书机会。知识能冲破命运的束缚。” 王仪贞的一生很传奇。她从被迫做妾的女子,变成了为女子教育努力的人。她的故事,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