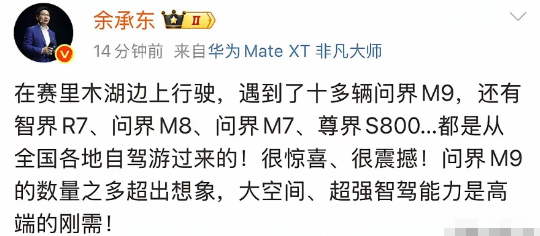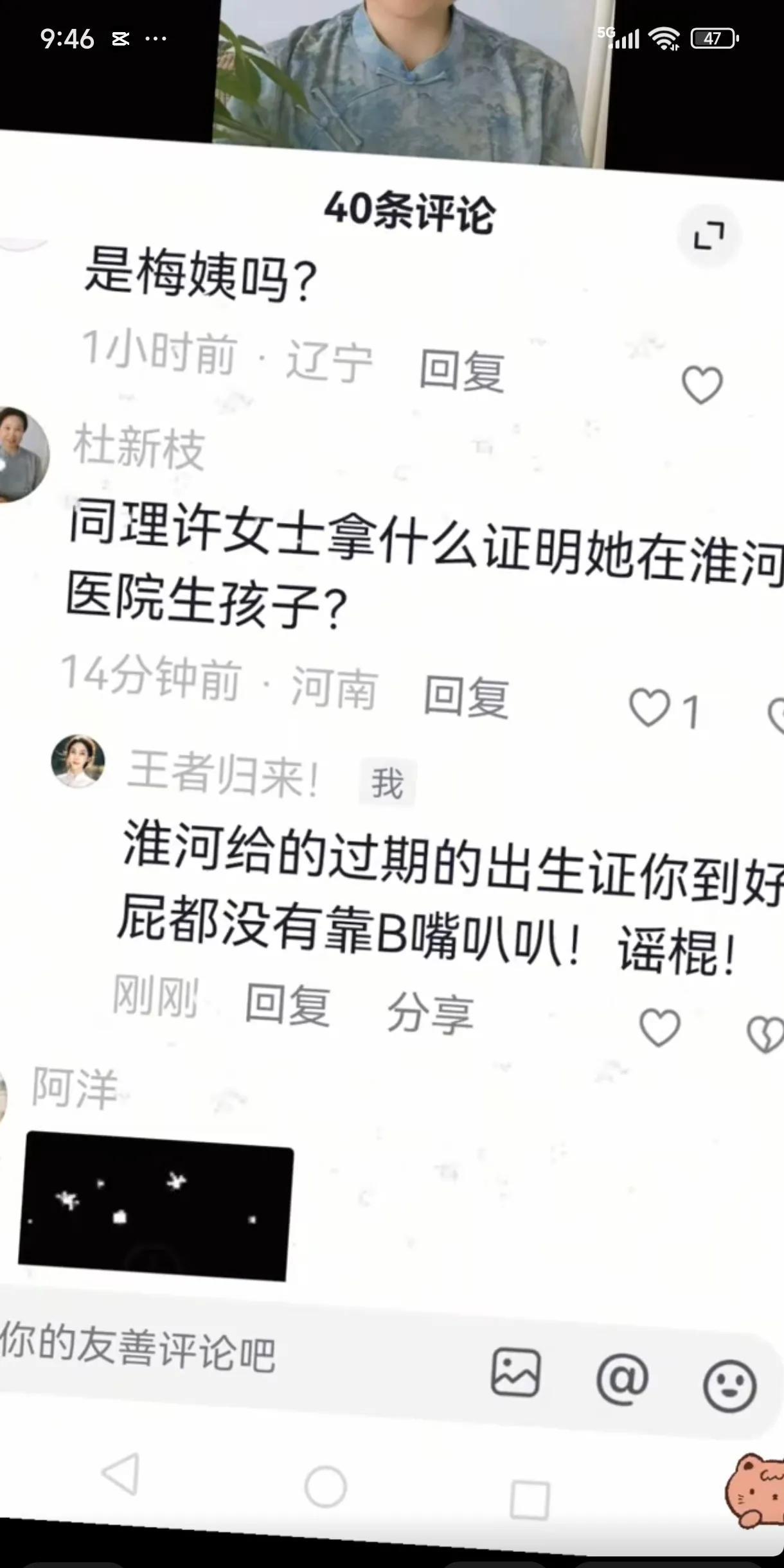一天,张爱玲的父亲趁妻子不在家,偷偷拿着针管来到张爱玲的房间,在昏迷的张爱玲胳膊上注射一针。房间里的大烟味混着药味,昏黄灯光下,父亲张志沂的影子落在墙上,像块沉重的黑布。 彼时张爱玲正发着疟疾,被反锁在屋里快半个月,高烧烧得意识模糊,若不是老佣人蒋干哭着求 “再拖要出人命”,这一针或许根本不会来。 药水推注的凉意透过皮肤传来,她没醒,可后来清醒时,只记得那针管的冰冷 ,比疟疾的高烧更让她寒心。 这不是她第一次感受父亲的凉薄。张爱玲家世显赫,祖父是晚清重臣张佩纶,祖母是李鸿章之女李菊藕,幼时家里有十几个佣人,白俄司机开着常换的汽车,她认车全凭司机的脸。 父亲张志沂是出了名的才子,通古文懂诗词,她七岁写小说,八岁仿写《摩登红楼梦》,父亲还笑着替她写了章回目录。 那时她最爱钻父亲的书房,闻着墨香混着烟味,看父亲把小报摊在书堆上,偶尔教她认生僻字 ,那是她童年里唯一的暖。 可这暖没撑多久。民国初年科举废除,张志沂的仕途梦碎了,他躲在书房抽大烟,后来还养了姨太。 母亲黄逸梵是将门之女,受新风气影响,看不惯丈夫的颓靡,在张爱玲四岁时借陪小姑留洋走了。 八岁时母亲归来,父母勉强复合三年,还是离了婚。 父亲很快续娶孙用蕃,张家彻底变了天。继母把两箱旧衣裳塞给读贵族学校的张爱玲,看着她裹着不合身的衣服在同学面前窘迫;她回家要学琴学费,父亲和继母正卧在烟榻上吞云吐雾,谁也没应声,只有弟弟挨着继母撒娇 。 那一刻,她知道自己是多余的。 真正的决裂是一巴掌。母亲想送她留洋,继母阻挠,她跟父亲说后去母亲住处住了一周。回家时,继母迎面扇她耳光,骂她 “眼里没这个家”。 她本能架住对方的手,恰好撞见父亲下楼。继母哭喊 “她打我”,张志沂没问缘由,冲上来就拳脚相加,把她踢得撞在墙角,浑身骨头像散了架。 她躺在地上,看着父亲走回烟榻,看着继母得意的笑,连老佣人都不敢扶她,后来弟弟还在信里说她 “有辱门楣”,这个家,早没了她的容身之地。 被打后,父亲把她反锁在房间,没人送水送饭。疟疾就是那时找上她的,高烧烧到糊涂时,她或许还想起过父亲教她写字的模样,可很快被剧痛淹没。 直到蒋干哭喊着求情,张志沂才拿着针管来。这一针救了她的命,却扎碎了最后一点父女情。 病愈后,她装作乖顺,偷偷摸清门警换班时辰,某个寒夜翻出张家大门,跑到姑姑家,从此再也没回去。 后来她去香港求学,战乱中断学业,返沪后借住姑姑家,连学费都要自己挣。弟弟让她向父亲要,她硬着头皮回了张宅。 父女对坐四十分钟,父亲只问了几句学业,答应给学费,却绝口不提生活费。那是他们最后一面,学费到账后,张爱玲再也没找过父亲 , 她宁愿熬夜写稿,也不愿再看一次父亲的冷漠。 那些萎靡与冷漠,是她对父亲最深的记忆。幼时书房的暖,早被拳脚和针管的冷覆盖,她再也没提过父亲替她写目录的事,只写 “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 袍子是张家的光环,虱子是父亲的暴力、继母的刻薄。 旁人说她薄情,成名后不寻父,婚变后不诉苦,赴美前悄无声息。可没人见过她被锁在屋里发疟疾的模样,没见过她被踢到墙角的绝望。 后来她遇胡兰成,那个比她大十四岁、有婚史的汪伪文胆,旁人不解她为何卑微到尘埃里,可只有她知道,胡兰成的几句体己话,是她从未从父亲那里得到的 “重视”。 自幼缺爱的人,最易被虚假温存蛊惑,哪怕那是深渊。 张爱玲说 “如见从前之我,便会原宥当下之我”。或许写那些情爱故事时,她也在原谅那个被父亲刺痛的自己。 她的文字里全是现实的影子,弄堂微雨、旗袍女子的愁绪,都是她的半生沧桑。 信源:(《张爱玲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