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有其名,实则一无是处的宋仁宗,不过是儒家吹嘘出来的明君。 表面上,他在位四十二年,朝廷宽和,士大夫敢言,文治看似辉煌。 但只要往细里看,一场轰轰烈烈的新政轰然倒塌,一次沉重的西夏战争换来屈辱岁赐,一次岭南起义差点让广州陷落,这些都足以揭开“仁宗明君”的幻象。 若不揭开这层光环,很多人可能真会被儒家史官的笔墨骗过去。 宋仁宗被推上神坛,很大一部分是因为“士大夫共治”的氛围。科举把大批文臣送入庙堂,台谏可以在殿廷当面抨击皇帝的任命,这在封建王朝中极罕见。 比如包拯就敢在仁宗面前直言反对张尧佐升官。史书用这样的故事来营造一个“宽厚仁主”的形象。 可是换个角度看,当政权被文臣集团牢牢掌控时,皇帝的权威实际上被削空,仁宗的“宽厚”很可能出于不得已。 真要算明君,靠的是退让,还是靠的是解决问题的手腕? 这种矛盾在庆历年间表现得最清楚。 1043年,范仲淹、富弼等人提出“十事疏”,想从整顿吏治、精简冗官入手进行改革。 仁宗一开始支持,史书写他“诏富弼同范仲淹条理时政”,看起来果断。 可一年多后,反扑来了,新政动了大臣的利益,党争迅速爆发,欧阳修、范仲淹、富弼一个个被贬斥。 到了1045年,仁宗选择放手,不再坚持,新政就这样草草收场。从启动到崩溃,不到三年。 很多人依然说他“知人善任”,可我却觉得,这更像是“知难而退”。要问一句,一个连自己任命的改革者都保护不了的皇帝,何来“圣明”? 1038年西夏建国,宋夏之间爆发连年战争,宋军在西北疲于奔命,财政消耗巨大,最后在1044年签下“庆历和议”。 西夏重新称臣,宋则每年支付银十万两、绢十万匹、茶三万斤,还要重开榷场。 有人说这是“以和促稳”,但从财政角度看,这是长期出血,换来的边境稳定,是用岁赐堆出来的。 如果用金银绢茶堆出一个“太平”,那谁都能做“明君”,史书却大谈“仁宗的宽和外交”,这难道不是粉饰吗? 而且,边疆压力不仅来自西北,岭南的侬智高起义更是惊心动魄。 1052年,侬智高起兵数万,一路攻下邕州、柳州,甚至兵临广州。广州一旦陷落,整个岭南都会震荡。 朝廷仓促派狄青出征,狄青身披铁甲,亲自督战,才在1053年击败侬军,平乱后,桂林碑刻至今犹在,记载狄青的功绩。 可想想,如果不是狄青临危力挽狂澜,仁宗的南方版图很可能被撕开大口子。 结果史书一句“仁宗仁政感人,民心归附”就把责任轻轻带过,仿佛灾难只是南方小插曲,真相能被这样掩盖吗? 这些事件背后,是制度性的问题。北宋自立国以来就推行“以文驭武”,到仁宗朝更加明显。 枢密院和兵权分割,监军制度让将帅动辄受制,军队战斗力越来越弱。军队里充斥冗兵吃空饷,官场又是冗官成堆。 所谓“三冗”,成了国家的沉重包袱,仁宗没有解决,只是维持现状,财政压力不断加大,边境危机一波接一波。这哪里是“仁政”,分明是“无政”。 有人或许要说,仁宗在位时间长,社会整体算稳定,可稳定的代价是牺牲改革,忍受外患,承受财政崩塌的隐患。 史官笔下的仁宗是“宽厚圣主”,但事实摆在面前:庆历新政倒了,党争起了,西夏要岁赐,岭南差点丢城,财政被冗官冗兵拖垮。 这样的皇帝,真能算得上“千古明君”吗? 宋仁宗的“明君”形象,大半出自儒家士大夫的笔头,他们需要一个“理想化君主”来印证自己制度的价值。 可历史不该只有赞美,更要有剖析。剖开看,仁宗空有其名,实则一无是处。 一位“明君”,至少要在关键时刻展现担当,而仁宗的选择,总是退让,总是妥协,这样的皇帝,若不被吹捧,又该如何评价? 参考来源: 人民日报海外版:《庆历新政:改革的起与落》 光明日报客户端:《包拯直谏仁宗,敢言风骨何以形成》 国家民委官网“道中华”:《宋夏和议与西北互市的形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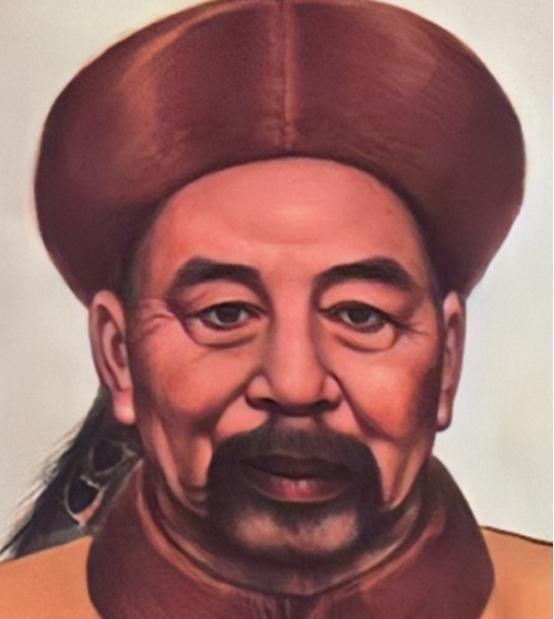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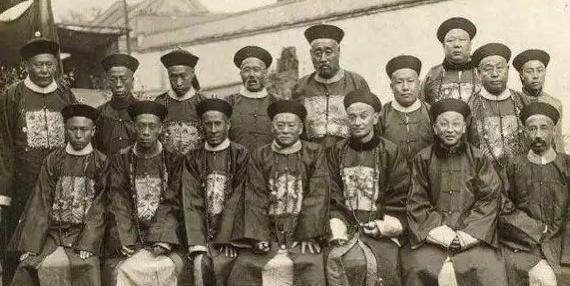


![你们说得都对![哭哭][哭哭][哭哭]](http://image.uczzd.cn/18404438782520287985.jpg?id=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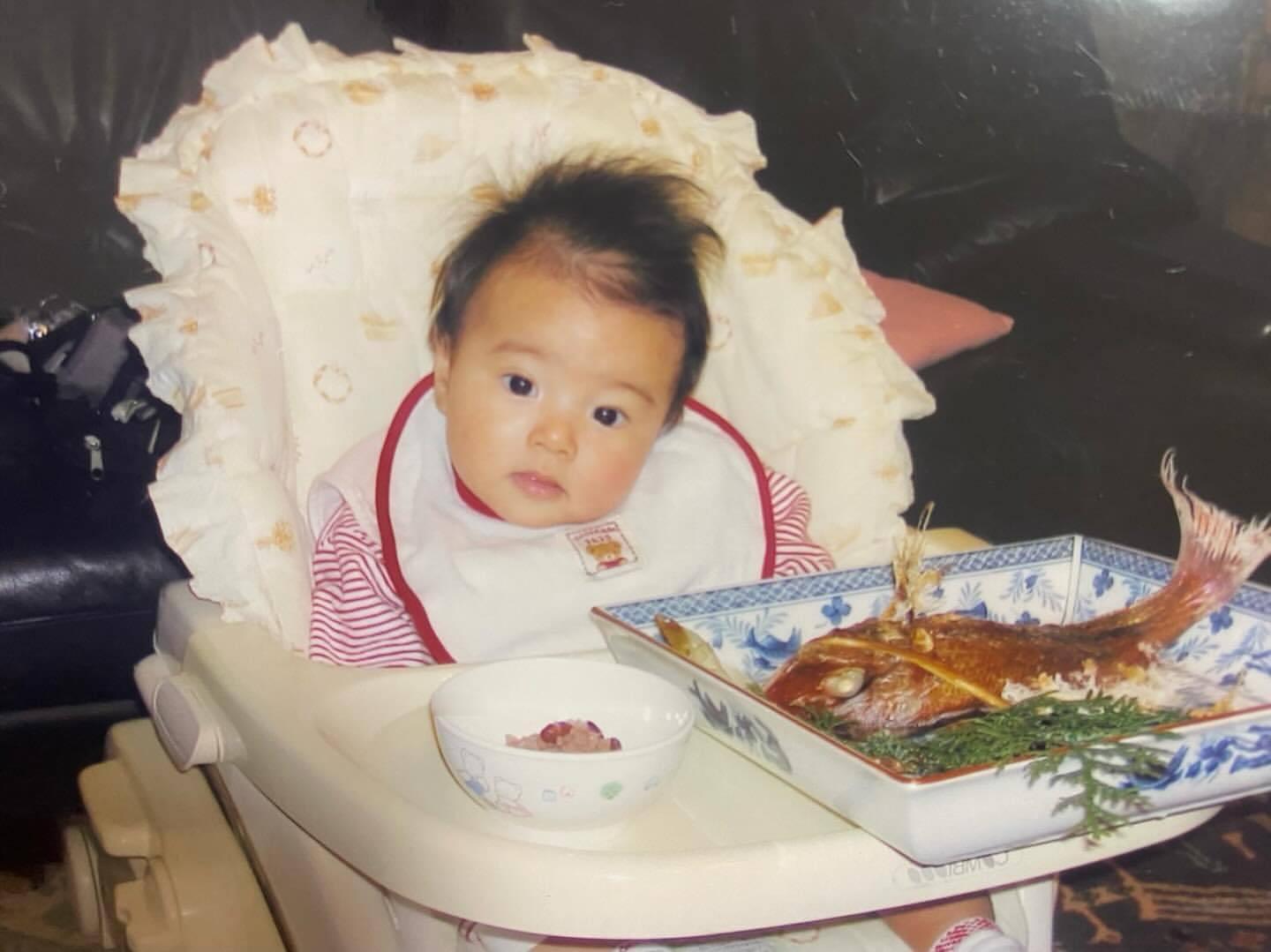


悼明
现在有一些人已经忘本了。儒家咋了?没有儒家,就没有华夏文明!!!汉武依靠儒家思想,北逐匈奴,成就了汉武的武功。唐宗依靠儒家思想,才有“贞观之治”!疏远魏征,偏离儒家思想,搞汉胡一家国策,却为安史之乱,华夏文明光速堕落埋下了祸根。儒家思想并不保守守旧,相反,宋朝欧阳文忠公继承了韩文公的思想,在其影响下,北宋的儒者们倡导“我注六经、六经注我”,形成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开放局面。没有蒙元、满清的刻意阉割,中国并不需要向外寻求救国真理和搞全盘西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