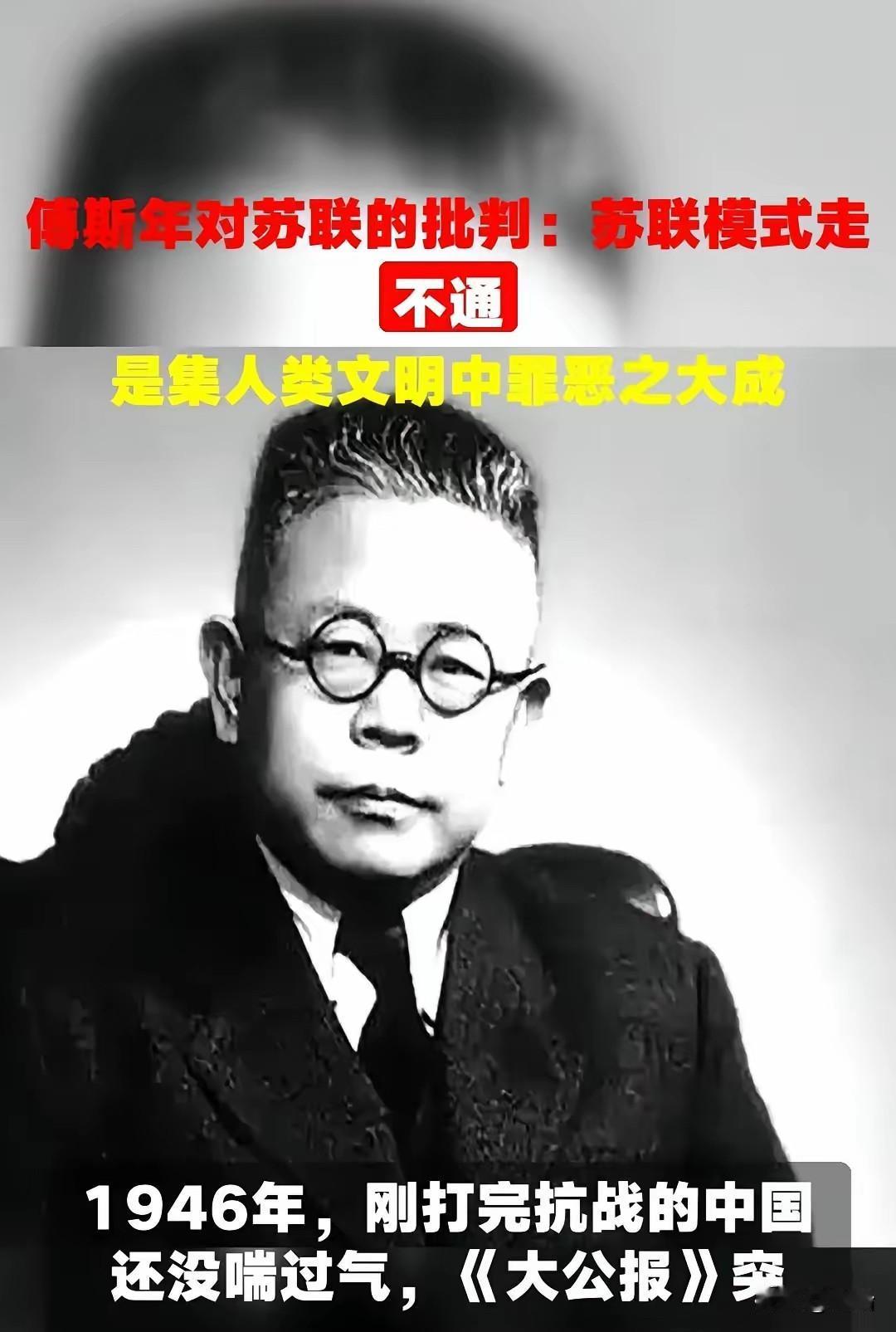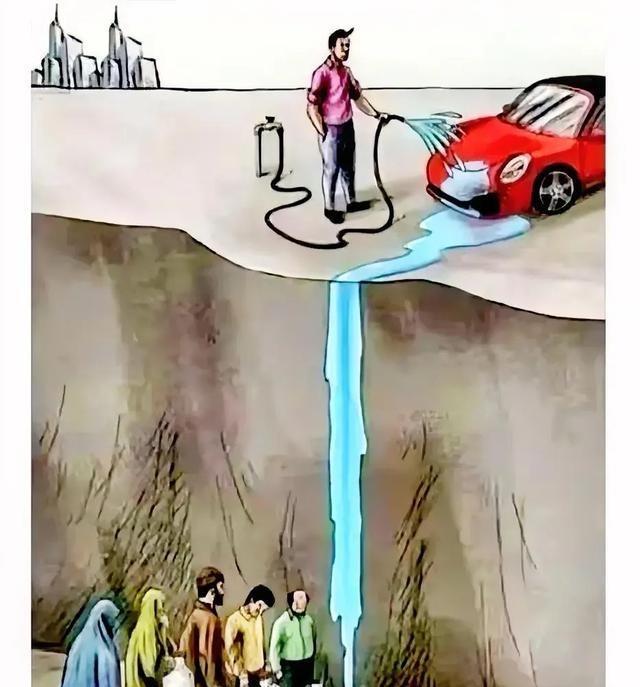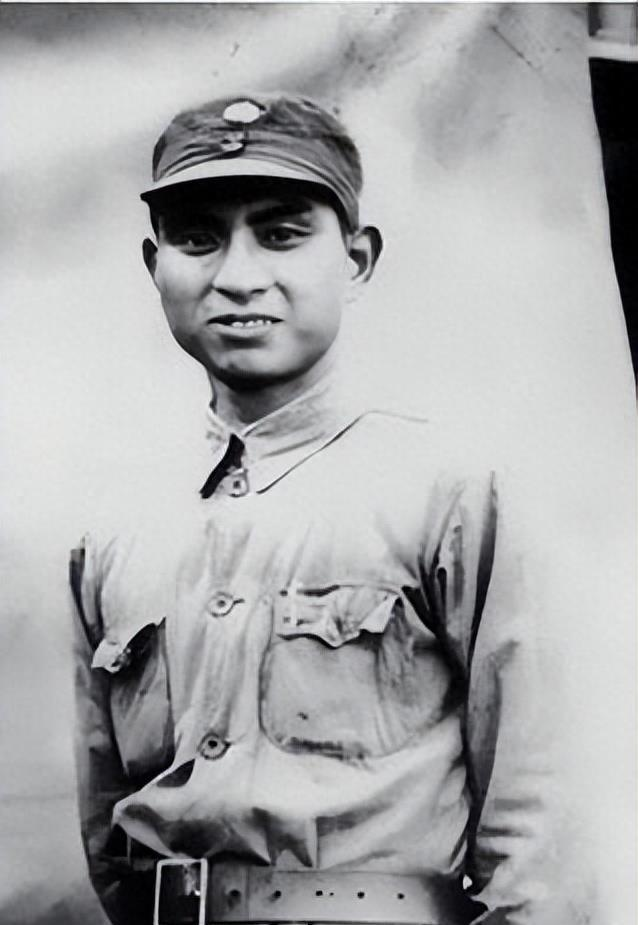前苏联靠缴获德国战利品撑场面,中国白手起家造出万吨水压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同样拥有万吨水压机的中苏两国,却走出了截然不同的技术路径。 苏联的设备是二战时从德国工厂拆来的战利品,连完整图纸都凑不齐,中国则在一片空白里自己画图纸、造零件,1962年那台矗立在上海重型机器厂的庞然大物,成了中国工业从“模仿”到“自创”的里程碑。 1958年,沈阳重型机器厂的工程师们第一次见到苏联提供的水压机照片时,就发现了不对劲。那些模糊的影像里,德国造的机身布满焊痕,明显是战时应急拼接的产物。 苏联专家耸耸肩说,能拆回来就不错了,哪还顾得上图纸。当时苏联自己的重型机械厂,也在靠这台缴获设备勉强维持生产,对中国提出的技术支持请求,只给了些无关痛痒的参数表。 上海江南造船厂的车间里,沈鸿带着工人用算盘计算水压机的受力数据。 这位没上过大学的总设计师,把家里的八仙桌改成绘图台,白天在车间看锻件如何变形,晚上就在油灯下画草图。 1960年中苏关系恶化后,苏联专家撤走时砸毁了部分半成品,留下的烂摊子反而让中国工程师彻底断了依赖的念头. 他们发现苏联提供的几张设计图里,关键部位的尺寸标注都有错误,显然是故意留下的陷阱。 万吨水压机的“心脏”——直径1.4米的工作缸,成了第一个拦路虎。 当时中国最大的镗床只能加工直径1米的零件,工人们想出土办法:在缸体上画好刻度,用几把镗刀轮流作业,每进刀0.5毫米就测量一次,花了整整45天才达到精度要求。 而苏联那台缴获设备的工作缸,因为长期受力不均,已经出现了0.3毫米的椭圆度,导致每次压制大型锻件时都要额外加固。 水压机的四根立柱,每根长18米、重80吨,需要整体锻造。鞍钢的平炉炼出的钢锭,第一次锻造时就出现裂纹。 技术人员跑到鞍钢的炼钢车间蹲了三个月,发现是脱氧工艺不过关,他们借鉴古代“百炼钢”的原理,增加了三次精炼工序,终于炼出合格的合金结构钢。 这些立柱后来用了50多年,2015年检修时检测,磨损量还不到设计标准的15%,而苏联那台设备的立柱,在1970年代就因为疲劳断裂更换过两次。 1962年6月22日,当3000吨压力缓缓压在试锻的钢坯上时,操作室里的人都屏住了呼吸。 这台中国人自己造的水压机,成功将20吨重的钢锭压成了需要的形状,而苏联那台设备,此时正因为密封件老化,每工作一小时就要停机换一次密封圈。 沈鸿在日记里写道:“别人给的终究是别人的,自己造的哪怕丑一点,用着心里踏实。” 当时西方媒体嘲笑中国造不出精密液压元件,说这台水压机不过是“钢铁堆起来的空架子”。 但他们不知道,上海液压件厂的工人用手工研磨的方法,让阀门的密封面达到了0.01毫米的精度,比苏联专家留下的标准还高3倍。 1964年,这台水压机为中国第一台万吨远洋货轮压制出主机曲轴,而苏联那台设备,此时已经因为缺乏备件,只能断断续续生产。 水压机的横梁铸件重达140吨,浇注时需要500名工人同时操作20台浇包。 为了防止铸件出现气孔,技术人员发明了“阶梯式浇注法”,让钢水从不同高度同时注入,这个办法后来被写进了中国重型机械制造的教科书。 而苏联那台设备的横梁,因为是战时仓促铸造,内部存在砂眼,每次压制超过8000吨就必须减速,严重影响效率。 1965年,当中国的万吨水压机开始为军工企业压制导弹发动机外壳时,苏联才意识到自己当年的技术封锁多么短视。 他们试图通过第三方接触,想换取中国的水压机技术参数,被中国工程师拒绝了。 沈鸿说,不是不分享,是他们当年给的“教训”太深刻,我们的技术标准里,藏着无数个日夜的摸索,这些不是几张图纸能换走的。 这台水压机后来被命名为“争气机”,它压制出的第一块大型锻件,现在还陈列在国家博物馆。 旁边的展柜里,放着苏联那台设备1980年代报废时的零件,上面的德国制造商标已经模糊不清。 两种技术路径的对比,在钢铁的沉默里写得明明白白:靠缴获得来的优势,终究会随着时间褪色;而自己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路,才能越走越宽。 参考资料:影像中的百年党史:1961年 我国建成万吨水压机:看看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