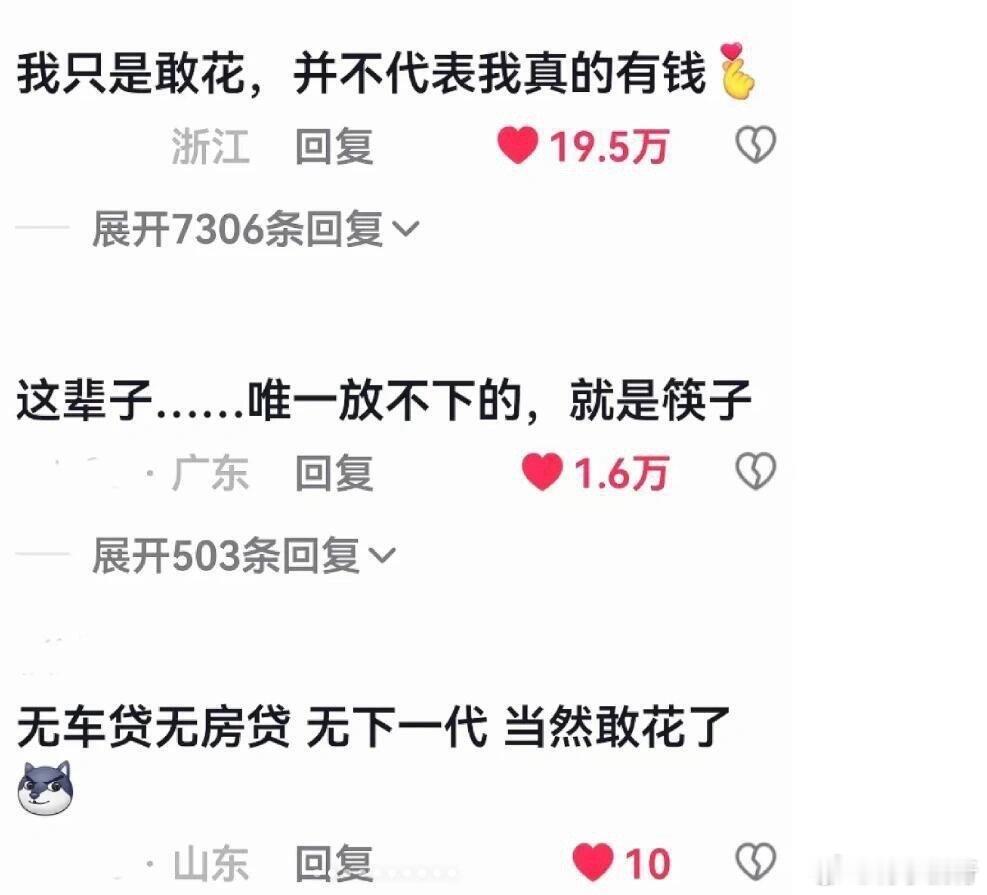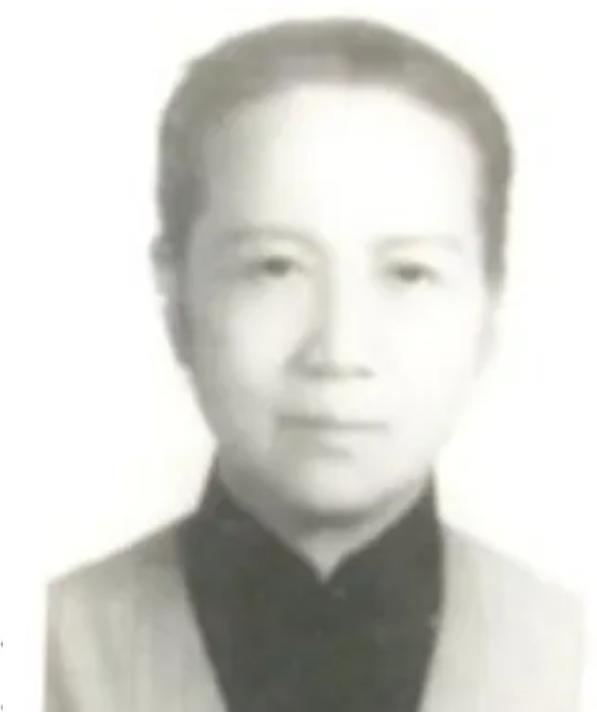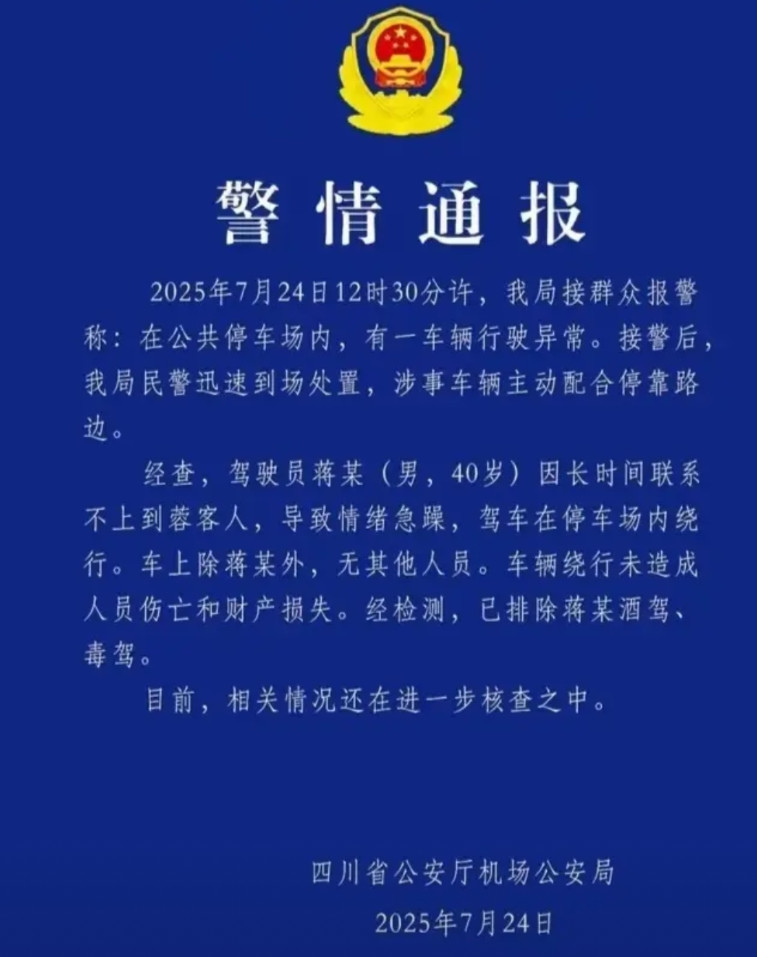1949年12月15日深夜,成都北校场公馆地下密室,杨森亲手锁上第18个樟木箱,金条碰撞声让副官李德明喉结滚动。“军座,专机只能带三个箱子......“话音未落,杨森突然将钥匙拍在桌上:“明早把这个交给汉烈。“
1949年12月,中国内战接近尾声,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土崩瓦解。四川作为国民党最后的重要据点,承受着巨大的军事压力。12月11日,国民党将领郭汝瑰在宜宾起义;12月13日,解放军攻占宜宾;15日进占简阳;16日拿下乐山。成都平原的国民党军队退路被迅速切断,成都城内弥漫着撤离的传闻,市民议论纷纷,官员与军人家属开始收拾行囊。杨森,作为川军中的核心人物,深知大势已去,面临军队撤离与个人财富处理的艰难抉择。
杨森是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的关键人物,曾任贵州省主席等要职,经历了数十年军政生涯。他以强硬作风和灵活策略闻名,积累了大量财富,其中包括存放在成都北校场公馆地下密室的金条。这些金条不仅是个人资产,也是他计划撤往台湾的资金保障。北校场公馆位于成都城北,靠近黄埔军校成都分校旧址,是杨森临时指挥撤离事务的据点。此时,他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做出决定,既要保全家族利益,又要应对军队的存亡。
1949年12月15日深夜,杨森在地下密室锁上第18个装满金条的樟木箱。面对副官李德明的提醒——专机只能携带三个箱子,他果断将钥匙交给儿子杨汉烈。这一举动不仅是对财富归属的安排,更是对二十军未来走向的托付。杨森选择带走部分金条撤往台湾,同时将大部分财富和军队的命运留给杨汉烈,体现了他对时局的判断:国民党在大陆的败局已定,家族与军队需要新的出路。
杨汉烈,时年25岁,刚被任命为第二十军少将军长,肩负重任。12月16日清晨,他收到父亲留下的公文包,内有兵符印信和字条:“存亡之际,可寻贺龙。”杨森已乘专机离去,留下“伺机而动”的暗示。面对解放军的压境和军队内部的分裂,杨汉烈迅速行动。12月17日,他宣布与解放军联络起义,试图带领二十军走向新生。这一决定并非毫无阻力,内部派系矛盾随之显现。
二十军内部,黄埔系年轻军官支持杨汉烈,保定系老将则态度暧昧。参谋处长景嘉谟强烈反对起义,指责杨森带走1200两黄金,留下混乱局面。12月17日的会议上,景嘉谟甚至拔枪威胁,134师师长萧传伦因家人被控制而动摇。次日凌晨,景嘉谟率两个团突围,留下字条讽刺杨汉烈,显示出他对投降解放军的坚决抵制。景嘉谟的选择反映了部分国民党军官在末路中的挣扎,既不愿屈服,也不甘心覆灭。
杨森带走三个箱子的金条飞往台湾,而杨汉印在重庆白市驿机场出现时,竟携带有五个黄金箱,超出预期。这些金条的来源引发疑问,可能来自杨森的秘密安排。杨森留给杨汉烈的密令中提到,若局势不可挽回,可携黄金赴港,显示他对家族后路的多重准备。然而,杨汉烈最终选择起义,未动用这批财富,部分金条的下落成为历史谜团。景嘉谟后来在成都废墟中挖出三根金条,潜逃香港,也暗示金条分散的复杂命运。
12月26日,杨汉烈在四川金堂率部起义,部队放下武器,接受解放军整编。次日,成都和平解放,市民夹道欢迎,标志着国民党在四川的最后抵抗瓦解。二十军的大多数官兵融入新中国建设,结束了其作为国民党武装的历史。景嘉谟的残部则在川康边境溃散,与胡宗南部队火并后几近全灭,显示出顽抗者的悲惨结局。
杨森在台湾度过余生,晚年常思念留在大陆的儿子,未再返回故土。杨汉烈起义后投身新中国建设,改革开放后成为企业家,完成了从军人到平民的转型。景嘉谟逃亡香港,晚年在街头摆摊,回忆往事时充满遗憾。他的坚持虽有气节,却难逃时代洪流的碾压。
杨森的决定既有现实考量,也有家族私心。他将金条和军队交给杨汉烈,既是无奈之举,也为儿子留下了选择的余地。杨汉烈的起义顺应了历史潮流,避免了更多无谓牺牲。而景嘉谟的逃亡虽显个人意志,却难掩孤立无援的结局。金条的去向、军队的命运与个人的选择,共同构成了这段历史的丰富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