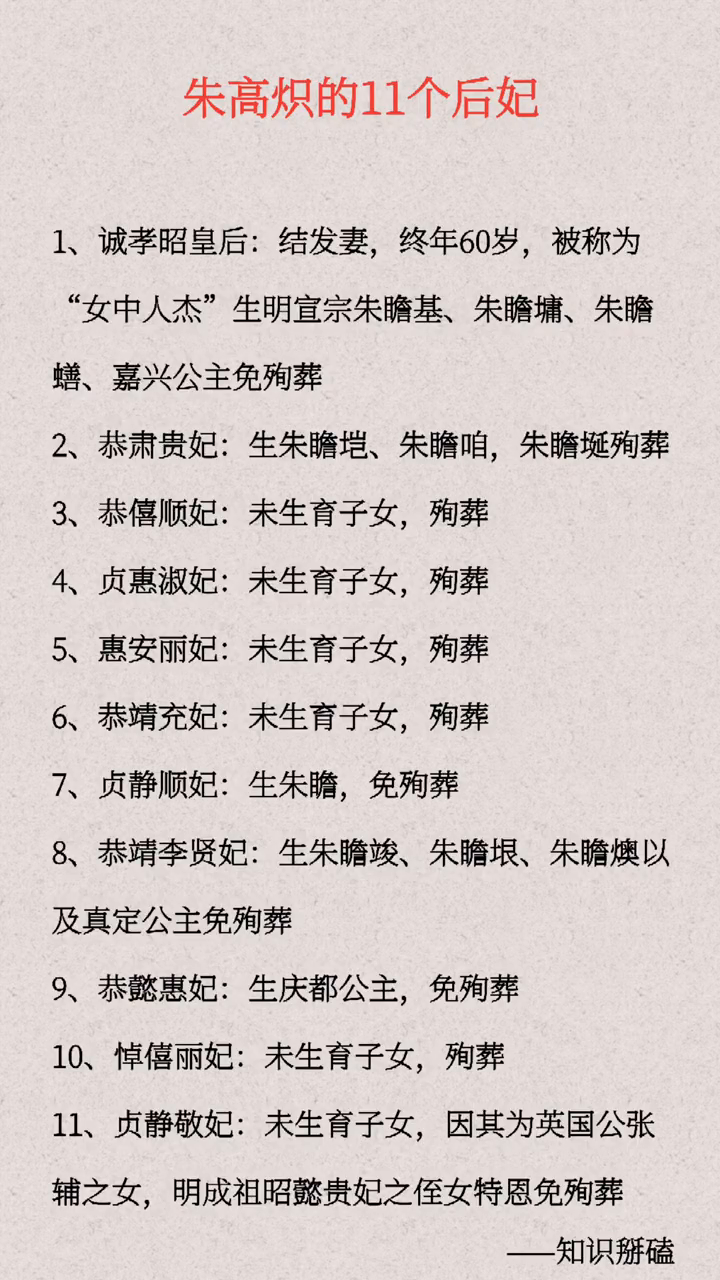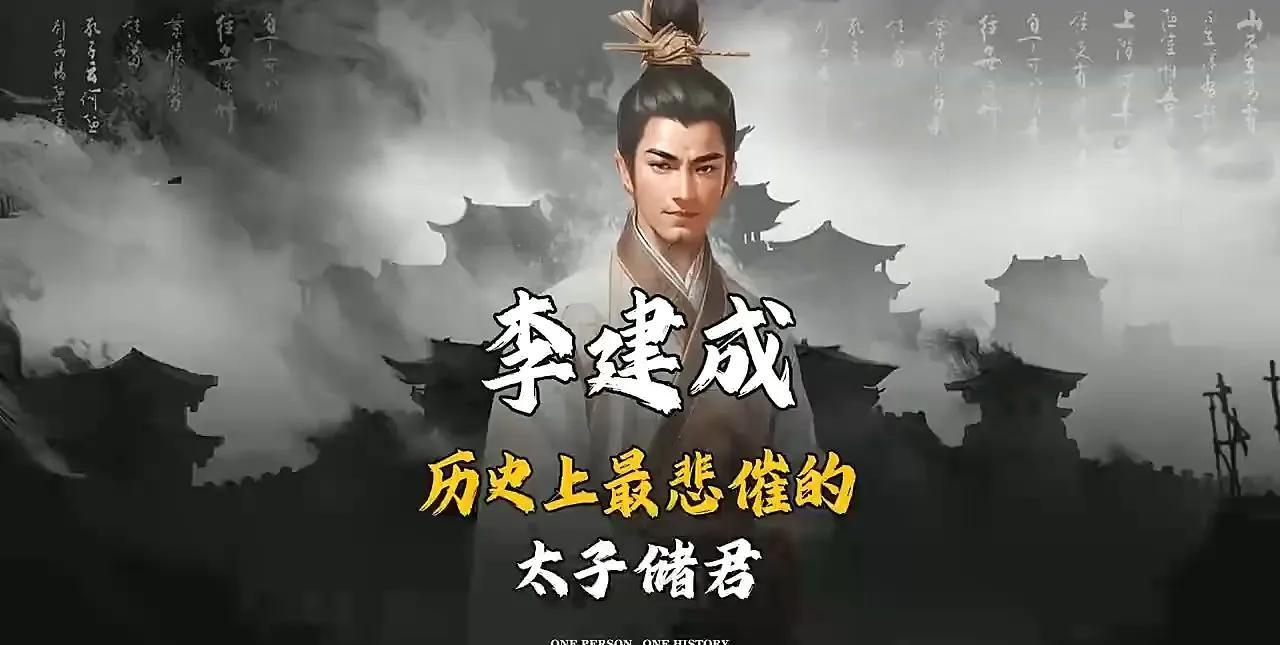皇帝死了。死在路上,死在北征归途中。消息一旦传开,局势将崩。六军未回,京城空虚,外患未平,朝堂权力真空。一旦震荡,局面将一发不可收拾。就在这紧要关头,几个文臣、内官,凭一口气、一点胆,把整个王朝托了下来。 但这一口气,也藏着风险。藏尸、封口、布诏、运筹,每一步都不容差错。杨荣,就是这场静默政变的主脑。 1424年七月,榆木川,草木焦黄,气温灼热。朱棣一如往常,亲率六师北征。目标,是漠北蒙古。过去二十年,他一共五次亲征,从未示弱。这一次,也不例外。 可这次不一样。 七月十六,皇帝突感身体不适。起初没人太在意。他年近六十,风尘仆仆,多次征战,稍感疲乏也属正常。可两天后,情况急转直下。 七月十八,永乐皇帝朱棣,驾崩于榆木川行营。 军中一片震惊。随行的马云、杨荣、金幼孜三人,第一时间受命处理后事。可此时的“后事”,不是丧仪,而是保密。保住皇帝驾崩的消息,就是保住整个王朝。 外有北元残部虎视,内有朱高炽尚未继位,皇太孙朱瞻基年纪尚轻。皇帝若死,天下将乱。 当晚,军营灯火彻夜不熄。三人围坐军帐,气氛凝重。没人敢哭,没人敢传丧。杨荣开口。他不是武将,但这一次,他说了算。 遗体,不能示人。皇帝,必须“活着”。 命人寻来锡器,熔炼密封,制成圆筒。遗体放入,封口焊死。棺不成棺,筒如军器。外人只道运粮,实则是皇帝梓宫。 棺封之日,命令下达——日常照旧,按常例三餐进膳,军中上奏依旧“亲批”,一切维持原样。任何泄密者,斩。 这不是权谋游戏,是实战,是危局自救。 锡桶铸成后,工匠们被秘密处决。理由很简单,消息不能传。 军中死寂,号令井然。杨荣与金幼孜,一个处理机要文书,一个联络内廷宦官;马云暗中调度守军,确保安全。 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政变。一群文人、太监,把皇帝的尸体藏在一筒冷金属中,把全军的秩序维系在一张笑脸后。 行军继续。梓宫随军东归。十几天,队伍不缓不急,一路平稳。沿线百姓、军士、驻营官兵,都未察觉异常。 日升月落,军中照常读诏,宦官依旧传旨。没人敢问,没人敢疑。 杨荣掌军务,以皇命名义批示大小政事。他没有兵权,但他有诏书,有皇印。这几样东西,在动荡未明的当下,就是最高权威。 与此同时,他已派人回京通报太子朱高炽。只不过,消息不是“死讯”,而是“密报”。只有太子知,其他人一律封口。 金幼孜负责典仪,不动声色安排葬礼前置事宜。封地遣使、地方通知、太常预演,都在秘密推进中。马云,则持续在军中压制波动。 整个王朝,表面无事。实则,暗潮汹涌。政治空窗期,全靠一群文臣、宦官,用纸笔、律令、权威硬撑。 九月初,军队行至潼关。杨荣与少监海寿分队先行,携密诏入京。 日夜兼程,九月七日,朱高炽接报。 接诏时,他瘫坐榻上。据说他因肥胖,难以下跪,只能抱诏痛哭。但很快,他冷静下来,安排继位。 派皇太孙朱瞻基出京,迎接军队,扶梓宫东归。又命廷臣、太监联络京营守卫,调集太常官员筹备即位大典。 消息发布那一刻,京中震惊,却未乱。因为该知道的,都已准备;不该知道的,仍在“太宗在世”的假象中。 朱高炽顺利即位,年号洪熙,成为明仁宗。群臣朝贺,政局平稳。短短几周,从皇帝死去到新君即位,几无波澜。 这其中,杨荣之功,居首。金幼孜紧随。马云虽属宦官,也立大功。 日后,三人均获重赏。杨荣任大学士兼太常卿,主持朝政;金幼孜升为户部尚书;马云虽无高位,却得封赏,赐金数千。 他们赌对了。赌对了“秘不发丧”的策略,也赌对了朱高炽的冷静。 一场危局,就这样被文官们,从混乱边缘拉回。 这一年,是永乐二十二年。朱棣在北征途中死去,他的一生,以战起,以战终。 但比战争更复杂的,是身后事。不是谁接位的问题,而是怎么接。 太子的资格没人质疑。但如果继位是在皇帝尸身未寒、北军未归、京师无卫之时,哪怕只乱一夜,就可能万劫不复。 这一夜,朱棣的尸体被藏入锡筒,一字不发;杨荣握笔封诏,一刻不乱;金幼孜披衣传令,一步不退。 他们不是夺权者,却也完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接班”。 不是刀剑,而是策术;不是皇命,而是胆识。 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权力争斗,而是一场政务硬仗。一场文官体系对混乱可能性的精准防守。 也许,这才是真正的“纸上江山”。